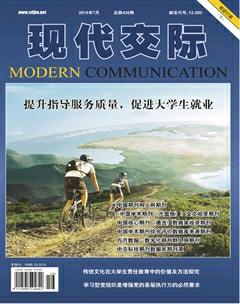西方自由限制理論綜述
趙鑫+楊博
[摘要]法律的強制性表現在對自由的保護與限制上,探討法律與強制性的關系也便是探討法律對自由限制的諸多規定性。在西方法哲學思潮的源流中,大致有八種法律限制自由的指引性理念:洛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諾齊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康德的邊際約束,密爾的傷害原則,家長主義對自由的限制原理,以賽亞·伯林的自由限制標準以及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強制標準。
[關鍵詞]邊際約束 傷害原則 家長主義 積極自由 消極自由 差別原則 法律的道德強制
[中圖分類號]D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4-0020-02
法律為何能夠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原因之一是其具有國家強制性,而強制性作何表現?同公法的聯結,主線是對權利的剝奪,但內隱著對喪失權利者的補償或變相補償;同私法的聯結,主線是對權利的滋養,但內隱著對剝奪權利者的制裁。而權利之本質,抑或其活動的空間,大抵可歸結為自由云云。因此,我們談法律、談強制性、談法律與強制性的關系,必然應當落腳于法律對自由的限制上。而談限制,我們便應當考察法律限制自由的啟動條件、運作方式乃至其限度,而梳理西方法哲學思潮脈絡,大致有八種典型的自由限制理念,我們將逐一作解讀如下。
一、洛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
洛克認為,社會成員的生命、自由與財產權是先于國家和政府而存在的,也即與自然狀態共生,且不因國家的產生、社會契約的締結而失去“絕對性”與“不可剝奪性”。但與此同時,洛克提出了獲取財產權利的道德正當性條件,即“留有足夠的和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共有”[1]9的限制性條款。諾齊克將洛克的限制性條款理解為“使其他人的狀況不致變壞”[1]8,即如若占有使另一人基于財產的可支配性程度有所下降,這種占有就是不合法的。對占有削弱財產支配自由的表現,諾齊克認為有兩種形態:首先,使別人失去通過一個特殊占有來改善自己狀況的機會;其次,使別人不再能夠自由地使用它先前能使用的東西。
二、諾齊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
諾齊克對洛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進行了較弱理解,這樣而言,“一個人就不可以把一個沙漠中的唯一一眼水井占為己有,并隨意開價”[2]56。這種較弱理解便必然需要一個更為復雜的矯正正義過程來補強獲得財產權利的正當性論證過程:假如一個人的占有違背了這種限制性條款,使得其他任何一個人的情形比他的曾經最糟的情形或可能預想到的最糟的情形更糟,那么,這個人的占有就不具備諾齊克所說的道德正當性。
三、羅爾斯差別原則對自由的限制
羅爾斯的“差別原則”對諾齊克資格正義理論中的矯正標準作了補充。羅爾斯對“差別原則”的闡述經歷了一個調整的過程:起初,羅爾斯從帕累托改善的角度論證“不平等”存在的合理性:這種不平等的存在使得每個人的狀態都比原來更好。需要注意的是,羅爾斯強調的并非整體優化,而是每個個體生存狀況的改善,譬如征稅——在羅爾斯看來——之所以是正義的,不僅僅要因為稅收惠及者的狀況變好了,還要因為納稅人的狀況也變好了。但羅爾斯的這套標準無法導出唯一、確定的結果,因而被人以“比原來更好的形式不一定只有一種”等類似的理由加以詬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羅爾斯在他的《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中對“差別原則”作了補充論述:如果有多種選擇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比原來更好,則應當在其中挑選能夠最大程度改善原本最不利者狀況的方法作為標準。[3]207
四、康德權利作為行為的邊際約束
相較于洛克、諾齊克與羅爾斯的標準,康德道德哲學的邊際約束構想顯得更為嚴苛。自由這一概念乃是康德的道德和法律哲學的核心。然而他卻對倫理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作了區分,對他來說,倫理上的或道德上的自由,意味著人之意志的自主性和自決;只要我們能夠遵守銘刻在所有人心中的道德律,那么我們在道德上就是自由的。這一道德律要求我們根據某一被我們希望成為普遍之法的準則來行事。康德把這種道德律稱為“絕對命令”[4]27。而另一方面,他把法律上的自由定義為個人對己身意志之外的強制力量,尤其是他人的專斷與控制的獨立與排除,康德認為這種獨立是人根據人性而具有的原初的、唯一的、固有的權利。他指出,這一基本權利含有形式平等的思想,因為它意味著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意志個體,且因為意志獨立,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康德非常崇尚人格自由與人格的內在尊嚴,他認為,人永遠都只能作為目的而存在、決不能被其他任何人視為實現己身目的的工具與手段。康德把法律定義為“那些能夠使一個人的專斷意志按照一般的自由律與他人的專斷意志相協調的全部條件的綜合”[4]30。這就意味著,如果某個人的行為或狀況,根據設定自由的一般法律能夠與除該個體之外的所有他人的自由并存且無沖突,那么任何人妨礙該個體實施前述范圍內的行為或者妨礙該個體維持這種平和的現狀,就是侵犯了該個體的自由。此時,法律便可以運用強制力量來對付那些不適當和不必要干涉他人自由的人。
五、密爾的傷害原則
密爾所提出的傷害原則與康德的邊際約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似。密爾認為,只有當為了防止和控制一個人對他人利益造成損失時,限制一個人的自由才是必要的。密爾在《論自由》中針對“社會所能合法適用于個人權利的性質和限度”[5]132的問題提出了如是的看法,他認為對于文明社群中的任一成員,唯一能夠在違背其意志的情況下、不失正當性地剝奪或限制其權利的情形,僅僅在于防止對他人自由的侵損。“人之所以有理由個別地或集體地對其中任何成員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的唯一目的,乃是自行保護。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之所以能夠施用權力以反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其唯一的目的就在防止危害他人。然而,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不論是物質上的還是道德上的私利,都不構成采取這種干涉措施的充足理由。”[5]135密爾的傷害原則是為了限制公共權力對個人自由的強制性干預而制定的,因為其具有較為透徹、簡便的正當性表象而被當代許多國家所采用,我國憲法也有類似的規定。
六、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家長主義原則
密爾及其后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均反對以“家長主義”為名的自由限制立法,他們將溫和慈父的護佑透析為潛藏自由干預危機的風險來源。當一個人的行為會嚴重傷害自己,或者他的行為將使他喪失重大利益時,可以限制他的自由。法律通過控制自我傷害,引導其自我利益的實現,增進自由。哈特認為,為了保護個人自由,有時候對于因為智力、職位、經濟等方面而處于弱勢的人,應予以保護,支持法律禁止某些受害者同意承受的損害。對此原則的批評,主要是認為該原則有擴大國家對個人自由干預的危險,應嚴格控制運用該原則。[6]11-13
七、以賽亞·伯林標準:僅應當對積極自由進行限制
在古典自由主義與家長主義關于傷害標準的張力映襯下,以賽亞·伯林的沖突邊界解釋似乎更為形象。以賽亞·伯林就自由作了兩個向度的界分,一是“消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免于做某件事情的自由(freedom from);另一則是“積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是要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 do)。消極自由指主體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行為,而不受外界的強回和干擾,強調的是防御;而積極自由側重行為主體被保障的自由,強調的是擴張與進攻。[7]53-54自殺的自由是消極自由,通俗來講可以解釋為,我殺我自己、你不要管我,而非我要你來殺我、你必須殺我。安樂死的自由是積極自由,通俗來講就是,當我想死的時候你一定要讓我死,安樂死的“積極”性就體現在外力通過提供死的方法保證其死的自由。
因此,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自由是消極自由。以賽亞·伯林這一劃分十分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一般為法律所保護的自由是消極自由、而非積極自由。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來說明:
就用餐者而言:
積極自由:我要吃羊肉,餐館必須提供給我羊肉,而不能是牛肉。
消極自由:我要吃羊肉,你不能不讓我吃羊肉。
就經營者而言:
積極自由:我只賣牛肉,你必須只吃牛肉,而不能吃羊肉。
消極自由:我只賣牛肉,你不能不讓我賣牛肉。
很顯然,在用餐者—經營者的結構中,積極自由發生了嚴重的沖突,如果法律同時保障二者的積極自由,勢必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積極自由往往會產生限制他人消極自由的效果,在上述結構中,用餐者的積極自由意味著強迫餐館提供羊肉、即“不讓他賣牛肉”,便是對經營者“不能不讓我賣牛肉”的消極自由的限制。因此,法律未曾賦予每個人以不加限制的積極自由并非因為積極自由本身是一種惡或者在價值上遜于消極自由,而是因為積極自由會藉由社會成員行為模式的碰撞產生不可行(能)的外觀。正如有的學者概括的那樣,“當每個人都擁有無限的自由時,每個人都不再擁有自由。”[8]61因此,在以賽·亞伯林看來,積極自由必然應當受到限制。
八、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強制理論對自由的限制
同以上七種自由限制理念相比,德富林的道德強制標準最為松泛,卻也因此面臨擴大對自由不當干預面積的構難。德富林提出了實現道德領域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四個原則,亦即是法律強制實施道德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第一,容忍與社會完整統一相協調的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只要不超出容忍的限度,無論什么都不應由法律來懲罰。僅僅說大多數人不喜歡某一行為是不夠的,必須有譴責的真實感情。憎恨的出現就表明容忍的限度已到邊緣,沒有不容忍、義憤和憎惡,任何社會都不能進步;它們是道德法則背后的力量。
第二,容忍限度的改變。德富林說:“我假定道德標準不會改變;就它們來自神的啟示來說,它們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我又傾向于假定,社會作出的道德判斷總是對社會有利的。但是,社會容忍偏離道德標準的程度卻是一代一代變化的。”[9]9
第三,盡可能充分地尊重個人隱私。這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要把所有私人的不道德行為從法律領域排除出去,而是指個人隱私的權利主張有與公共利益相對的獨立的分量。
第四,法涉及最低限度的而不是最高限度的行為標準。任何僅從逃避懲罰的目的出發控制自己行為的人都沒有多大的價值,每個有價值的社會都會為它的成員設定高于法律的標準。這一點是明顯的,但仍然需要強調,因為人們常常不能夠區分兩個問題:社會是否有權通過道德判斷和法律應否被用來強制實施它的判斷。
上述四個原則劃定了法律應當干預道德、強制實施社會道德的界限。德富林并不把這四個原則看作做極嚴格的、沒有松動余地的規則,而是看做是應當考慮的因素。[9]8-10
【參考文獻】
[1]張翠梅,邱子建.對“財產權利之道德正當性”的論證——從洛克與諾齊克的權利理論談起[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04).
[2]張翠梅.諾齊克之獲得財產權利的“限制性條款”[J].學術交流,2009(03).
[3]周琦.羅爾斯差別原則的理論價值[J].學術界,2009(02).
[4]羅克全.“道德邊際約束”與國家限度——諾齊克的權利理論研究[J].天津社會科學,2003(05).
[5]張繼亮.傷害、利益與權利——理解密爾傷害原則的新視角[J].道德與文明,2015(05).
[6]黃文藝.作為一種法律干預模式的家長主義[J].法學研究,2010(05).
[7]李石.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辨析——對以賽亞·伯林“兩種自由概念論”的分析與批評[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
[8]譚杰.論康德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兼與伯林兩種自由概念的比較[J].道德與文明,2011(04).
[9]孫海波.道德難題與立法選擇——法律道德主義立場及實踐檢討[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