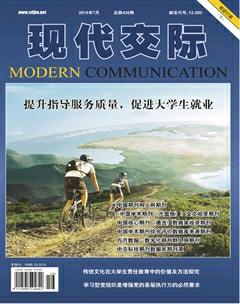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對比研究
蘭垂洪
[摘要]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方法論研究范式歷來是社會學發展史中的爭論主題,不同范式的學者發出不同的聲音,對社會學的研究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試圖以實證主義社會學傳統的奠基之作《自殺論》和人文主義社會學傳統的完美詮釋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切入口,從本體論、方法論和研究邏輯三個方面探討它們之間的不同。
[關鍵詞]實證主義 人文主義 自殺論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14-0022-02
著名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和韋伯都是古典時期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代表作分別是《自殺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兩部社會學經典作品完美地詮釋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學思想,成為社會學學科的奠基之作,同時也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方法論研究范式,即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下面我們將以這兩部作品為例,從本體論、方法論和研究邏輯這三個方面來考察這兩種社會學研究傳統的不同之處。
一、本體論之爭
從哲學上看,方法論的不同是由于對世界本質認識的不同,因此對事物的解釋也就不同。歸根結底,這是哲學上的大問題,涉及存在的性質和特征。本體論具有優先性,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因為它提出“存在”的本質問題,即我們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實”并且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的。《自殺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分別體現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思想。自然地,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本體論思想也體現在這兩部作品之中。
(一)實證主義的本體論
本體論就是關于“存在”的本質問題。實證主義社會學傳統認為,社會是真實存在于世界上的,社會優先于個人,社會是第一性的,個人是第二性的,社會具有個人所不具有的獨特屬性,這就是本體論中的社會唯實論。社會是實實在在存在于世界上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把社會完全看成脫離個人生命力的存在。我們將探討《自殺論》中所體現的社會唯實論。
《自殺論》既是對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準則思想的運用,又為社會學學科地位提供了合法性。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運用了其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準則,即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一種社會事實的決定性原因,應該到先于它存在的社會事實之中去尋找,而不應到個人意識的狀態中去尋找”。[1]也就是說,社會學研究就是用一種社會事實去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而這種社會事實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在的物體。在《自殺論》中,迪爾凱姆把自殺率、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都看成是社會事實,它們具有個人所不具有的獨特屬性,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殺率是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綜合起來看,社會優先于個人,社會具有不可還原性。社會層次的自殺率、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具有單個人所不具有的獨特屬性。
《自殺論》中體現的本體論思想正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社會唯實論思想。不管是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果來看,《自殺論》都反映了實證主義的本體論。
(二)人文主義的本體論
人文主義社會學傳統認為,社會是虛構的產物,個人組成了社會,社會的性質可以還原為個人的性質,社會只是一個符號,一個集合名稱而已,沒有實在的意義。這就是本體論中的社會唯名論,社會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一種假象,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把社會完全看成個人主觀意識的產物,或者叫作“想象的共同體”。下面我們將探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體現的社會唯名論。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韋伯的經典代表作,是其“理解社會學”思想的集中反映。他把具有主觀意義的社會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注重社會行動的解釋。該書以新教徒的社會行動為研究對象,揭示社會行動背后的主觀意義,韋伯采取的是主觀、移情式理解的方法。在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徒的倫理觀導致社會行動,從而導致社會現象的出現。“志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的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2]這種觀念使新教徒把增加資本當作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使其社會行為合理化、道德化,這必然更加鼓勵新教徒們采取這種行動。韋伯在該書下篇部分考察了加爾文宗、虔信派等諸派的教義教規。就加爾文宗而言,“首先教義就是如此。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世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誡,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3]在這里,社會是虛構的,只有單個的新教徒是實在的,新教徒們堅持自己的宗教觀,進行生產實踐活動,構成群體、組織和機構,形成資本主義社會。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體現的本體論思想正是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社會唯名論思想。不管是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果來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都反映了人文主義的本體論。
綜上,從本體論上看,對于我們的外部世界是否是“真實”并且獨立于我們而存在的這一問題,《自殺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其所體現的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社會唯實論思想;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其所體現的則是人文主義社會學研究傳統的社會唯名論思想。社會唯實論和社會唯名論都是社會學中的本體論。
二、方法論的不同
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傳統體現在本體論上的不同就是社會唯實論和社會唯名論的不同,這也就決定了它們各自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不同。我們知道,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都主張人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可以獲得對社會現象的正確認識,只是認識的手段不同,即方法不同。《自殺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運用不同方法論的兩部典范之作。
(一)實證主義的方法論
因為實證主義社會學傳統遵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力求探尋社會現象的發展運行規律,因此,其主張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在抽象層次上,從社會結構的宏觀角度著眼,力圖把握社會整體的運行狀況。《自殺論》的研究采取的就是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從社會層面上來研究自殺現象。
首先,在《自殺論》中,迪爾凱姆把研究對象確定為一個社會的自殺率:“每一個社會在它歷史上的每一個時刻都有某種明確的自殺傾向。我們通過比較自殺的總數和總人口數之間的關系來衡量這種傾向的強度。我們把這個數據稱之為被考察的社會所特有的自殺死亡率。”[4]因此,自殺率具有整體的性質,是一股自殺的社會潮流。其次,迪爾凱姆排除了心理變態和自然環境等“非社會因素”,開始探索自殺的社會原因和社會類型。這種社會原因就是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這是整體主義方法論的自殺歸因的表現。最后,迪爾凱姆提出了抑制自殺率的策略。他從社會的結構性層面出發,認為抑制自殺率最合適的團體是職業團體或行會,它可以成為一種集體人格,形成對成員的權威,成為他們的道德環境。因此,這樣的社會凝聚力和道德環境是從整體主義提出的。
(二)人文主義的方法論
人文主義社會學傳統遵循歷史主義的意義闡釋與因果解釋方法,力求獲得對事件或行動的價值或意義理解,因此,其主張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取向,在具體層面上,從個體能動的微觀角度出發,來理解社會整體的運行情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試圖探討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親和性,通過歷史理解的方法探究新教徒社會行動背后的倫理價值觀。
韋伯從社會唯名論出發,堅持個體先于社會,認為通過對個體的理解就能達到對社會的理解,在個體行動的主觀意義中能夠找到社會結構的因果解釋。這樣,以理解為橋梁,韋伯將個體與社會聯結起來,形成了其個體主義的、理解的方法論。[5]為了探究近代資本主義為什么只在西方而不在東方出現這一問題,韋伯考察了西方從古至今的文化觀,認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倫理是其根源。新教倫理為投資者,即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這種資本主義精神的合理性提供了道德倫理依據,為理性經濟人行為提供了精神支持。[6]韋伯運用文化價值來研究經濟制度的發展,建立道德倫理與經濟行為之間的聯系。這就從新教徒的價值倫理觀來看待社會行動,單個人的行動構成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該書遵循的是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取向。
三、研究邏輯的不同
科學研究有兩種研究邏輯:演繹和歸納。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分別運用前者和后者,對應的方法論分別是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因此,《自殺論》和《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分別運用了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
(一)實證主義的研究邏輯
實證主義運用了演繹邏輯,演繹邏輯是從一般原理或理論出發,通過邏輯推理來解釋具體的事件或現象。《自殺論》從整體主義出發,研究各個國家的自殺率及其自殺原因和類型。從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的一般原理出發來看待具體的自殺案例,而不是列出自殺案例的清單,然后總結一般理論。實際上,對個人自殺進行名副其實的觀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收集到大量全面、真實的自殺案例材料。這就決定了迪爾凱姆必須進行演繹邏輯的推理,顛倒研究的順序:不是首先研究大量的自殺案例,研究它們的特點和差異,研究這些特點和差異的原因,然后對它們進行分類,而是一開始就直接研究自殺的社會原因,并根據不同的社會原因對自殺進行分類。迪爾凱姆從社會整合和社會規范的一般原理出發來尋找自殺的社會類型和社會原因,因為運用歸納邏輯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人文主義的研究邏輯
人文主義運用了歸納邏輯,歸納邏輯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通過對大量的現象進行觀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結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從看得見的活生生物質到看不見的精神。[7]在書中,韋伯從個體主義出發,觀察大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不同行為,了解到他們行動背后的倫理價值觀的不同。“對于這些情況無疑只能這樣解釋:有環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這里是家族共同體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氣氛所首肯的那種教育類型)決定了職業的選擇,從而也決定了一生的職業生涯”。[8]這就說明新教倫理影響了職業選擇,影響了社會生產實踐活動,最終形成了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在該書中,韋伯還通過挖掘禁欲主義新教諸分支的教義和實踐倫理觀,發現禁欲主義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具有某種“親和性”,這也是這本書最后得出的結論。
【參考文獻】
[1](法)迪爾凱姆(著),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2][3](德)韋伯(著),于曉,陳維綱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修訂版)[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4](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著),馮韻文(譯).自殺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5]黃波.從個體行動到社會結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方法論軌跡[J].蘭州學刊,2008(08):100-101.
[6][7]葉靜怡.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方法論和思想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04):63-68.
[8](德)馬克斯·韋伯(著).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