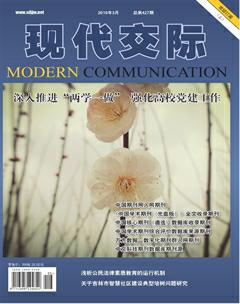淺析廣告的話語霸權
王凱
摘要:“霸權”一詞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提出的。當今社會,消費主義“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和日常實踐,在中華大地上開始四處蔓延”[1],廣告在消費社會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廣告顯性霸權是指廣告對控制對象的信息接收和行為選擇上的一種強迫,這種廣告霸權是外在的,是通過觀察就可以感受到的。”
關鍵詞:霸權;廣告;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H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5-0068-02
“霸權”一詞是由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提出來的。葛蘭西認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為了確保他們在社會和文化上的領導地位,利用霸權作為手段,勸誘被統治階級接受他們的道德、政治和文化價值。筆者拋開政治的立場,僅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對廣告話語霸權進行探析。廣告話語霸權的主體與客體分別是廣告的文本的制造者與廣告的接受者。廣告是一種以經濟為目的的媒介話語。在利益的驅動下,廣告通過與媒體的合謀,對意識形態進行物化,以各種方式謀求自己的權威話語方式。話語霸權的地位具有強大的滲透力、影響力,甚至是控制力,直接作用于人的潛意識及無意識層次,不僅預設和引導了現代人的消費觀念,同時對現代人的生存狀態也會發生極大的影響。廣告所傳達的價值標準一旦被社會認同,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指標和原則。
一、顯性霸權
當今社會,消費主義“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和實踐活動,在中華大地上開始四處蔓延”[1],廣告在消費社會中充斥和影響著人們的視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消費信息的傳播角色。“廣告顯性霸權是指廣告對控制對象的信息接收和行為選擇上的一種強迫,這種廣告霸權是外在的,是通過觀察就可以感受到的。”[2]它主要表現在對受眾的感官沖擊上,包括重復性的強化灌輸和不請自來,還表現在對大眾文化機制的支配地位,包括廣告宣傳對企業及其他媒介文化的壓力與制約。
1.重復灌輸
廣告的重復灌輸體現在廠商憑借資本實力,在各類大眾傳媒上不斷重復地播放同一段廣告,不斷強化受眾對廣告內容的感知和印象程度,形成話語霸權。如果這種簡單粗暴的重復得到有效傳播,那么在這種重復中便不再存有異議,流行意見便在不斷的重復中形成,意識形態漸漸物化到廣告產品中,影響、強化和左右消費者的觀念乃至行動。廣告信息往往簡單明了,其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地不斷重復,容易使消費者印象深刻。縱使這種廣告霸權顯而易見,或者作為廣告受眾的消費者初時會頗有異議,但在接受程度上還會產生難以抗拒的效應,迎合了謊言重復一百遍后就很容易形成真理的俗語,也符合了心理學中關于心理暗示所形成深刻印象的規律。如一則保健品的廣告:“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只收腦白金”。縱使該廣告已經推出就飽受詬病,但廠商仍然堅持對消費者的重復灌輸。即便消費者對廣告再有意見,也無意識間把腦白金和收禮、送禮聯系起來,自覺和不自覺地導向購買行為。恒源祥的“羊羊羊”系列廣告堪稱重復灌輸的極致。廣告詞信息單一,對人們進行轟炸式重復灌輸,讓人們無處可逃。隨著廣告近乎泛濫的傳播,恒源祥的廣告詞植根到人們的意識中,恒源祥的品牌也就隨之印入人們的腦海中了。
2.不請自來
廣告的不請自來指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各種各樣的廣告,大多數不是我們主動獲求的,也即在視聽上不是主動聽取和閱讀的。全媒體時代,作為社會中的任何人無不被不同的媒體包圍著,同時也就不得不被不同的媒體廣告包圍著,可以說,有信息傳遞的地方幾乎就有廣告的傳播。如在互聯網中,在資本的支撐下,廣告主利用數據分析可精準地發現自己的目標受眾,采用利用彈窗、視頻插播等方式大量進行廣告傳播,廣告信息對目標受眾的不請自來侵占著消費者的私人時間和空間,讓消費者有欲罷不能的無奈。除了互聯網,戶外廣告更是無處不在,不管你是在車站等車,在飯店吃飯,還是在商場購物;不管你是不是想要瀏覽和傾聽廣告,每個人幾乎都逃離不了廣告的包圍,消費者在廣告面前實在沒有主動權可言,只能任憑廣告對自己的兜售。
3.對企業和其他媒介的壓力與制約
廣告學者伯曼曾指出,在大眾文化中,最具支配性的社會機制就是廣告。這是廣告話語霸權對社會巨大影響的佐證。市場化的今天,資本運作是關鍵,而廣告則是資本運作的助推器。“廣告宣傳對企業的壓力源于企業生產導向向營銷導向的轉變”[3]。還必須看到,當今時代的商品同質化嚴重,不同品牌產品的質量差異逐漸縮小,“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客觀現實出現了,廣告是企業最有效的促銷手段,同時企業對廣告的依賴也越來越強,廣告正在堂而皇之地也是頗顯力量地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獨立力量,廣告對企業的霸權可見一斑。
二、隱性霸權
相對于顯性霸權的顯而易見,隱性霸權的權威則是匿名的、隱蔽的,潛移默化中改變著人們的消費觀念。廣告隱性霸權是指廣告宣傳對受眾的一種文化規約力和廣告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受眾的一種控制力。[4]它并沒有強迫人們必須做什么,但卻往往引起相當一致的行為:說著同樣的廣告語,用著同樣的產品,接受同樣的消費觀。也正是因為這種隱性霸權的非暴力性,才使得人們被廣告這種隱性的權威支配言行,而且無從抗拒。
1.文化規約力
福塞爾在《格調》一書中提到,人們通過消費來體現其社會階層。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的消費體現是不一樣的。與上個世界的美國一樣,中國人民目前也存在對自己所屬階層的焦慮。人們樂意通過消費來展示自己的社會階層,這就為廣告宣傳對受眾的文化規約力提供社會條件。在產品質量同質化的今天,廣告主們樂意將自己的產品貼上標簽,如“豪華”“卓越”“成功”或者是“實惠”“低廉”,以這樣很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包裝,來將自己的產品劃分為高端或者是大眾。廣告的隱性霸權在對商品符號化的過程中形成并強化。一方面,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人們傾向于守本分,及根據自身的社會階層定位購買符合自己身份的產品;另一方面,在消費社會的今天,人們傾向于消費產品本身之外的附加價值,以提升自己的品位和格調。以化妝品為例,蘭蔻主打高端品牌,打造“質”重于量的高價位產品,而相宜本草則走的是大眾路線,所以當一個高層白領要選化妝品時,為了她的“面子”,肯定會選擇符合她社會身份的高端品牌——蘭蔻。
2.意識形態控制力
廣告將其傳達的意識形態植入人們觀念之中,成為其理所當然的生活觀念,讓人們在熱衷模仿和追求時尚中喪失自主性和反抗力,成為廣告的意識形態主體。于是便出現了“吃薯條、喝可樂長大的一代”,及代表愛情的鉆石、巧克力、玫瑰花等等。廣告的隱性霸權對人們的意識形態進行了解構與重組,所達成的效果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于廣告的顯性霸權對于人們的影響,隱形霸權更加難以推翻,因為它不像顯性霸權那樣容易察覺,沒有公開的阻力,人們很輕易地便會被這種隱性的權威控制喪失反抗的意識。在廣告的隱性霸權中,廣告總是以渲染與消費者同一戰線,為消費者代言的身份出現,但眾所周知,真正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廣告主,消費者只是目標。這種巧妙的主體置換造成了廣告主與消費者的普遍利益之間的虛假統一。
三、廣告話語霸權的根源
那么廣告話語霸權從何而來呢?阿爾溫·托夫勒曾經這樣指出,權力的來源有三種:暴力、金錢和知識[5],費愛華在《廣告話語霸權的生成機制研究》中亦指出,廣告話語霸權作為一種權力,其來源同樣有三種:資本、知識和暴力[5]。據此,筆者認為,在廣告的話語霸權中,資本是基礎,知識是橋梁,暴力是途徑,但廣告話語霸權的產生歸根結底源于資源及其轉化,其中經濟、信息是資源的主要構成部分。經濟和信息資源的不對稱及其轉化是廣告話語霸權產生的根源。
1.經濟資源的不對稱
“廣告作為一種以商業利益為根本目的的媒介話語,需要以強大的經濟資本為后盾,沒有經濟資本作為支撐和驅動就不會產生任何廣告霸權。”[7]經濟資源的不對稱是廣告話語霸權實現的關鍵所在。一個新產品問世,沒有充實的資金支持是無法形成廣告的強大宣傳氛圍的,沒有大轟大嗡的強勢廣告效應,就無法通過廣告來增強其品牌影響力,也就無法在消費者中形成深刻印象,打不開廣闊的市場,廣告的話語霸權也就沒有大展身手的機會。
2.信息資源的不對稱
在商業社會中,“信息不對稱”是一個普遍現象。占據文化資源多的人或機構享有對文化的霸權,具有讓人信服的權威。他們善于將各種信息進行加工,通過搜集、篩選、吸收、強化進行“編碼”,最后形成廣告話語。廣告話語的編碼作為廣告話語霸權建構的支點也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很顯然,廣告話語的編碼者相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講,占據著更多的信息資源。面對浩如煙海的產品,產品所包含的信息相對復雜不易被消費者知曉,因此,消費者更傾向于廣告編碼者制造的一系列的商品的“符號”來對廠商和產品做出判斷和購買的決定。以牙膏廣告為例,廣告主傾向于讓模特扮演牙醫、專家,給出專業的建議,或者“假裝實驗”,擺“事實”講道理,消費者默許他們占據的信息資源多的同時,也默許了他們的建議或者“事實”,廣告的話語霸權得以實現。
四、結語
無論廣告的隱性話語霸權還是顯性話語霸權,均已經對社會并對人們的生存方式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社會現實是,在商業社會中,廣告的存在是必然的,我們無法逃離廣告,自然也無法逃離廣告的話語霸權,但也無需悲觀,因為“廣告話語霸權的生成既是資本增值的需要,也是媒體提高實力和影響力的需要”[8]。對于消費者而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以免以為被廣告的話語霸權綁架而毫無還手之力;對于廣告主和媒體而言,不能一味地追求利潤而至社會的健康穩定而不顧。
參考文獻:
[1]李駿,對消費社會的一項社會學考察[J].理論導刊,2003(05):33-36.
[2][3][4]朱曉明,非暴力強迫——廣告霸權的文化解讀[J].現代廣告,2008(05):54-55.
[5]阿爾溫·托夫勒,權力的轉移 [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6]李淑芳,廣告傳播的擬態作用機制[J].當代傳播,2008(03):78-80.
[7][8]費愛華,廣告話語霸權的生成機制研究[J].南京師大學報,2009(11):61-65.
責任編輯:孫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