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玉成
■張麗鈞
你的玉成
■張麗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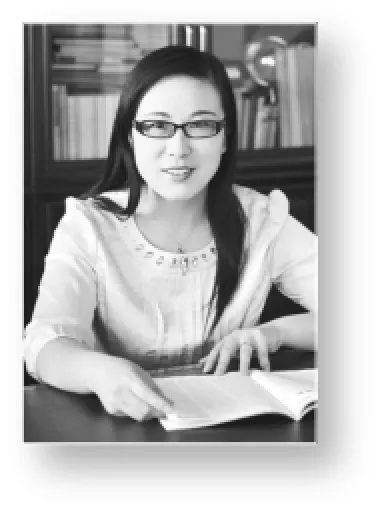
去外地公干,冷不丁被當地一個人問及你:“你們市那個叫李游的教授,熟嗎?”我沉吟了一下,說:“認識,不太熟。”
我沒有提及,我們之間曾發生過一件不太愉快的事。這么多年過去,那件事,我以為我已經忘掉它了;但是,當你的名字再度被人提起時,我才發現,我根本不可能忘掉它——它,已然刻在我骨頭上了。
那時,我正瘋狂地迷戀著寫作,發表了幾十篇文章。誰若贊美幾句我的文筆,就恨不能把心都剜給人家。某日,我的一位同事去你所在的高校辦事兒,負責蓋章的正是你(當時你還不是教授)。你看看我同事手里的材料,悠然道:“這章,我沒法蓋。”我同事好話說盡,就差獻上膝蓋了,但根本不奏效。就在我同事欲要絕望地離開時,你突然開口:“你是不是跟張麗鈞一個單位呀?”我同事以為絕處逢生,忙道:“是啊是啊!我倆關系特別鐵!”你說:“既然關系特別鐵,那我跟你說件事,你給評價一下?”我同事趕忙點頭,洗耳恭聽。你于是說:“張麗鈞的丈夫是個大才子,發表了好多詩歌,這你知道吧?”我同事忙說:“知道知道。”你話鋒一轉:“但據我所知,張麗鈞發表的那幾篇文章都是她丈夫幫她寫的。這事,你怎么看?”我同事一聽,驚呆了,說:“不可能!我親眼看到過她寫東西!”你用你那洞悉一切的眼睛斜睨著我同事,說:“喲,這就開始替張麗鈞辯護了?難道你不明白——越不會寫東西的人,越要在人前假裝會寫,當著你的面劃拉兩筆,讓你以為她真會寫——張麗鈞不是這樣的人嗎?我跟她丈夫認識。我一看那署名張麗鈞的文章,就斷定出自他丈夫的筆下!”……話不投機,我同事的事兒當然沒有辦成。回來后,她幾乎是哭著跟我講了她和你的這番對話。最后她說:“你回家告訴我姐夫,讓他跟那個叫李游的人絕交!”
回到家,我問丈夫:“李游這人怎樣?”他說:“挺好的呀!挺有正義感的一個哥們兒。——怎么想起問他?”我笑笑說:“沒事。”
多少次路過你的單位,第一個想到的竟不是供職于該單位的我的大學同學,而是你——“挺有正義感”的你!一萬遍重溫你與我同事的那番對話,一萬遍揣想你在使用某個極具殺傷力的詞時該搭配著怎樣的表情——鄙薄?厭棄?憤恚?不屑?有一次,我應邀去你的學校參觀一個畫展,居然有一種去找你的沖動,惡毒的臺詞都擬好了:“李先生究竟是我丈夫肚子里的哪條蛔蟲啊?”
慢慢地,日子被我過成了兩種——寫作的日子,不寫作的日子。隨著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擱筆的理由天天都來打劫我,不寫作的日子眼見得多起來。但是,只要一想到你的譏謗,我就不由自主地打一個激靈。我跟自己說:“嘿,你瞧你,分明是在朝著李游指的道兒跑啊!用不了多久,你就真會墮落到讓丈夫捉刀代筆的境地!哼哼,你就等著讓李游們罵死吧!”
我咬牙堅持寫作。應承下的約稿,熬到后半夜也要趕出來;同時開辟幾個專欄,出差時就在火車上用手機寫;做手術了,喘息掙扎著也要寫……我兒子評價我說:“媽,我發現你是個特別善于擠兌自己的人。”
現在,我老公已經很少寫作了,可我還在寫。我想,如果我真的有機會見到你,我大概會這樣說:李教授,謝謝你!當初,你我都未曾料及,你沒來由的一次鄙夷竟然有機會在日后發酵為“玉成”。你虛擬出的那個借丈夫的才華為自我臉上貼金的無恥女人,一直鞭捶著我、淬礪著我,促我拼命奔跑,遠離這種令人作嘔的丑陋。你賜給我一次次機緣,讓我欣悅地發現我生命的韌性,讓我奢侈地擁有甘心逐夢的充盈。你的“玉成”,是一件包裝難看的禮物,你讓接到這禮物的人驚喜地約見到了一個遠離怠惰平庸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