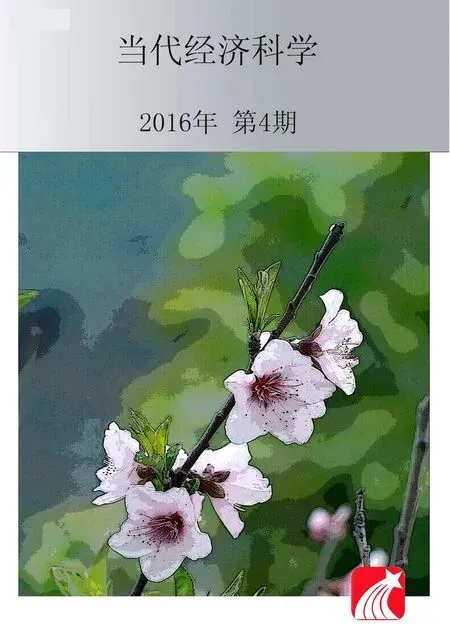回歸醫療服務本質:從“醫藥分開”看醫療服務供給
王文娟 ,南孟哲
(1.中央財經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 100081;2.中央財經大學 統計與數學學院,北京 100081)
?
回歸醫療服務本質:從“醫藥分開”看醫療服務供給
王文娟1,南孟哲2
(1.中央財經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 100081;2.中央財經大學 統計與數學學院,北京 100081)
本文在構建中介變量模型并實證分析“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影響的基礎上,研究了優化醫療服務供給的政策建議。研究發現,醫療服務供給中存在的問題源自兩個分離:一是醫方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分離;二是需求者與支付者角色的分離。前者解釋了效率不高的問題,后者解釋了費用較高的問題。進一步研究表明,優化醫療服務供給亟需回歸醫療服務本質:把握關鍵要素,將改善醫院和醫生收入作為突破口;樹立正確導向,將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作為長久之策;平衡各方利益,將財政補貼作為醫藥分開的主要手段;掃除制度障礙,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合約形式。
醫療服務本質;影響因素;醫藥分開;醫療服務供給
一、引 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逐步改善我國的公共服務供給。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11次提到“公共服務”,并提出“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共享發展理念,共享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同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出“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李克強總理為《經濟學人》撰文,指出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之一。2016年3月,“十三五”規劃強調“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增強政府職責,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一時間,“共享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社會政策托底”等成為公共服務供給研究領域的關鍵詞。
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醫療服務供給在“十二五”期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年末,醫療衛生機構數較2010年末增加5.3萬個,衛生機構床位數增加229.3萬張,衛生技術人員數增加215萬人,增幅分別達到5.7%、47.9%和36.6%;重大疾病防控、國民健康行動計劃、衛生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等持續推進;居民健康狀況繼續改善,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均提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然而,這些舉措與成就離“共享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一是醫療服務供給尚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所激發的醫療服務需求,供求之間缺口巨大,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仍是醫改的當務之急[1];二是資源配置扭曲導致了醫療服務市場的混亂,改革需要把輸出醫療資源的要素解放出來[2];三是公立醫院改革仍是醫改的重中之重,牽住公立醫院這個牛鼻子,把醫院創收的機制破除了,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3];四是改革涉及醫院內部的利益結構調整,更涉及整個醫療服務體系的人力資源配置制度變革[4]等等。針對這些延續性的問題,早在1997年國務院便開始主導“醫藥分開”;2002年國務院八部委聯合發文,提出“解決當前存在的‘以藥養醫’問題”;200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將破除“以藥養醫”作為關鍵環節,明確了“醫藥分開”的改革方向;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提出試點城市所有公立醫院“醫藥分開”。那么,經過近二十年的改革,“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解決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本文將通過考察“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剩余部分將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從理論上闡述“醫藥分開”、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因素及評價方式,以及“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第三部分構建模型并實證分析“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第四部分總結并提出優化我國醫療服務供給的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
(一)“醫藥分開”的本質與具體內容
“醫藥分開”的本質是從醫院、醫生兩個層面切斷其與藥品之間的利益聯系,做到公立醫院利益與藥品脫鉤、醫生利益與藥品脫鉤,公立醫院不依靠藥品收入來維持日常運行和發展,醫生不從開具處方的藥品中獲取直接的經濟利益[5]。“醫藥分開”的具體內容包含取消藥品加成和建立配套補償機制,其中建立補償機制包括增設醫事服務費和增加財政補貼兩個方面。因此,本文從取消藥品加成、增設醫事服務費、增加財政補貼三個方面討論“醫藥分開”政策:一是醫療費用中藥品所占比例過高是不爭的事實,取消藥品加成切斷了醫院藥品銷售收入的經濟利益,對控制醫療費用無序上漲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二是取消掛號費、增設醫事服務費,更加合理地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激勵醫務人員為患者提供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三是取消藥品加成對醫療機構收入帶來一定影響,醫院亟需補償以保證服務質量,而增加財政補貼是改革試點中普遍采用的補償措施。
(二)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因素及評價方式
影響醫療服務供給的因素主要包括投入產出因素、內部管理因素和外部政策因素[6]。投入產出因素上,郭曉日指出門診人均費用、出院者人均醫藥費用與醫院效率負相關,病床使用率、床日成本對醫院效率有積極影響[7]。戴平生指出個人衛生支出比例的提高傾向于增加衛生技術人員數、醫療機構床位冗余值,可能造成更多衛生資源的浪費[8]。內部管理因素上,卞鷹等研究發現獎金制度、人員聘任、競爭上崗、全員目標責任制的實施對醫院單元成本、住院日和DEA均有顯著作用[6]。Yasar A. Ozcan等指出營利性護理院效率比非營利性護理院效率高,大規模護理院比小規模護理院效率更高,控制規模和所有權不變,政府補助醫療保險計劃可以提高效率[9]。外部政策因素上,林皓等指出政府投入占醫院總支出比重下降、無法補償成本的情況下,醫院行為會發生扭曲,片面追求自身財務利益最大化[10]。Shen Yu-Chu通過研究美國來自預付費制度(PPS)和衛生維護組織(HMO)帶來的財政壓力,發現財政壓力對醫療質量有負面影響,這種影響在短期和中期尤為明顯[11]。Nikolaos Maniadakis等通過對英國90年代醫療內部市場化改革效果研究,指出內部市場化改革大大提升了醫療機構產能,但卻以質量降低作為了代價,旨在創造動機提高醫療服務供給效率的政策只對效率產生一次作用,而難以產生穩定的長期效應[12]。
關于醫療服務供給的評價方式,學界廣泛地應用DEA和SFA方法。Sherman首先將DEA方法應用于醫院效率的分析中[13],Wagstaff首先將SFA方法應用到健康醫療領域的效率測量中[14],兩種方法隨后被各個國家諸多學者廣泛應用。但是DEA方法和SFA方法都只是對醫療服務供給技術效率的評價,即對醫療機構自身投入產出的技術效率評價,欠缺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可及性、充足度以及配置效率等綜合的社會總效應的評價。Patrick M.Bernet從消費者視角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進行了隨機前沿分析,使用DEA方法同時評價了醫療服務供給的技術效率和可及性,結果表明資源供給的可及性對社會總效應有正向作用[15]。Gary D. Ferrier通過研究樣本醫院費用效率、技術效率、分配效率和規模效率,指出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低下都將導致費用的增加,造成浪費[16]。事實上,衛生經濟學一般選取四個效率評估指標:準入壁壘、技術效率、供給充足度、分配效率。準入壁壘指在接受醫療服務中遇到的障礙,比如價格、時間和交通因素;技術效率指在給定產出質量和數量的情況下以最小的費用來完成產出,一般用貨幣指標衡量;供給充足度指給定效率和質量要求,充足的醫療衛生服務資源的可利用性,主要依賴財政補貼實現;配置效率指給定的資本和勞動是否投入到社會上最有價值的地方,即資源利用是否達到帕累托有效,準入壁壘和不充足的資源供給都會制約分配效率[17]。
(三)“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
“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存在爭議。部分學者給出了積極的評價。YJ CHOU等通過總結臺灣“醫藥分開”改革經驗,指出“醫藥分開”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藥品支出并且影響醫生開方行為[18]。宋杰等通過研究北京試行醫藥分開改革對醫患雙方的影響,指出門診患者次均費用和次均藥費均大幅下降,患者滿意度提高,并且患者就醫更加理性,專家號需求下降,專家有更多時間和精力為患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19]。另一部分學者給出了更加審慎的評價。徐敢指出“醫藥分開”能直接產生使醫院用藥均衡數量下降的效果,但是對藥品價格虛高并未產生直接的效果[20]。李大平在分析藥價虛高成因時質疑“醫藥分開”的作用,指出供藥方和醫院的“變相協作”不能根本上切斷醫生處方與醫生經濟利益的關系,不能解決藥價虛高[21]。蔣建華指出藥品加成政策只是醫療費用高的表面原因,醫療費用高的真正原因是醫療系統的壟斷,降低醫療費用必須采取放松政府管制、引進民間資本、維護醫療市場秩序等綜合措施,政府取消醫院藥品加成政策、增加對醫院的補貼、增設藥事服務費的做法在降低醫療費用方面難以取得理想效果[22]。朱恒鵬指出不改革公立醫院的行政管理體制,不解決醫生的身份定位問題,無論是取消藥品行政定價,還是提高醫療服務價格,都無法徹底解決藥價高、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23]。
(四)醫療服務供給的優化路徑
一是政府主導的路徑,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財政補貼是促進醫療服務供給者與需求者有效交流的關鍵,消費由供給支付轉為需求支付、由隱性合同轉為顯性合同、由服務付費轉向風險分擔支付都能夠有效降低醫療費用[24]。曾雁冰指出加大政府對醫療服務的投入力度、提高業務收入收益率實現醫療費用的大幅度降低,可有效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25]。G.A.Melnick等通過對比加利福尼亞州與美國其他地區情況,指出政府規制的管理式醫療比競爭機制的管理更能夠改善醫療服務供給和規范醫生收入水平[26]。二是市場主導的路徑,詹國彬、王雁紅從英國NHS改革中得出啟示,醫療服務供給中引入市場競爭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主流趨勢,應倡導醫療服務中的顧客導向,提升醫療服務的回應性并追求顧客滿意[27]。陳釗等指出只有在醫療籌資市場化的同時實現醫療服務價格的市場化,才能徹底消除“以藥養醫”現象的同時緩解“看病難”與“看病貴”兩大矛盾,特別要在醫生的收入決定中充分引入競爭機制[28]。三是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路徑。周志忍指出政府責任市場化的傾向應予以校正,而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市場化改革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大力度;沒有管理制度和服務提供機制改革帶來的微觀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即使政府財政投入擴大數倍也不一定得到期望的結果,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公正問題[29]。王延中、馮立果指出政府“甩包袱”的市場化改革只能解決“寡”的問題,而不能解決“均”的問題,建議繼續市場化改革,但政府必須鼓勵醫療服務競爭、打擊壟斷、維護好市場秩序,并承擔起公共衛生和最低層次基本醫療服務的責任[30]。
通過以上理論分析,筆者認為:第一,當前對于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統性的總結,從而導致改革實踐中難以抓住關鍵影響因素并對癥下藥;第二,對提升醫療服務供給效率的策略缺乏動態研究,無論是政府主導、市場主導或者是兩者結合,都需要從動態的視角看,針對不同階段不同情況應有具體的政策引導;第三,研究提出的觀點缺乏針對性,部分研究指出提高政府補貼,卻沒有指明應該補貼給誰、以多大力度補貼;第四,缺少對醫院收入和醫生收入作用的研究,很多研究對醫院收入和醫生收入避而遠之,然而理順醫院和醫生收入是醫改的關鍵所在,醫院收入、醫生收入問題不可回避。因此,本文將引入醫院收入和醫生收入作為中介變量,從充足度、可及性、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四個維度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進行系統地研究,揭示“醫藥分開”政策的傳導機制,并結合我國醫療服務供給現狀,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三、模型設定與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如上文所述,為了揭示醫院收入和醫生收入在醫藥分開改革政策中的作用機制,本文參照Mark Pauly[31]、徐敢[20]等人的研究建立中介變量模型。用x1,x2,x3分別表示門診次均藥費,掛號費,財政衛生支出;m1,m2分別表示平均每所綜合醫院年收入和醫師年人均收入;y1,y2,y3,y4分別表示衛生總費用占GDP百分比,總診療人數,門診次均費用,病床使用率,依次建立回歸方程并建立結構方程組:
yj=πij+cxi+εij(i=1,2,3;j=1,2,3,4)
(1)
mk=πik+axi+εik(i=1,2,3;k=1,2)
(2)
yj=πijk+c′xi+bmk+εijk(i=1,2,3;j=1,2,3,4;k=1,2)
(3)
在回歸的基礎上檢驗系數、構造soble統計量,判斷y1,y2在結構方程組中的中介效應。
(二)實證分析
本文以2002—2012年為研究時間段,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研究使用SPSS17.0軟件進行外生潛變量、內生潛變量以及觀測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進一步對回歸系數進行sobel檢驗,研究統一選取90%的置信度對模型各項假設進行檢驗。同時,本研究使用Amos17.0軟件進行結構方程模型構建與分析。圖1顯示的是醫藥分開三個維度分別對醫院和醫生收入影響的標準化系數,以及醫院和醫生收入分別對醫療服務供給四個效率維度影響的標準化系數。


圖1 回歸的標準化系數
1.醫藥分開對醫院和醫生收入的影響。結果顯示,醫藥分開政策的三個構面對醫院收入和醫生收入均產生了顯著正效應。其中,門診次均藥費產生的影響最大,而財政衛生支出產生的影響效應最小。這與我國“以藥養醫”和財政衛生補助不足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在沒有實施“醫藥分開”政策的情況下,醫院和醫生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藥品收入,其次是掛號費,最后是財政衛生支出。此外,門診次均藥費、掛號費、財政衛生支出對醫院收入產生的影響比對醫生收入產生的影響大,這反映了我國公立醫院管辦不分、醫院收入捆綁醫生收入的現象。由于門診次均藥費對醫院收入產生的影響比對醫生收入產生的影響大,醫院因為取消藥品加成受到的損失將比醫生更大。同理,掛號費對醫院和醫生收入產生的影響比財政衛生支出產生的影響大,所以實施“醫藥分開”政策后,通過增設醫事服務費補貼醫院和醫生收入會比衛生財政補貼更有效。
2.醫院和醫生收入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結果顯示,醫院總收入和醫師年人均收入分別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四個維度的度量指標都產生了顯著正向效應。其中,醫院收入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充足度的影響比醫生收入更大,而醫生收入在可及性、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三維度的影響比醫院收入大。說明當前情況下,補貼醫生比補貼醫院更能夠提升配置效率,但不利于增加總供給和控制費用。
3.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結果顯示,醫藥分開政策的三個構面分別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的四個構面產生了顯著的間接正效應。具體而言,門診次均藥費、掛號費和財政衛生支出分別對醫療服務供給充足度、可及性、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均產生顯著影響。醫藥分開政策通過醫院和醫生收入的中介作用,產生的最顯著效應是總診療人數的變化,即改革最突出的效果是提升了可及性,“看病難”的問題將得以緩解。此外,綜合考慮財政衛生補助對醫院和醫生收入的影響,醫院和醫生收入對醫療服務供給充足度影響的乘數效應,相比補助醫生,補助醫院將對醫療服務供給充足度產生更顯著的效果。
4.醫院和醫生收入的中介效應。表1顯示的是醫院和醫生收入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結果表明醫院和醫生收入在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影響的部分維度下中介效應顯著。醫院收入(m1)和醫生收入(m2)在醫藥分開三個維度(x1,x2,x3)對醫療服務供給可及性即總診療人數(y2)的影響中均表現出顯著的中介效應。如果降低門診次均藥費,但醫事服務費和財政衛生補助沒有滿足醫院和醫生收入增長的訴求,總診療人數就不會按計劃調整,醫療服務供給的可及性也不會改善。此外,醫院和醫生收入(m1,m2)在財政衛生支出(x3)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四個維度(y1,y2,y3,y4)的影響中均表現出顯著中介效應。說明醫院和醫生受到有效的財政補助時,將對醫療服務供給產生顯著作用;否則,醫療供給主體(即醫院和醫生)就不能提供高效的醫療服務。另外,醫生收入(m2)在掛號費(x2)對醫療服務供給配置效率(y4)的影響中表現出完全中介效應,說明通過掛號費改革、增設醫事服務費可以提高醫生收入,從而使得醫生勞動力資源、醫療設備資源投入到更有價值的地方。

表1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同時,研究還發現,醫院收入(m1)在取消藥品加成(x1)和增設醫事服務費(x2)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充足度(y1)、技術效率(y3)、配置效率(y4)的影響路徑下中介效應并不顯著,醫生收入(m2)在取消藥品加成(x1)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充足度(y1)、技術效率(y3)、配置效率(y4),以及增設醫事服務費(x2)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充足度(y1)、技術效率(y3)的影響路徑下中介效應均不顯著。進一步說明,當前情況下,取消藥品加成和增設醫事服務費,對于改善醫院和醫生收入狀況,進而改善醫療服務供給的充足度、技術效率及配置效率的作用有限,現階段仍需維持和增加財政衛生支出。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理論和實證分析表明,增設醫事服務費等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的措施,相較財政補貼更有利于提升醫療服務供給效率;而現階段維持和增加財政補貼更有利于增加總供給和控制費用。此外,醫院和醫生收入對醫療服務供給效率有顯著影響,且在醫藥分開對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中的中介效應顯著;同時,對這兩個維度的研究表明,在當前歷史條件下,補貼醫生比補貼醫院更有利于提升配置效率,但不利于增加總供給和控制費用。本文認為,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結果,主要源自醫療服務供給中的兩個分離:一是醫方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分離;二是需求者與支付者角色的分離。前一個分離更多地表現為產權問題,是根本問題,解釋了效率不高的問題;后一個分離更多地表現為制度問題,是從屬問題,解釋了費用較高的問題。兩者分離的直接影響是增加了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
其中,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分離又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醫方掌握剩余控制權,而政府掌握剩余索取權;二是醫生掌握剩余控制權,而醫院掌握剩余索取權。這就是為什么醫院和醫生收入成為優化醫療服務供給的決定因素之一,而補貼醫生更有利于提升效率的原因所在。長期以來,醫療服務的行政定價,在限制醫院和醫生在醫療服務供給上的選擇的同時,具有對特定醫療服務供給的導向性。此外,醫生與醫院之間的聲譽機制和責任機制倒掛,行政手段建立的醫院聲譽耗散了醫生本身的聲譽,行政手段形成的醫院責任分散了醫生應當承擔的責任。醫生賴以謀求高收入的兩大重要因素——聲譽和責任,難以由自身掌控。然而,聲譽和責任必須依托具體的醫療服務,而醫療服務由醫生直接供給而非醫院。然而,醫院作為醫生群體的一個非人格化的“醫生”代表,承擔了為醫生謀求高收入、同時分散責任的角色;而作為醫院管理層,則通過掌握“渠道”獲得了相較其他醫生更高的收入。我們認為正是醫生這些以減少自身收入租值耗散為目的的不規范行為,造成了醫療服務行業、藥品行業不合理的資源配置[32]。
需求者和支付者角色的分離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醫保和政府補貼的支付功能;二是醫院本身的支付功能。而這也是為什么相較于增加財政衛生補貼,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更能夠提升醫院和醫生收入;而在當前條件下財政補貼仍是優化醫療服務供給的最有效方式的原因所在。醫保和政府補貼無疑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然而,其所具有的“花別人的錢為其他人辦事”的屬性,使其社會效益遠高于經濟效益。本文認為,提高社保和政府補貼的經濟效益,亟需實現醫療服務需求者與支付者的統一,即“花自己的錢為自己辦事”。因此,享受醫保和政府補貼的需求者,要么支付了相應的價格,要么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如排隊、接受公益性宣傳等。同時,政府應立足將這一支出項向收益項轉變,發揮社保和政府補貼人群巨大的優勢,開發其經濟價值,通過“交叉補貼”的方式,提高醫保和政府補貼的收益。此外,醫院本身所具有的支付功能,模糊了醫療責任應對的需求者和支付者。在醫療服務整體處于“經驗醫療”階段的歷史背景下,醫療責任應對的需求者和支付者應為醫生,通過行政手段將醫生捆綁在醫院,模糊了這一責任的歸屬,甚至使得醫療服務的需求者成為這一責任的承擔者之一。因此,引入第三方評估和保險主體,回歸醫療責任的本質屬性,對于發揮其在醫療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于此,本文認為,優化醫療服務供給亟需回歸醫療服務本質,彌補兩個分離。具體來說,就是要把握關鍵要素,堅持正確導向,平衡各方利益,掃除制度障礙。
一是把握關鍵要素,將改善醫院和醫生收入作為突破口。醫生收入分配制度影響整個醫療系統的績效。新醫改要從根本上瓦解“以藥養醫”,就需要將改善醫院和醫生收入作為醫改的重要目標之一。政府應逐步放開對醫療服務市場的管制,盡可能增加醫院和醫生的選擇,通過市場競爭機制、通過供需關系調節,將醫療服務價格、醫生收入與當地收入分配狀況相協調。參照發達及新興國家或地區的醫療服務價格水平和醫生收入水平,結合醫療服務在我國特定社會條件下的重要地位,劃定具有“底線公平”意義的階段性醫療服務水平,“底線”之上的部分,由醫院和醫生依據市場規律自行決定。此外,扭轉不合理的聲譽機制和責任機制。順應新的歷史發展潮流,尤其是“經驗醫療”向“精準醫療”的轉變、零邊際成本社會和共享經濟時代的到來,提升醫生在醫療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調動其維護聲譽、承擔責任的積極性,逐步提升醫生在剩余索取權上的優先性,從而改善醫生“減少人力資源使用”、“拓展人力資源使用”或者“轉讓人力資源使用”等不規范現象。
二是樹立正確導向,將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系作為長久之策。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雖然短期內會增加醫療費用,但從長期來看,將使價格維持在合理的均衡價格上。目前試點的掛號費改革、增設醫事服務費、藥事服務費等,本質是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的探索。在醫藥分開過程中,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將比財政補助更加有效地改善醫院和醫生收入。這些舉措,為提升醫院和醫生收入創造了有效條件。
三是平衡各方利益,將財政補貼作為醫藥分開的主要手段,且側重補貼醫療機構。政府投入不單單是投入,更為重要的是一種推進制度變革的杠桿[33]。醫藥分開政策實施之初,取消藥品加成將使醫院面臨比醫生更嚴重的收入虧損,會直接影響到醫院的正常經營,短期內財政衛生支出的補助對象應主要指向醫院而非醫生,從而首先解決醫療服務供給不足、供需缺口巨大的問題。但長期來說,當我國醫療服務市場成熟以及價格體系健全以后,財政衛生補助的對象應該轉移指向醫生。財政補助醫生能夠更有效地提升醫療衛生資源配置效率,在解決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的基礎上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四是掃除制度障礙,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合約形式。目前,醫方與政府之間、醫院與醫生之間存在諸如醫生編制問題、職稱評定問題、醫生自由執業問題,醫院與醫生間的聲譽機制與責任機制等,這些特定的形式,對醫院和醫生行為都產生了特定的導向。只有順應歷史條件、技術條件的發展,適時改變不合理的合約形式,為醫療服務供給的優化掃除制度障礙,才能更好地使全社會共享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成果。
[1]周其仁. 中國醫改的根本問題[J]. 中國醫院院長, 2011(21): 66-67.
[2]朱幼棣. 朱幼棣談中國醫改為什么這么難?[EB/O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xfe/2015/0311/122074.
html,2015-03-17.
[3]李玲. 2015兩會再談醫改,公立醫院才是醫改的牛鼻子[EB/OL]. http://www.guancha.cn/liling2/2015_03_04_311011.shtml,2015-03-04.
[4]朱恒鵬. 藥價降低七成,毋需財政掏錢[J]. 財新周刊,2015(23):34.
[5]王賢吉,付晨,金春林,等. 醫藥分開的內涵與實現途徑探討[J]. 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3(1):36-39.
[6]卞鷹,張錫云,葛人煒,等. 衛生經濟改革對醫院經濟效率影響研究[J]. 中國衛生資源,2001(4):153-156.
[7]郭曉日. 我國公立醫院效率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 山東:山東大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2012.
[8]戴生平. 醫療改革對我國衛生行業績效的影響——基于三階段DEA模型的實證分析[J]. 廈門大學學報,2011(6):97-103.
[9]Ozcan Y A, Wogen S E, Mau Li Wen.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skilled nursing facilities[J].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1998,22 (4):211-224.
[10]林皓,金祥榮. 政府投入與我國醫院效率的變化[J]. 經濟學家,2007(2):77-83.
[11]Shen Yuchu.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quality of care in hospitals[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3,22(2):243-269.
[12]Maniadakis N, Hollingsworth B, Thanassoulis 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l market on hospital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and service quality[J].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cience,1999,2(2):75-85.
[13]Sherman H D. Hospital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echnique[J]. Medical Care, 1984, 22(10): 922-938.
[14]Wagstaff A. Estimating efficiency in the hospital sector: a comparison of three statistical cost frontier models[J]. Applied Economics, 1989, 21(5): 659-672.
[15]Bernet P M, Moises J, Valdmanis V G. Social efficiency of hospital care delivery: frontier analysis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J]. Medical Care Research and Review, 2010,68(1): 36S-54S.
[16]Ferrier G D. Rural hospital performance and its correlates[J]. The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6, 7(1): 63-80.
[17] Feldstein P J. Health care economics [M].7th edition. New York, NY: Delmar Publishers Inc, 2011.
[18]Chou Y J, Yip Winnie C, Lee Cheng-Hua, et al. Impact of separating drug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on provider behavior: Taiwan’s experience[J].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03,18(3):316-329.
[19]宋杰,陳航,吳家鋒,等. 北京試行醫藥分開改革對醫患雙方的影響觀察[J]. 中國醫院管理,2013(9):3-5.
[20]徐敢. 公立醫院醫藥分開路徑和補償機制系統建模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學管理學院,2010 .
[21]李大平. 藥價虛高的成因分析與治理對策——質疑醫藥分開[J]. 衛生經濟研究,2011(4):584-585.
[22]蔣建華. 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對醫療費用的影響[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0(5):44-46.
[23]朱恒鵬. 取消以藥養醫能讓看病便宜嗎?[EB/OL].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5-25/100812288.html, 2015-05-25.
[2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system:improving performance[R]. Geneva,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25]曾雁冰. 基于系統動力學方法的醫療費用過快增長問題建模與控制研究[D]. 上海:復旦大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2011.
[26]Melnick G A, Zwanziger J. Stat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under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1980 through 1991[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5, 85(10):1391-6.
[27]詹國彬,王雁紅. 英國NHS改革對我國的啟示[J]. 南京社會科學, 2010(9):36-42.
[28]陳釗,劉曉峰,汪匯. 服務價格市場化: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未盡之路[J]. 管理世界, 2008(8):52-58.
[29]周志忍. 醫療服務市場化改革辯[N]. 健康報, 2007-04-05.
[30]王延中,馮立果. 中國醫療衛生改革何處去——“甩包袱”式市場化改革的資源集聚效應與改進[J]. 中國工業經濟, 2007(8):24-31.
[31]Pauly M, Redisch M. The not-for-profit hospital as a physician’s cooperative[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73,63(1):87-99.
[32]毛克宇. 醫療服務政府定價下醫生行為的經濟分析[J].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9(1):40-46.
[33]顧昕. 走向全民醫保:中國新醫改的戰略與戰術[M]. 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校對:李斌泉
2016-05-30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基于交易費用理論的我國醫藥衛生體制協同改革模式研究”(項目編號:71473284)。
王文娟(1965-),女,山西省大同市人,管理學博士,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公共衛生管理;南孟哲(1994-),女,陜西省富縣人,中央財經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學生,研究方向:數學與應用數學。
A
1002-2848-2016(04)-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