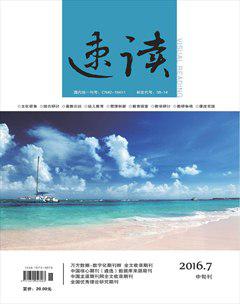論《一九八四》的陌生化藝術(shù)手法
摘 要:20世紀(jì)英國(guó)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創(chuàng)作的《一九八四》是典型的反烏托邦政治預(yù)言性小說(shuō),當(dāng)下較少有人從其藝術(shù)性出發(fā)對(duì)它進(jìn)行品評(píng)。而本文將從《一九八四》的藝術(shù)性入手,從“陌生化”的角度來(lái)研究《一九八四》的藝術(shù)手法,闡釋作者是如何運(yùn)用這種藝術(shù)手法來(lái)描繪在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下大洋國(guó)內(nèi)陰森恐怖的社會(huì)場(chǎng)景,如何將我們慣以為常的事物以全新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出來(lái),探究這種藝術(shù)手法在主題闡述、人物塑造和故事敘述等方面所發(fā)揮的獨(dú)特作用。
關(guān)鍵詞:《一九八四》;陌生化;奧威爾
“陌生化”是俄國(guó)形式主義者創(chuàng)造的一種很有價(jià)值的評(píng)論術(shù)語(yǔ),對(duì)文學(xué)理論有很大的意義。文學(xué)作品中運(yùn)用“陌生化”手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讓人們?cè)陂喿x的過(guò)程中獲得煥然一新的審美體驗(yàn),而這就需要以陌生的方式來(lái)表現(xiàn)人們?cè)緦乙?jiàn)不鮮的事物。在《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大量使用了“陌生化”的藝術(shù)手法,但他并沒(méi)有一味強(qiáng)調(diào)形式,而是以此來(lái)突顯作品的主題思想,映襯與之相隨的故事內(nèi)容,他巧妙地在小說(shuō)的敘事視角、敘事手法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融入了陌生化,下面我就從這三個(gè)方面來(lái)具體分析《一九八四》的“藝術(shù)性”。
一、小說(shuō)的陌生化敘事視角
首先來(lái)說(shuō)小說(shuō)中敘述視角的陌生化。選擇怎樣的視角來(lái)敘述文本內(nèi)容無(wú)疑影響著作品的敘事傾向、文字風(fēng)格以及人物形象,而不斷變化的或者是獨(dú)特的視角則會(huì)更新我們對(duì)很多慣有事物的認(rèn)識(shí),讓我們從陳舊的生活和世界之中脫離出來(lái),再一次觀(guān)察我們習(xí)以為常的事物,得到新的發(fā)現(xiàn)和體驗(yàn)。《一九八四》中,在全知視角的主旋律之中作者有意穿插了有限多變的第三人稱(chēng)有限視角,使小說(shuō)中的一些事物以第一次出現(xiàn)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溫斯頓的視角正是第三人稱(chēng)有限視角在小說(shuō)中的具體運(yùn)用。在這里“作者放棄了第三人稱(chēng)可以無(wú)所不在的自由,實(shí)際上退縮到了一個(gè)固定的焦點(diǎn)上”。讀者跟隨溫斯頓的視角,感受著大洋國(guó)虛無(wú)的過(guò)去,荒誕的現(xiàn)在,審視著讓人不寒而栗的內(nèi)黨,而小說(shuō)中敘述視角從“全知”轉(zhuǎn)為“有限”也實(shí)現(xiàn)了“陌生化”場(chǎng)景的呈現(xiàn),借助溫斯頓的視角,未來(lái)國(guó)度中陌生卻又熟悉的事物才得以蒙上一層面紗,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小說(shuō)中多處使用了第三人稱(chēng)有限視角,比如其中對(duì)紅葡萄酒的描寫(xiě):“奧博良把酒拿了過(guò)來(lái),在玻璃杯中倒了一種深紅色的液體……從上面看下去,那幾乎是黑色的,但在酒杯里卻亮晶晶地像紅寶石。它有一種又酸又甜的氣味。”再如小說(shuō)中對(duì)于裘莉亞化妝的描寫(xiě):“她的變化比赤身裸體還使他驚奇……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驚人。這里抹些紅,那里涂些白,她不僅好看多了,而且更加女性化了。”以及對(duì)白砂糖的描寫(xiě):“她遞給溫斯頓的第一個(gè)紙包給他一種奇怪而又熟悉的感覺(jué)。里面始終沉甸甸的細(xì)沙一樣的東西,你一捏,它就陷了進(jìn)去。”
這種陌生化描述實(shí)際上正是借助敘述視角的轉(zhuǎn)移而得以實(shí)現(xiàn)的,這幾段話(huà)看似用的是全知全能的視角,但中間卻穿插著溫斯頓自己對(duì)于葡萄酒、化妝以及白砂糖的感受和描述。也就是說(shuō)奧威爾在這里通過(guò)第三人稱(chēng)有限視角,把人們常見(jiàn)的事物陌生化,使讀者以初見(jiàn)此物的心態(tài)去觀(guān)察它們,從而打破慣有的認(rèn)知模式,獲得一種新的審美體驗(yàn)。所以以“陌生化”的視角描繪事物,使事物不以常態(tài)示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讀者閱讀感受的難度,延長(zhǎng)審美欣賞的時(shí)長(zhǎng),從而產(chǎn)生特別的審美情趣。
二、小說(shuō)的陌生化敘述手法
接著來(lái)說(shuō)小說(shuō)敘述手法的陌生化。在《一九八四》中,作者并沒(méi)有直接拋出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而是通過(guò)象征來(lái)喻示作品的主題意義和自己的觀(guān)點(diǎn)。可以說(shuō)“奧威爾是通過(guò)激發(fā)、修改和重組讀者有意識(shí)或無(wú)意識(shí)中業(yè)已熟知的意象來(lái)構(gòu)想未來(lái)的。”奧威爾對(duì)小說(shuō)中多元意象的陌生化處理,使大洋國(guó)中極權(quán)主義對(duì)人的壓迫和對(duì)客觀(guān)現(xiàn)實(shí)的歪曲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靜脈曲張”這一象征著自由的意象。
一開(kāi)始溫斯頓的身體狀況并不是很好,靜脈曲張潰瘍總是很癢,讓人煎熬,而這跟他的自由程度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此時(shí)的他還沒(méi)有遇到裘莉亞,所以面對(duì)混亂無(wú)望的生活,內(nèi)心苦悶而無(wú)處傾訴,只能通過(guò)日記來(lái)排解,而這并不能在實(shí)際意義上改變什么,反而讓他因?yàn)槿沼浱嵝牡跄懀卤凰枷刖彀l(fā)現(xiàn)而招致自身的毀滅。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裘莉亞的出現(xiàn),裘莉亞進(jìn)入他的生活,讓他在生理和心理上積壓著的苦悶都得以釋放,當(dāng)他以擁有愛(ài)情的方式來(lái)私下反抗黨的統(tǒng)治時(shí),他的反抗從只敢寫(xiě)日記上升到了實(shí)際行動(dòng),個(gè)人自由程度無(wú)疑擴(kuò)大了,而此時(shí)象征著他自身自由程度的靜脈曲張潰瘍也逐漸好轉(zhuǎn)了,內(nèi)心的愉悅以及情感生活的相對(duì)自由使“他長(zhǎng)胖了,靜脈曲張潰瘍消退,只是在腳踝上方的皮膚上留下一塊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但當(dāng)他被思想警察逮捕并不斷地拷打、審訊,進(jìn)行肉體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毀時(shí),他再一次失去了作為一個(gè)真實(shí)存在的人的自由,他的精神已處于崩潰的邊緣,而隨著自由被逐漸剝奪,他的靜脈曲張潰瘍也再次惡化“腳踝上的靜脈曲張已潰瘍成一片,皮膚一層一層掉下來(lái)。”
“靜脈曲張”這一特殊的意象總是在溫斯頓的生活發(fā)生某些質(zhì)的變化時(shí)出現(xiàn),它的不斷變化不僅反映了溫斯頓生理的狀況,同時(shí)也喻示著不同時(shí)期溫斯頓個(gè)人自由的不同程度。當(dāng)權(quán)利的化身“老大哥”或者“黨”不斷侵入個(gè)人生活時(shí),靜脈曲張潰瘍作為溫斯頓身體病理組織的一部分充分喻示著極權(quán)主義所帶給他的切膚之痛。奧威爾用陌生化的方式處理這一意象,使它變得詭譎而特殊,不僅昭示著溫斯頓內(nèi)心的發(fā)展,也象征著自由被不斷消解,奴役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三、小說(shuō)的陌生化人物形象
人物可以說(shuō)是小說(shuō)故事起因以及情節(jié)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因,而人物的形象、性格以及最終的命運(yùn)在一定程度上投射著作品的主題思想以及作者對(duì)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評(píng)價(jià)。《一九八四》中的人物不同于以往反烏托邦中的扁平人物,他們的性格被有意塑造成符合故事背景卻又反常于人們的期待和想象。就拿主人公溫斯頓來(lái)說(shuō),他的形象以及命運(yùn)就無(wú)疑偏離了我們對(duì)主人公形象的期待。
溫斯頓就是一個(gè)普通的外圍黨員,唯一特別的就是他因?yàn)槿藗儗?duì)黨的無(wú)條件擁護(hù)、對(duì)于虛假敵人的狂熱以及物質(zhì)生活的困窘,而產(chǎn)生的對(duì)黨、對(duì)“老大哥”的一系列的質(zhì)疑。他想要追求精神的自由,保持思想的獨(dú)立,但在日夜被監(jiān)視的環(huán)境下他只能從行為到面部表情都偽裝自己,并參與到其中,他是精神的反抗者,同時(shí)也是懦弱的附和者。而且,溫斯頓也沒(méi)有一個(gè)可以做出反抗行為的健壯身軀,靜脈曲張的潰瘍、早起的咳嗽、蒼白消瘦的身體,以及最后當(dāng)他遭受了身體和精神的百般折磨后的腐爛的身軀,讓他的形象再一次偏離了人們所期望的救世主式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溫斯頓的性格也是英雄人物的異化。一方面他有著強(qiáng)烈的反抗意識(shí),可另一方面他又在極權(quán)主義的體制中享受著工作的樂(lè)趣。“工作是溫斯頓生活中最大的樂(lè)趣……你一鉆進(jìn)去就會(huì)忘掉自己……這是一些細(xì)膩微妙的偽造工作……溫斯頓擅長(zhǎng)于這樣一類(lèi)的工作。”他在認(rèn)識(shí)到黨在不斷篡改歷史抹殺過(guò)去的同時(shí),也樂(lè)此不疲地參與著謊言的編織,他的行為實(shí)際上推動(dòng)了他所憎惡的極權(quán)主義社會(huì)的運(yùn)轉(zhuǎn),而且他有時(shí)甚至沉迷于其中無(wú)法自拔,所以即便他知道了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下的政治體制是靠哪些手段在維持,他也并不能做出什么有效的反抗行動(dòng)。
由此可見(jiàn),溫斯頓完全是一個(gè)負(fù)面的英雄形象,在精神和肉體上存在著許多不足的他,僅僅靠思想的背離和利用性愛(ài)放縱本能來(lái)反抗極權(quán)統(tǒng)治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事實(shí)也證明溫斯頓的反抗不僅沒(méi)有改變什么,反而讓自己走向了肉體的衰敗消亡,以及思想和靈魂的徹底毀滅。透過(guò)溫斯頓的反英雄形象及他的悲劇命運(yùn),極權(quán)主義社會(huì)對(duì)個(gè)體生命的異化扭曲展露無(wú)遺。
《一九八四》借用“陌生化”這種藝術(shù)手法表達(dá)了反對(duì)極權(quán)主義統(tǒng)治的政治觀(guān)點(diǎn),但很顯然奧威爾并沒(méi)有將藝術(shù)和政治分離開(kāi)來(lái),而是將它們統(tǒng)一于自己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之中。奧威爾認(rèn)為“你對(duì)自己的政治傾向越是有明確意識(shí),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動(dòng)而不犧牲自己的審美和思想上的獨(dú)立完整。”任何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都無(wú)法擺脫審美的因素,他想要做的就是讓政治寫(xiě)作成為一種藝術(shù)。《一九八四》的藝術(shù)性雖非光彩奪目,但是在用陌生化理論對(duì)它進(jìn)行細(xì)化分析后可以發(fā)現(xiàn),小說(shuō)的政治內(nèi)容正是以藝術(shù)手法為載體才得以呈現(xiàn),所以說(shuō)奧威爾在創(chuàng)作的過(guò)程中所采用的“陌生化”藝術(shù)手法使作品在片段化的場(chǎng)景展示中深化了思想主題,從而讓作品具有了高度的可讀性,讓我們看到了在作品主題之外的《一九八四》的審美價(jià)值和藝術(shù)魅力。
參考文獻(xiàn):
[1]童慶炳.《文學(xué)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英]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M].董樂(lè)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3][英]戴維·洛奇.《小說(shuō)的藝術(shù)》[M].王峻巖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4][英]喬治·奧威爾.《我為什么要寫(xiě)作》[M].董樂(lè)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作者簡(jiǎn)介:
王囡囡(1993.09~ ),女,陜西省綏德人,西安市長(zhǎng)安區(qū)陜西師范大學(xué),課程與教學(xué)論(語(yǔ)文),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