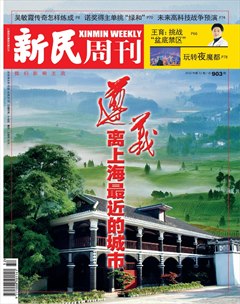魔都教育節奏對接小縣城
黃祺
上海基礎教育的高水平,近年來在西方國家教育界聲名鵲起,通過PISA測試等一系列國際公認的學生素質測試,西方教育界同行驚訝地發現,上海基礎教育體系培養的學生,各方面綜合能力都要高于其他國家。為此,英國教育部門今年宣布,全國約8000所小學將采用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學生學習數學的方法。
連英國都要學習上海教育,中國內地更是對上海基礎教育之計“求技若渴”。在中央要求上海對口幫扶遵義的大背景下,2013年11月,上海市教委與遵義市教育局簽訂《2013-2015教育對口幫扶協議》。此后,上海市楊浦區教育局和普陀區教育局,分別組織區內優秀教師團隊到遵義支教,楊浦區更是分批派出教師和管理人員共45人,以接力的方式駐扎遵義三年。
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遵義,城鄉差別大,城鄉之間教育水平的差別也很大。上海教師們沒有選擇留在遵義市區,而是投入到教育更為落后的縣級中小學,為帶動最基層教育機構的教學水平改善而努力。
“精準扶貧、按需援教”,是上海教育援教工作堅持的方向。3年來,上海市先后投入幫扶資金5800余萬元,實施教育幫扶項目53個;通過“金種子”培養計劃等分批選拔上百名校長前往上海掛職學習;同時,“百名上海名師遵義行”項目派出專家到遵義講課指導,拓寬當地教師的視野,提升當地教學理念。
當魔都教育節奏遭遇小縣城,當上海教師來到縣城中小學,會發生怎樣神奇的改變?記者近期對支教回滬不久的上海教師們,進行了深入的采訪。
改變,從40分鐘開始
從遵義回到上海已經半年,上海市黃興學校語文教師茹佳,還常常牽掛著她曾支教的學校——貴州省遵義市正安七中,記掛著她在那里帶的“徒弟”,記掛著那里的學生們。這個暑假,茹佳的微信上收到正安七中老師發來的喜報:正安七中今年中考成績位列全縣第一名。三年前,這所中學中考成績,在全縣排第九。
成績的改變,是最直觀的指標,上海支教教師們知道,因為他們的努力,一些更深層次的改變,也已經發生。
正安縣距離遵義市160公里,車程2個半小時,是遵義市相對比較落后的一個縣。縣城很小,“從東到西6000步,我數過”,茹佳說。正安七中,是一所位于縣城邊緣的中學,留守兒童比較多,教學質量在縣城里多年來處于下游。
“當地的教學方式,還在用上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方式。”這是到遵義支教的上海教師的普遍感受。支教老師們首先想改變,正是課堂。
茹佳老師到正安七中后,先花了兩周的聽課調研,她發現,當地老師各有優點,但習慣單打獨斗,互相溝通較少,資源整合較少。特別是作文課,因為超大的班額,作文批改也成為難題。有時候花了很大的力氣批改了,學生卻不明白老師評語的意思,有的明白了卻也不知如何修改和進步。“所以作文教學幾乎是一個低效的教育空白。”
梳理了問題后,她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給學生上課。“我結合當地教材中一篇《周莊水韻》進行了作文示范課的指導。在聽一位老師上這節課的時候我發現,貴州的孩子們對遙遠的江南水鄉沒有什么概念,只覺得文字美,卻不能有更深層次的感受。我就想換一種思路,通過美文的欣賞,寫屬于自己的生活。用文字來愛家鄉。”
茹佳喜歡攝影,她在宿舍樓窗口拍攝了一段雨中學校操場的視頻,學生們看后,感慨原來自己的學校也有如此美景。有了情感的共鳴與鋪墊,茹佳老師就地取材,讓學生對照著課文,從欣賞文字中的江南雨景,延伸到描寫自己身邊的雨景。“一堂景物描寫的習作課,讓孩子們有內容可以寫,不害怕寫作文,甚至有信心主動去記錄生活的片段,是老師最欣慰的時刻。”茹佳說。
茹佳還給學生展示了自己寫下的關于雨的日記片段,學生們踴躍地點評,這樣的場景,讓當地聽課老師們得到了啟發。
上海市普陀區洛川學校數學教師徐志平,支教的學校是習水縣金州實驗小學。與上海小學普遍二三十人的情況不同,在遵義,縣一級學校大多規模大,每一班的學生數量也多達五六十人。客觀和主觀的因素,導致這些學校沿用老式的教學方式,至今沒有改變。
徐志平告訴記者,上海的小學數學課,要求每堂課給學生做十多道練習題,讓學生在練習、討論的過程中掌握數學知識。而他支教的學校,數學老師只能保證一堂課三四道習題,老師讓學生舉手到黑板上做題,做不到每個學生都得到練習。
到金州實驗小學多次聽課后,徐志平向當地教師提出,可以試一試多給學生練習,讓學生自己探討,而當地教師的反應是:“學生能行嗎?”
為了打消教師們的顧慮,徐志平用上海數學課的上法給金州試驗小學的學生上數學課,幾次課下來,當地教師不得不折服。“徐老師帶來教學方法和思路,讓人耳目一新。”當地教了10多年數學老師,感慨道。
英語課,可以說是讓上海教師們感覺反差最大的一個學科,也是水平提升比較難的學科,這一點,同濟小學英語教師佘毓菁深有感受。佘毓菁支教的是湄潭縣湄江四小,剛到學校,佘老師發現,當地教學與上海最大的不同,是教師不太關注學生對語言的運用,機械式地講課。針對這個問題,佘毓菁帶著自己的“徒弟”,手把手地教他們備課、上課,她希望,從培養當地骨干教師入手,讓“徒弟”先學習上海的英語教學方式,然后再讓他們去影響帶動其他老師。
理念幫扶,知難而進
大多數援黔上海教師,是第一次到遵義,也是第一次到教育落后地區的基層學校支教。去之前,教師們想象中的困難,與真實遇到的困難,有一定的差距。
普陀區教育局派出的李允翔、徐志平、戴繼鴻三位教師,被分配到遵義市習水縣的兩所學校和遠程教育中心支教。出發前,三人的行囊頗為豐富,被子、床單、枕頭都帶上了,“以為要住茅草屋呢”,老師們玩笑道。
到了習水縣,上海老師們看到,當地學校硬件設施不差,除了經常停水停電,生活條件也還算不錯。真正的差距,是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上,而上海基礎教育水平的領先,也在于理念和方法上。
李允翔是普陀區曹楊二中附屬學校辦公室主任、語文教師,作為管理人員到習水縣習水七中掛職副校長。剛到學校,李允翔幾乎天天聽課,有時候在一間教室里能坐一天。在看到理念和方法上的差距后,他開始試圖用講座、教研討論這樣的方式,將上海的教育理念傳遞給當地教師。
示范課上了一堂又一堂,講座一場又一場,教研討論一次又一次,但上海老師們發現,當地教師的教學方式,改變卻并不大。雄心受挫,李允翔反省,這種“理念對理念”的方式,行不通。李允翔開始另一個實驗:在習水七中開展教學改革,讓參與的教師自己體驗教學方法改變帶來的好處。
在當地學校領導的支持下,李允翔開始制定教學改革計劃,招募愿意參加的教師加入。教學改革涉及到從設置主題、備課到質量考核的整個過程,參加的老師要按照改革要求備課、上課。要參加改革,勢必增加工作量,挑戰大,難度也大。讓李允翔感到慶幸的是,他的改革計劃沒有碰壁,30多位教師加入了他的改革計劃。
盡管時間不長,無法得到直觀的改革成果,但李允翔欣喜地看到,當地教師愿意嘗試改變教學方式,開始從滿堂灌轉變為更關注學生的反應,敢于讓學生發言,讓學生討論。這些看起來細微的變化,正是現代教育的精髓。李允翔相信,上海教師為當地開了頭,教育改革的火種就有了延續下去的可能。
教育幫扶,也要精細化
“一開始接到任務時,我們是有顧慮的。楊浦區教育系統如果要承接幫扶任務,就要做好,要做好,就有壓力、有挑戰。”楊浦區教育局副局長吳巍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從接過任務開始,楊浦區教育局就對對口幫扶遵義進行了三年規劃,為此建立了有200多名優秀教師和管理人才的后備人才庫,除了派人到遵義,還為支教學校確定了上海的對口學校作為后方支持,鞍山實驗中學、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楊浦職業技術學校、復旦實驗中學都分別結對共建了遵義當地學校。也就是說,楊浦區不僅僅是派人對一個學校支教,而是讓上海的一所學校對口遵義一所學校支教。
吳巍介紹,楊浦區對口幫扶遵義市湄潭縣、道真縣、正安縣的一所小學和兩所中學,派出的支教隊員中,管理人員在上海都是學校校長,到支教學校任副校長,任期一年,教師則每批任期半年。
第一批支教隊,首先對支教學校以及區域的整體教育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研,找出當地急需和欠缺的地方,針對性地擬定幫扶計劃。第一批支教隊隊長、國和小學校長倪曉燕,到湄潭縣湄江四小當副校長。經過對當地辦學、師資、學生來源、信息化等方面的調研,倪曉燕發現,當地太需要信息化投入,雖然學校在信息化方面有一定的基礎設施,但網絡條件、操作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問題。
針對當地的情況,楊浦區教育局圍繞信息化建設,為三所學校建立完善了遠程錄播教室,為此投入專項資金100多萬元。有了遠程教室,上海支教隊還手把手交當地老師使用、維護設備,與上海的共建學校開展遠程教學活動。
上海支教教師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幫扶地區師資力量薄弱,但當地教師有很強的學習欲望,都希望能多學一點上海經驗和上海做法。了解到這些需求,楊浦區共建學校為遵義教師提供了到上海進修培訓的機會。鞍山實驗中學校長邵世開介紹,3年來,已經有60多名來自遵義市道真縣玉溪中學的老師到上海進行為期一周的浸潤式學習。如果光從學校規模和硬件設施講,鞍山實驗中學并沒有比遵義的學校好多少,但邵世開認為,這樣的辦學條件反而更容易給遵義的教師們帶來啟發。“為什么硬件條件差別不大,辦學質量卻差距很大?我們希望讓遵義的老師們知道,好學校并不是說硬件好就行,要構件適合學生的教育體系,學校教育要與當地社會環境、師資條件相適應。”
3年的幫扶,改變正在發生。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校長丁利民告訴記者,結對共建的湄潭縣湄江四小校長剛到上海進修時,問不出什么問題,等進修快要結束時,校長問了一連串關于課程建設的問題。
影響當地教育生態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程,3年時間對于教育事業的發展來說很短,不過,上海基礎教育系統對口幫扶的地區,在教育生態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遵義教師的眼中,上海教育一個最大的特色,是“魔都節奏”。到上海的學校進修,遵義的教師問:為什么女教師都穿平底鞋?丁利民回答:上海教師每天在學校里走動比較多,站立時間長,老師們只能穿平底鞋。上海對口幫扶的中小學,原本教師不用坐班,但受上海支教隊影響,一些學校也開始實行坐班制,教師們利用在學校的時間,開展起了各種教研活動。
佘毓菁說,在她支教的湄江四小,她幾次被管辦公樓的大爺鎖在樓里,大爺沒想到,晚上六七點鐘,還有老師在辦公室工作。佘毓菁帶著“徒弟”加班備課、研究教案,后來這兩位“徒弟”的示范課,讓當地同行刮目相看。
除了在對口幫扶學校工作,上海支教隊還經常下鄉支教,輻射周邊鄉鎮學校,將上海教育理念帶到更廣的地區。
除了教學本身,上海支教老師還關注到學生的心理健康。
楊浦區第三批支教隊隊長、建設初級中學校長虞永超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道真縣玉溪中學,有300多名留守兒童,這些住校生,長期缺少家庭關懷。首批來到此支教的“上海老師”,在調研后建起了留守兒童“愛心驛站”。
“愛心驛站”每年確定30個左右的學生進行重點幫扶,每天晚上6點15分到7點,為留守兒童輔導學業,答疑解惑,談心疏導,點亮心燈。“‘愛心驛站建立后,通過前后兩批援助教師的努力,這批學生精神面貌有了明顯提升,學習成績提高也很快。”玉溪中學校長韓峰說。
盡管在遵義支教的生活辛苦,但從遵義回到上海的支教老師們,最愿意談論的還是對當地教師的理解和尊重。楊浦區第二批支教隊隊長、開魯新村第二小學校長丁建萍告訴記者,當地教師除了教學,還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有一個小孩,父母在外打工,晚上一個人溜出學校,躲在工地。老師們大半夜到處找,直到把小孩找回來。”丁建萍說,當地教師堅守在這個崗位上,付出更多,犧牲更多,讓上海教師們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