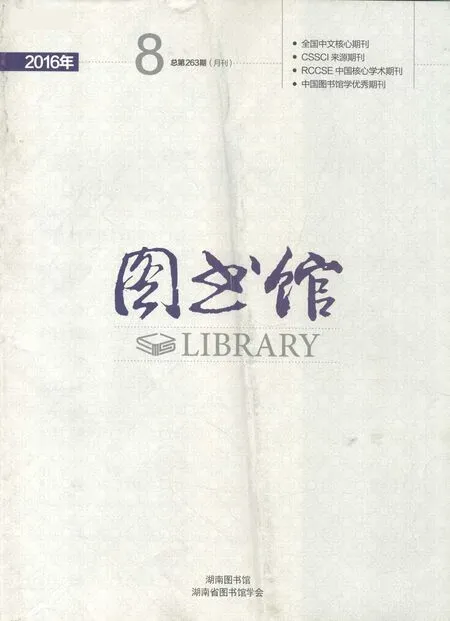近代城市圖書館事業發展述評
——以武漢為中心
耿 達 傅才武(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武漢 430072)
·學術論壇·
近代城市圖書館事業發展述評
——以武漢為中心
耿達傅才武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武漢430072)
近代中國城市圖書館事業取得了不錯的發展,特別是在1927-1937的“黃金十年”,城市圖書館事業發展迅猛。武漢三鎮的圖書館種類多樣、分布均衡、覆蓋面廣、管理明晰、服務周全,影響波及全省乃至全國。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圖書館不僅影響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對近代城市的發展轉型具有重要作用。
圖書館場館建設管理體制服務舉措
〔引用本文格式〕耿達,傅才武.近代城市圖書館事業發展述評——以武漢為中心[J].圖書館,2016(8):42-48
圖書館是城市發展的文化名片,圖書館事業是近代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內容。作為近代中國“交通文軌”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武漢的圖書館事業也取得了不錯的發展。雖然學界關于圖書館事業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但關于武漢圖書館事業的研究甚少,且以單個場館的研究為主,缺乏區域化的整體眼光。鑒于此,文章根據相關檔案、報刊、文獻資料,以武漢三鎮為研究地域,以1904年武漢第一座圖書館的建立為時間起點,1949年為時間結點,通過這一時間段對武漢圖書館事業的考察,以了解近代城市圖書館在場館建設、管理體制和服務舉措方面的具體情況。
1 場館建設
“西學東漸”與政府推動社會教育這兩種合力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國圖書館的產生與發展。武漢是近代中國較早實行對外開埠通商(1861漢口)和開展洋務運動(張之洞主持湖北“新政”)的內陸地區,工商業發展基礎較好,文教事業也打開了局面。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大力推行社會教育,圖書館事業作為社會教育的一環,發展開始加速。據統計1911年底湖北的通俗圖書館達到44個,藏書18000部,每日平均閱覽人數達到1800人,1處每日讀者約600人[1]。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政治相對穩定,社會經濟恢復發展,1927-1937年是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時期。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民國十九年(1930)統計資料顯示,這一時期有普通圖書館903所、專門圖書館58所、民眾圖書館575所、社教機關附設圖書館331所、專業團體附設圖書館107所、書報處(內含巡行文庫)259所、學校圖書館654所、私人藏書樓8所,總計2935所,尤其重要的是,公共圖書館已達2068所(包括普通圖書館、民眾圖書館、社教機關附設圖書館和書報處),占當時全部圖書館數量的70%[2]。1933年教育部調查各省市已設立之各類圖書館(除西康、新疆尚未填報外),就已經呈報之26省市統計出普通、專門、學校、民眾、流通、機關、私家七類圖書館總計2840所,其中湖北省有普通圖書館7所、專門圖書館1所、學校圖書館207所、民眾圖書館37所、機關圖書館8所,總計有各類圖書館260所,占全國圖書館總數的9.15%[3]。1936年,教育部根據各省市教育廳教育局及其他設有圖書館之機關所填報調查表,并參以舊檔案及其他有關圖書館之出版物,經詳加整理,編成《全國公私立圖書館一覽表》,所收錄的公私圖書館達到4032個[4]。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圖書館運動”遍及全國各地,武漢地區在圖書館建設方面一直處于全省全國前列。武漢地區第一座近代公共圖書館肇始于1904年建立的湖北省圖書館,此后,武漢地區圖書館事業發展方興未艾。根據1936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印制的《全國公私立圖書館一覽表》,統計出湖北省有各類圖書館共291個,其中普通圖書館7個、專門圖書館1個、學校圖書館221個、民眾圖書館43個、流通圖書館4個、機關圖書館12個、私家圖書館3個;而武漢的各類圖書館達到168個,占湖北全省圖書館總數的57.73%,其中武漢有省立圖書館1個、公立圖書館1個、私立圖書館1個、附設圖書館165個(包括學校圖書館151、機關圖書館8個、民眾圖書館5個、專門圖書館1個)。
武漢的圖書館具體區域分布為武昌共有圖書館83個、漢口共有圖書館78個、漢陽共有圖書館7個。從武漢這168個圖書館建立的時間來看(有7個館建立時間缺失),1911年前建立的圖書館1個、1911年—1926年建立的圖書館9個、1927年—1936年建立的圖書館151個。民國黃金十年間武漢的圖書館發展迅猛,建立的圖書館數占武漢所建總數的93%,其中1932到1934年3年中建立的圖書館達92個,僅1934年就建有47個,達到民國時期武漢圖書館建設的峰值。

表1 1933年、1935年湖北圖書館數占全國圖書館數比例[3]

表2 1936年武漢圖書館數占湖北圖書館數比例[5]

表3 1904年-1936年武漢圖書館建立情況[5]
抗日戰爭初期,武漢一度成為戰時首都,抗戰書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各種深受民眾歡迎的小型書刊閱覽室、圖書館應運而生。如由滬遷漢的“量才圖書館”,在重新購置書刊后,于1938年1月正式向民眾開放,還組織社會力量,推動戰時社會教育,鼓舞廣大民眾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職業青年抗日團體螞蟻社成立“螞蟻圖書館”,首創無條件借閱辦法。青年救國團的“青救圖書室”、婦女生活雜志社的“婦女圖書室”都相繼在漢設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聚集武漢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武漢三鎮的學校、傷兵醫院、大街小巷成立20多個“救亡圖書室”,及時為各界民眾提供精神食糧。武漢淪陷后,漢口市立圖書館建立,但規模甚小,至1946年武漢光復后,漢口市政府接收并正式創建漢口市立圖書館[6]。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使民國黃金十年興起的圖書館事業在戰火中受到嚴重損失。據有關資料統計,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共損失圖書館2118所,損失藏書總數在1000萬冊以上[7]。1938年,戰火逼近武漢,湖北省立圖書館將館藏圖書裝成170箱經宜昌運至秭歸、恩施。
戰爭使近代武漢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遭受巨大挫折。抗戰勝利后,漢口市立圖書館的籌備和建立是武漢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工程。龔孟賢任館長后,“增加工作人員,積極推動業務,整理原有圖書、儀器、標本,并增購一般書刊及中外報紙,一俟布置就緒,即行開始閱覽”[8]。漢口市立圖書館藏書4萬多冊,設有雜志、報章、一般和兒童閱覽四部,另外為供專門問題研究,還特設研究室。開館后,“該館的閱讀者日益眾多,報章室總是擠得滿滿的,閱讀者多半是和平區的市民和附近國職二中等校的學生。至于遠地的讀者卻很少,因此該館館址似乎過于偏處了……為補救稍遠的閱讀者及方便全市各中小學機關的閱讀起見,館方現在正準備館外借閱,并準備在全市各區設書報流通站,由館方派員輪流供應書籍,這確是很好的服務”[9]。1948年為服務廣大市民需要,設立兩分館閱覽室(中山公園第一分館閱覽室和第二分館雨農圖書館)。
近代武漢的圖書館建設在湖北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乃至在全國都具有一定的影響,是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其中藏書量較大、在全國圖書館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有湖北省立圖書館(最早的省立公共圖書館之一)、武昌文華公書林(最早提供現代文化服務的私立圖書館)、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最大的學校圖書館)、漢口市立圖書館(市立公共圖書館)。
湖北省立圖書館是武漢最早建立的公共圖書館,也是全國最早的省級公共圖書館之一,1904年由張之洞籌劃創辦。館址位于武昌蘭陵街,當時藏書約4萬冊,讀者必須衣著整齊、進門買票。1927年改為湖北省立圖書館,采用美式管理辦法,進館新書改用卡片式目錄,引用美國杜威十進分類法編目,讀者進館不再收費。1928年藏書為10萬余冊,其中古籍舊書7萬余冊,中文新書1萬余冊。館內分別設立有圖書閱覽室、藏書室、閱報室、兒童閱覽室、教育品陳列室等,全部免費開放。“1929年讀者56537人,全年開放354天”;到1935年,藏書發展到有“古籍九萬多冊,善本三千多冊,平裝書二萬多冊,西文書三千多冊,日文書一千多冊,雜志一千多種一萬多冊,兒童書四千多冊,共計十三萬一千多冊”[10]。為促進文化發展,1936年9月在蛇山抱冰堂建成宮殿式新館,總面積2000余平方米,組織機構健全,員工17人。但未等新館正式開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于1938年西遷秭歸、恩施,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開放閱覽。1948年8月遷回武昌。
武昌文華公書林是武漢最早的私人圖書館,由美國人韋棣華于1910年籌辦。館址位于武昌曇華林,藏有“中文書籍2萬多冊,外文書籍3萬冊,中英文雜志100多種,另有古礦物、標本等一千多件”。公書林秉持為民眾服務的思想,把圖書公開陳列于書架之上,民眾不論出身、地域和身份皆可閱覽圖書。為吸引民眾閱讀,韋棣華女士利用參觀、演講、音樂會、表演等方式極力宣傳,1914年又設立“巡回文庫”,把學校、機關、工廠等機構納入到圖書閱覽的流動范疇,實行定期交換,這使得文華公書林逐漸成為“武漢三鎮赫赫有名的圖書館”[11]。1922年公書林進行館址改造擴充,公書林所屬的文華大學(后改為華中大學)在國內最早設立圖書館科(新中國建立后并入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是專業培養圖書館管理、運用專門人才的機構。著名圖書館學者沈祖榮即是公書林培養的第一批優秀學生代表。武昌文華公書林為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科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是民國時期國內最大的學校圖書館。1928年11月,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在武昌東湖之濱珞珈山麓籌建包括圖書館在內的新校舍。在新校舍建筑及設備預算中,圖書館建筑費(含防火設施)170000元,設備費(含防火設備及桌椅書架等)40000元。籌備會委員李四光出面聘請著名美國設計師開爾斯為圖書館及新校舍的總設計者。在圖書館建設過程中,大量購置圖書,每年經費約10萬元。“其中文學院在建校8年中,購買中西文圖書約有數萬冊,雜志100多種;理學院購進近代雜志200多種,購置舊雜志37種(全套);農學院一開辦就訂有中英文雜志30多種,購置中文農林書籍500余冊”。館藏中文書約六、七萬冊,西日文書約三萬冊,共約10萬余冊。每月閱覽及借書統計平均在二千人以上[12]。1936年新館建成時,“藏書已達14萬冊”[13]。
漢口市立圖書館是武漢最大的市立公共圖書館。漢口在1945年之前一直未有大型圖書館。20世紀20年代只有漢口市商民協會設立的“漢口市圖書館”、漢口工商俱樂部圖書室和漢口市黨部圖書館等。但到1933年9月,只剩下一所“漢口市立民眾圖書館”。1936年何成睿等人發起建立漢口大規模圖書館的倡議,成立了漢口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并指定了館址,還展開了部分閱覽工作,但由各種原因該計劃無形解體。所以直至抗日軍興,漢口終無一完善大型的圖書館。日本侵占武漢時期,先后在漢口設立了中日文化協會圖書館和漢口市立圖書館。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接收了漢口市立圖書館圖書3萬冊,并于1946年9月在長春街73號建立“漢口市立圖書館”,該館占地約100平方米,使用面積約200平方米,除書庫和辦公室等以外,有讀者座位約20個,年購書費150萬元。由于該館地址偏僻,群眾希望把它遷來市中心。1947年10月,將原中山公園圖書館加以充實撥給漢口市立圖書館管理,作為該館第一分館。1948年4月1日又在黃興路建了第二分館,即“雨農圖書館”。漢口市立圖書館總編制13人,藏書共5萬冊[14]。設有新聞及期刊閱覽室和普通閱覽室,普通閱覽室分館內閱覽和館外閱覽。每逢星期一普通閱覽室休假,該館每天接待讀者約150人次。1949年解放后改為武漢市圖書館。
2 管理體制
19世紀末,清政府在漢口設都司衙門,兼管社會教育、文化、藝術活動。由于圖書館發展規模不大、發展較緩慢,實行“文教不分”的管理辦法,社會文化活動多屬官辦,由政府任命主管負責人。如1898年擬定的《京師大學堂藏書樓章程》確立了“提調一員,供事十員”等管理體制,1904年晚清新政改革頒布的《大學堂圖書館章程》制定了“借取章程”、“借還書、預借及毀損賠償”等具體圖書管理制度[15]。1906年清廷進行體制改革,在學部下增設圖書司,各省則由提督學政管理。1912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圖書館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管轄。湖北省教育廳也成立相應機構,地方的文化藝術活動逐步納入政府的分級管理。1926年,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市教育局共同管理社會文化。教育局是管理圖書館的核心機構,當時教育的經費開支相當龐大,以漢口特別市為例,1930年漢口教育局一個月的教育經費支出大約在6.6萬元左右。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的最高機構——中華民國大學院,以進一步加強對圖書館的管理和控制。大學院相繼頒布《圖書館條例》、《新出圖書呈繳條例》等條例規章制度。其中《圖書館條例》對各地圖書館的設立和經費來源作了說明;《新出圖書呈繳條例》規定“凡新出圖書,出版者應繳送4本,出版者所在省市教育廳局1本,教育部圖書館、中央教育館、中央圖書館各1本,如不呈繳者,禁止該書發行”。1930年5月公布《圖書館規程》14條,規定“各省及特別市應設圖書館,儲集各種圖書供民眾閱覽”、“各省市縣所設之圖書館,稱公共圖書館;私法人或私人所設者,稱私立圖書館”。除此還規定了公立圖書館的典藏范圍,另外還增加了“每年6月底由各省市教育廳局將省市縣立圖書館及私立圖書館概況向教育部匯報1次”的內容,以進一步加強對圖書館事業的管理。同年10月,教育部頒布《私立圖書館立案辦法》3條。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圖書館法令法規,對促進地方縣市的圖書館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1939年教育部頒布《修正圖書館規程》33條,第一次詳細規定了省市縣立圖書館的機構設置、館長及各級負責人的資格以及圖書館經費等的籌措。
武漢地區的各級各類圖書館依據國民政府的圖書館規章制度建立了相應的規程和工作大綱。1929年湖北省教育廳計劃整理省立圖書館并充實教育品、陳列所及理化、博物等部,湖北省圖書館制定《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借書規則》、《參觀規則》。如《湖北省立圖書館組織規程》明確了圖書館的事務有10項:保存本館原有圖書及選購最近出版圖書;購備關于宣傳黨義各種定期及非定期刊物;搜集藏書善本、孤本、初印本各種書籍;保藏征集本省先正遺著;征求各種刊物及未刊著作;分類陳列各種圖書報章雜志,供給眾覽或借出;選購淺明書報,供給兒童閱覽;陳列各種教育用品,供公眾觀覽及學者參考;編訂及刊行各種中西文圖書目錄;研究圖書學及其應用方法,以促進社會教育之發展。關于館員的任免由教育廳負責:館長由教育廳委任,股長由館長呈請教育廳委任,股員由館長委任,書記由館長委用,呈報教育廳備案。并明確規定書報及陳列教育品之各室完全開放,供眾閱覽,概不收費。1931年3月《湖北省立圖書館章程》(12條)公布實施,12月《圖書選購委員會章程》(7條)公布施行。該選購委員會有9人組成,由教育廳聘該廳第一和第三兩科科長、圖書館館長及圖書館股長、學術專家5人組成。

圖1 湖北省立圖書館組織系統[16]
圖書館由教育局直接管轄,是社會教育的核心載體。武漢作為湖北的經濟、文化中心,尤其重視社會教育。在具體圖書館場所的管理經費方面,武漢政府在1932年-1934年,對圖書館的經費預算保持穩定的增長。以漢口市為例,1932年圖書館的經費為5368元,占當年教育文化費(447027元)的1.2%;圖書館的預算經費則從1932年的5368元增加到1933年的110352元再到1934年的142620元,增幅更是驚人。
3 服務舉措
“圖書館為藏書所,供各學校及民眾研究科學之用”[17]。為最大化的實現教育民眾的目標,圖書館積極采取各種途徑、開展各種活動。“圖書館為民眾公共求知之所,包羅萬有,貫通中外古今,無論男女老幼,貴賤貧富,聾啞殘疾,皆隨時隨地順其個性之所近,以自動閱讀研究,其功用不在學校之下,而收斂甚或且過之”[18]。為了達到服務大眾的目標,武昌的湖北省立圖書館進行了各個方面的優化。大革命以前,進館看書是收費的,所謂“供眾閱覽、進門買票”。1927年以后,圖書館實行免費開放,讀者領借書證進門閱覽。每人一證,每證可借平裝書五冊、線裝書十冊。一般書借書期限為三個星期,小說書兩個星期,圖書出納處和各閱覽室每天上午9時至下午5時開放,星期天不閉館。
1927年-1937年,武漢的公共圖書館實行免費開放政策,以提倡社會教育,為民眾服務。“夫設立圖書館,既以謀利益于社會為主。故凡可以益人者,則必盡力圖維,無或稍怠,俾人人咸得讀書之便利”,因此圖書館實行:“(一)免閱覽之費。圖書館之設立,概系公共性質。常課稅于地方,以為經費。故館內圖書,自當免費以供民眾之閱覽。(二)書庫之開放。自閱者之便利而言,必當開放書庫,俾得親就書架,任意取閱”[16]。

表4 1929年湖北省立圖書館報章雜志閱覽室讀者人數及職業統計[10]
1929年湖北省立圖書館閱報室全年開放了354天,全年閱報室的人數達到56537人,平均每天160人,其中學生(學者)的比例最高,達到43.77%,商人次之,為22.89%。可見當時的免費開放和開放時間的設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漢口市立圖書館也積極推廣各種工作,服務民眾,常設的有:放映教育電影、兒童書畫展覽、全國木刻展覽、國父生平事跡展覽、圖片展覽、舉辦公私立中學論文比賽。由于該館地址偏僻,群眾希望把它遷來市中心。于是,1947年10月把原中山公園圖書館加以充實撥給漢口市立圖書館管理,作為該館第一分館;次年4月1日又在黃興路建了第二分館,即“雨農圖書館”。
同時,圖書館與民教館聯系密切,如1948年中山公園內的自由民教館交由漢口市立圖書館第一分館中山公園圖書館接管,后又將漢口市立圖書館代管之全部科學儀器及生物各標本移交民教館,設置科學陳列室,一面又接收民教館附設中山公園之圖書室全部器物及書報,再加以充實成立分館。

表5 1948年漢口市立圖書館中山公園分館預算[19]
中山公園環境宜人、人流量大,漢口市立圖書館中山公園第一分館的設置,極大擴展了漢口市立圖書館的圖書展覽和閱讀功能,民眾閱讀人數有極大的提升。

表6 漢口市立圖書館1948年各閱覽室閱覽人數統計表[19]
漢口市立圖書館為提倡美術教育,發揚藝術天才,及科學運動起見,特于青年節與兒童節期間在市商會舉辦全市兒童書畫及科學畫片展覽。陳列作品中書法方面,楷、草、行、篆具備,圖書方面舉凡西洋書中之人物山水花卉計一千五百余件,應有盡有,美不勝舉[20]。
服務民眾是圖書館的根本使命,然而在民國初期,圖書館還屬于“新名詞”,民眾幾乎都沒怎么聽說過,如何吸引民眾,拓展服務,就需要建立一套服務宣傳體系,以促進知識的傳播。作為“傳播消息及知識之總機關”和“宣傳文化之總機關”,“公共圖書館如要擴張圖書事業,也要采用廣告來作宣傳的利器”[21]。因此,圖書館經常在各種刊物上打廣告宣傳各種書籍。如將每年的圖書館報告、圖書館小史、發展計劃登在報紙上進行宣傳。
圖書館為“傳播消息及知識”經常在武漢市內舉辦流通圖書館,如1934年5月湖北省立圖書館設流通書庫4個、各儲通俗圖書200余種,每日派員領運各類通俗圖書及各種報章雜志,分赴武漢各區公共場所或茶園附近民眾稠密之處進行圖書巡回流通閱覽。《武漢日報》載:“昨日,在黃鶴樓警鈡樓下各界民眾多人,圍集庫前,翻閱書目,各就其性之所喜者,紛紛取閱,莫不人手一編,亦有上等人士,參雜其中,咸以游覽之余閑,獲讀書之機會,稱為快事;將來逐漸推廣,遍行各地,誠一般民眾之福音也”[22]。后為進一步擴大知識的傳播,圖書館決定利用暑假到保安門等郊區進行流動展覽。
4 結論
從1904年到1949年,武漢地區的圖書館建設與發展既經歷了從“傳統到近代轉變”的初步發展期(1904—1927年)、“黃金十年”的迅猛發展機遇期(1927-1937年),也邁過了“黑暗八年”的衰落期(1937-1945年),1945年到1949年為重新整合期,為新中國圖書館建設發展打下基礎。以歷史的眼光總體來看,這45年間武漢地區的圖書館建設與發展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數量從無到有,種類由單到多,分布由點及面,功能由服務少數到服務大眾,影響波及全國,為武漢城市風貌和市民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
4.1近代武漢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特色
近代武漢圖書館建設與政治環境、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民眾的文化生活需求以及文化建設者的眼界等因素息息相關,近代武漢圖書館事業發展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黃金十年”為圖書館建設發展的高峰期。1927年-1937年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政治相對穩定,國民經濟不斷發展。武漢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中心城市,于1927年設立武漢特別市,統轄武漢三鎮。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劉文島、董修甲、吳國楨、吳國柄等人主持市政,這些高學歷的市政“專家型領導人”經過謀劃統籌推動了近代中國城市發展史上有名的“漢口市政改革”,對武漢的城市區域規劃、城市功能分區等進行了統一設計,加大了對武漢城市公共事業的財政投入。他們特別重視城市文化的作用,積極倡議圖書館等公共文化場所建設,把圖書館建設作為提升民眾教育、啟發民智、陶冶市民情操的重要手段。這一時期圖書館建設迅猛發展,武漢建設各種圖書館151所,其中大型公共圖書館2所,圖書館場所的建設數量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類型齊全,影響波及全國,是近代中國圖書館建設發展的縮影與典型。武漢圖書館的建設與發展不是單一類型的發展,而是多種類型共同發展。圖書館作為學習交流中心,有普通、專門、學校、民眾、流通、機關、私家等多種類型。并且,武漢市政府還把圖書館建設作為“重大文化工程”,以滿足民眾文化需求和城市文化發展的需要。其中,湖北省新圖書館、漢口市立圖書館為重大工程,市政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建設,科學規劃、注重服務,影響波及全國,特別是湖北省立圖書館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成為近代中國圖書館建設發展的典型。
第三,圖書館場所分布大體均衡,覆蓋面較廣,服務周全。圖書館是面向社會大眾開放的公共場所,與民眾的日常文化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圖書館場所的分布應遵循空間可達性和公平性的基本原則,即擁有相應文化需求的民眾能夠便捷的達到目標公共場所,并讓不同階層的民眾能夠平等的享受各種相關文化服務[23]。武漢的公共圖書館分布于城市的中心地帶,居民集中,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公共圖書館免費對民眾開放,讓不同階層的民眾都能夠平等的享受各種文化服務。圖書館還專門設立流動書庫,讓更多市民享受圖書閱覽服務。另外,圖書館基本覆蓋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圖書館的分支機構和流動設施更是深入到城市郊區。
第四,具有“傳統與現代”雙重屬性,積極探索現代管理體系。一方面,近代圖書館場所脫胎于傳統的文化設施又與傳統的文化設施有根本區別;另一方面,近代圖書館場所的建設借鑒和參照了西方的樣式及內容,體現了向西方現代化學習和看齊的趨勢。例如中國近代最早的圖書館是在傳統的藏書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圖書館是“動、平民式、貴致用、設在城市、民自動辦的、注重精神娛樂、文化宣傳的機關”[21],公共圖書館更是“人民之公共產業”[24]。總之,近代圖書館體現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內涵,追求“公共性”成為公共圖書館宣揚的主體價值。近代武漢圖書館脫胎于傳統但更具“現代性”,而對這些圖書館場所的管理則必然體現出政府追求“現代化”的時代訴求。圖書館納入政府管理的范疇,武漢市政當局為之成立了專門的行政管理機構和制定了相應的政策規章制度,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圖書館管理體系。
4.2圖書館建設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圖書館作為一種傳播文化知識的機關,雖在管理上受國家控制,但在具體工作和活動的開展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其目標是促進社會民眾教育,“廣泛傳播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風范”,培育符合新時代風尚的新市民。圖書館宣傳的公共文化知識和組織的民眾教育活動,使各自陌生的民眾聚集于一個公共場所,民眾的公共觀念得到有效培育,形成了“市民認同”。
在民國時期,圖書館建設對于民眾公共精神、公共觀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圖書館為市民的社會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個“公共場域”。這種“公共場域”具有一種規約作用,即規定了哪些行為是被鼓勵的、哪些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引導一種新的健康的生活風尚。同時,圖書館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有意識的灌輸一種公共意識,促進民眾社會教育的發展。
一方面,滋生助長了民眾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傳統的公共文化生活主要是過年過節期間的廟會。圖書館建立后,每天定時定點向普通民眾免費開放。這些場所通過圖書、展覽、音樂、講座等形式多樣的活動吸引廣大民眾參與進來,增強了近代武漢市民的公共生活體驗,是城市文明進步的表現。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空間,具有開放性和功能性,其免費開放能夠讓普通民眾進入其中進行學習和娛樂,擁有最廣泛的“可及性”,即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任何人所見所聞。在這種“情境”下個人與社會密切的聯系起來,民眾在公共文化空間中自覺排隊、遵守時間、維護秩序,還建立了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另外,在個人、社會或國家需要幫助的時候,公共文化場所積極號召民眾參與,如1931年武漢水災之后的義務捐贈、興建湖北省圖書館新館的捐款、捐書運動,都反映了一種公共精神。20世紀30年代,圖書館經常舉辦的各種展覽和各種團體性活動,也培育了民眾的公共精神。
另一方面,拓展了城市的功能。軍事功能、政治功能、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是城市的主要功能,而文化功能具體表現為文化貯存、文化傳播和交流、文化創造和發展三種形式,最能體現城市的內涵。武漢在古代王朝體系治理下主要作為軍事和政治中心,隨著明清商業經濟的發展,漢口的經濟地位日益攀升,成為“四大市鎮”之一。1861年漢口開埠通商后,工商業經濟進一步發展,并在張之洞主政期間,軍事、政治、經濟和文教事業都有不俗的建樹,為“大武漢”奠定了歷史基礎。民國時期,大眾文化流行,城市的文化功能日益重要,并成為城市“人氣”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文化建設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引擎”。圖書館建設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成為民國政府大力推動社會民眾教育的主要載體,得到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武漢圖書館建設在民國時期蓬勃發展,為城市發展創造了“公共文化空間”,不僅提升了市民的公共素養,而且也為城市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近代武漢的城市面貌和城市精神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這在抗日戰爭時期武漢的各種抗日文藝組織的積極活動中彰顯無遺。
總之,近代城市圖書館事業在場館建設、管理體制和服務舉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其中有很多場館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一直延續到今天,繼續發揮著服務大眾文化、傳播知識的重要作用,為城市文化發展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另外,“委員會制”的管理模式和循環流動的服務方式仍然對當今的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具有歷史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來稿時間:2016年3月)
1. 李希泌, 張椒華.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1982:256-257
2. 來新夏.中國圖書事業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94
3.本國教育文化史的新頁[J].教育雜志,1936, 26(4):281-282
4. 二十四年度全國公私立圖書館統計[J].教育與民眾,1936, 8(5):846-847
5.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全國公私立圖書館一覽表[M]. 1936
6.湖北省圖書館.百年圖書館事業與推進社會信息化[M].武漢:武漢出版社, 2005:7
7. 黃穎.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破壞與掠奪[J].津圖學刊,1995(3)
8. 漢口市立圖書館正式成立[N].大剛報, 1946-09-12
9. 本市圖書館訪問記[N].漢口報,1946-11-24
10. 湖北省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建館八十周年[M].武漢:湖北省圖書館, 1984:2-3
11.唐秀.文華公書林研究(1910-1938)[D].武漢: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1
12. 莊文亞.全國文化機關一覽[M].1934:338-339
13. 吳貽谷.武漢大學校史(1893—1993)[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3:12
14.姚海泉.漢口圖書館歷史知見錄[M].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231-232
15.楊志永.我國近現代公共圖書館事業變遷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9:46
16.童錫琛.近代圖書館制度[J].東方雜志,1912, 9(5):14
17.湖北省志《文藝志》編輯室.文藝志資料選輯(一)[M].1982:366, 57
18.畢斗山.湖北省立圖書館概況[M].漢口:白鶴印刷公司,1930
19.武漢市檔案館,卷宗號:LS009-30-00117
20.漢口市立圖書館[N].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847
21.李小緣.藏書樓與公共圖書館[J].圖書館學季刊,1926,1(3):388
22. 傳播知識及信息[N].武漢日報,1934-07-16
23.顧鳴東, 陳白磊.城市公共設施的空間可達性與公平性研究述評[J].現代城市,2010, 5(1):30-34
24. 李小緣.公共圖書館之組織[J].圖書館學季刊,1926,1(4):64-91
A Study of Modern City Library Cause by Taking Wuhan as an Example
Geng DaFu Caiwu
(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
〕In the modern China, Library causes also made a goo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1927-1937, the “golden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ru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libraries in Wuhan was variety and balanced distribution, coverage, management clear,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ffecting the province and the country. As a “public cultural space”, the library not only affects people’s cultural life,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y transformation.
〕LibraryVenue constructionManagement systemService initiatives
G259.2
耿達(1988-),男,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已發表論文10余篇,研究方向:中國文化史、公共文化政策;傅才武(1966-),男,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國家文化財政政策研究基地主任,研究方向:中國文化史、公共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