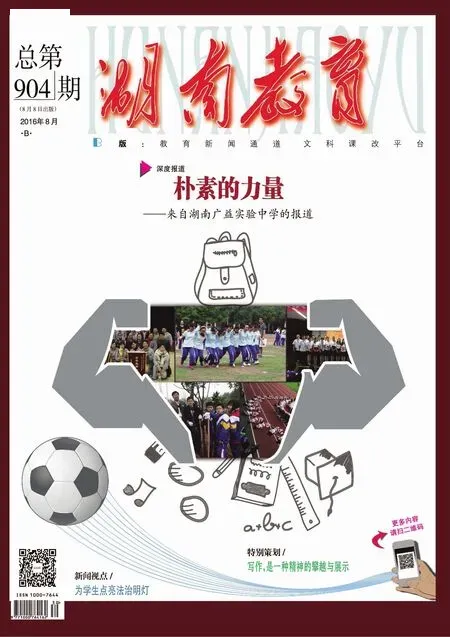從來就沒有完美的教材
李竹平
從來就沒有完美的教材
李竹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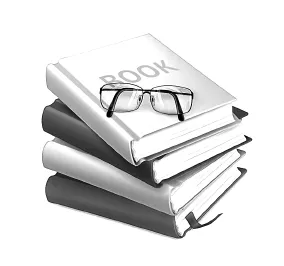
我們的教材總是被挑刺,曾經是,現在還是。
我說“從來就沒有完美的教材”,并非要為被挑刺的教材說話。作為一個使用教材這一“工具”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教師,就像工人拿起起子、農人掄起鋤頭一樣,哪個好用,哪個不好用,用過后自然就有了自己的判斷——但也只能是自己的判斷,有的你覺得好用的,別人也許覺得不好用。這里面有個體差異。衡量一本教材質量的好壞,必須來自于對教材的解讀和使用。
怎樣解讀一部教材呢?當然要看教材編寫的理念、思路、結構以及呈現方式。從理念來看,既有綱領性“標準”引領,也包括投射到操作層面的“行動”導向。以語文教材為例,有沒有將課程標準所闡述的目標和內容貫徹于教材當中,這是首先要考量的問題——雖然課程標準也不完美。例如,課程標準在寫作教學建議中提出“應抓住取材、構思、起草、加工等環節,指導學生在寫作實踐中學會寫作”,而整套教材都找不到與此相關的教學內容編排,那就犯了綱領性的錯誤,投射到操作層面,教師在行動中就極有可能忽視這些環節的指導。教材是教師教的憑依,更是學生學的首要材料和引領,所以既要便于教師的教也要便于學生的學,這是教材編寫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如果一套教材發到教師手中,大多數教師不能從教材自身弄明白用它干什么和怎么用,這套教材肯定是不合格的。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很多教材,尤其是語文教材,的確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
個人以為,我們的母語教材之所以總是遭到詬病,不是沒有正確的理念作為指導,而是我們的思維習慣導致了理念與實踐的隔閡。我們似乎不習慣于縝密而清晰的思維,一直以來推崇“言約義豐”,鼓勵讀出“自己的理解”,所以課程標準強調“解讀”,強調“解析”。許多專家的解讀或含糊其辭或高高在上,弄得一線教師云里霧里,無從下手。教材也大多與課程標準的這種“務虛”思維一脈相承,教學目標總被“隱含”,操作策略總被“隱藏”,教學操作和質量就更多地依賴于教師的個人特質和素養,出現了判若云泥的差距。同時,我們存在著認識上搖擺不定的事實,使得教材編寫者在有爭議的問題上采取回避態度,也給教材的解讀和使用帶來了麻煩。例如,在寫作知識的教學上,我們為了凸顯“實踐出真知”,便有意弱化甚至規避寫作知識的教學,以為只要有了實踐,知識便都會自然而然地“長”出來。美國一年級學生學習寫作,就明確了開頭、細節和結尾的寫法用法,我們卻生怕這樣會有損于學生寫作興趣的培養。我們總簡單地將感性與理性對立起來看待,而很少在兩者之間找出平衡點,做到相得益彰。
一套教材質量的好壞,還要通過實踐來檢驗。首先是教材好不好用的問題。這在前面談解讀時就提到過。一套好的教材,使用者通覽一遍,就知道它包含了哪些內容,力圖實現哪些目標,明白要循序漸進地做些什么;一套不好的教材,使用者通覽之后,腦子里會一團漿糊。其次是教師會不會用的問題。如果一套教材,大多數教師都能通過對教材的解讀,明了該怎么用它,這樣的教材一定是思路清晰、結構合理的;若大多數教師都覺得它看上去很美,就是不會用它,這樣的教材就值得懷疑了。
現在,不容樂觀的不僅僅是教材本身的質量問題,還有教師的主動性問題。我倒不覺得給蘇教版教材挑刺的彭老師是“多事”,恰恰相反,如果我們的教師都能這樣主動地、帶著批判性眼光來解讀課標,審視教材,而不是盲目依從,甚至奉為“圣經”,能處處遵循學科規律,時時充分考慮學生的心理和思維特點,對于我們的教學,將是莫大的助益。
從來就沒有完美的教材。如果真做不到讓教材更加完善些,那就要看我們怎樣對待和處理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