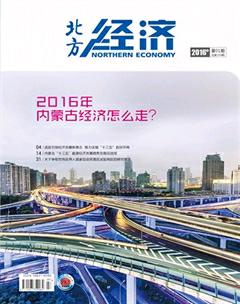城鎮化進程中新市民社會融合問題研究
雷曉康孫嘉臨
城鎮化進程中新市民社會融合問題研究
雷曉康1、2孫嘉臨2
一、城鎮化進程中新市民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分析
在我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新市民成為了一個新的群體。新市民是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中間狀態人群,他們已經在城市居住和生存下來,但不具備合法的城鎮居民戶籍,以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固定勞動力為主。新市民的社會融合是指新市民的就業、居住、價值觀等不斷地融入市民社會,并最終向城市居民轉化的過程。綜合來看,在城鎮化的背景下,新市民的社會融合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響:
(一)自身人力資本素質
勞動力遷移是人力資本的函數,自身人力資本素質較高的農民工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積累工作經驗,建立社會網絡,促進社會融合。在自身人力資本素質這一因素上,我們選擇教育水平、技能培訓和就業三個指標進行考量。
(二)經濟條件
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外來農民工在流入地從事的大多是待遇差、工資低的崗位,就業穩定性差,加上消費習慣還保持著在在農村生活時的痕跡,這種天然的不平等不利于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在經濟條件這一因素上,我們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兩個指標進行考量。
(三)居住情況
居住情況從側面反映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它決定著在上班之余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圈子,能否融入流入地的社區,建立新生活。在居住情況這一因素上,我們選擇住房這一指標進行考量。
(四)社會接納度
社會接納度涉及的是整個社會環境對農民工的接納程度。城市居民與新市民社會交往是否平等,整個社會對農民工的印象如何,以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社會貢獻的判斷等都會影響雙方的社會交往,進而影響農民工社會融合。在社會接納度這一因素上,我們選擇社會交往和公共權益兩個指標進行考量。
(五)政府政策支持
政府政策是農民工社會融合的一個重要因素。城鄉二元制度發展至今產生了一定的政策慣性,不能適應當前的城鎮化發展。與戶籍制度相聯系的一系列教育、福利和保障政策成為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阻礙。在政府政策支持這一因素上,我們選擇國家政策和社會保障兩個指標進行考量。
二、城鎮化進程中新市民社會融合現狀分析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農民工監測報告》發布的調查數據,我們從自身人力資本素質、經濟條件、居住情況、社會接納度和政府政策支持5個因素出發,對目前我國農民工社會融合現狀進行分析。
(一)新市民自身人力資本素質情況
在教育水平方面,在農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學文化程度占14.3%,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4%。其中外出農民工文化水平高于本地農民工,本地農民工文化水平則高于非農民工。同時,新生代青年農民工高中文化以上水平的比重明顯高于其他。
在技能培訓方面,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25.6%,沒有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的占69.2%,年長者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比例高于青年。農民工大多缺乏必要的工作經驗,知識技能的困境是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文化環境的重大障礙。
在就業方面,首先,農民工就業以體力勞動為主。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所占比重分別為35.7%、18.4%、12.2%,從事制造業的比重最高,從事建筑業的比重變化較快。其次,農民工受雇人員增長快于自營人員的增長。在外出農民工中,受雇人員占95.3%,自營人員占4.7%,在本地農民工中受雇人員占72.8%,自營人員占27.2%,其中外出自營和本地自營比上年下降0.5和0.9個百分點,可見農民工獲得了更多受雇傭的機會。最后,從就業穩定性上來看,農民工就業穩定性較差。農民工從事現職的平均時間為3.2年,從事現職不足1年的占11.7%,1-2年的占45.5%,3-5年的占27.8%,從事現職五年以上的僅為5%,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差,大量外出的同時也大量回流。

(二)新市民經濟條件情況
在收入方面,截至2012年全國范圍內農民工務工的月收入水平為2290元/人;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統計結果顯示,2012年中國員工的月平均工資為656美元,約合人民幣4134元;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城鎮居民人均總收入為26959元,平均月收入約為2247元。2012年我國農民工的月收入水平高于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基本能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但是,農民工月收入遠低于我國員工月平均工資,收入水平明顯較低。
在消費水平方面,據調查,2012 年外出農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費支出733元,省內務工農民工人均月消費支出685元,跨省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消費支出788元。英國《中國投資參考》對中國各地1500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2012年,農民工在消費品和服務上的支出約為4.2萬億人民幣,新生代農民工比老一代農民工更能花錢,他們的消費支出占收入的53%。消費支出比例的上升,說明隨著收入的提高,新市民開始產生品牌認識,消費習慣逐漸向城市社會靠攏。
(三)新市民居住情況
在住房方面,檢測報告顯示,2012年農民工在單位宿舍中居住的占32.3%,在工地或公棚居住的占10.4%,在生產經營場所居住的占6.1%,與他人合租住房的占19.7%,獨立租賃住房的占13.5%,每天回家居住的占13.8%,只有0.6%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農民工的居住條件較為簡陋,自購房是極少數農民工安居的選擇,大部分人只能在務工的公棚或生產場所居住。
(四)新市民社會接納情況
在社會交往方面,在社會適應初期,新市民社會交往仍以原來的社會網絡為主。值得關注的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有一部分人開始去認同和接受城市社會,參加集體活動,建立社交關系,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已與第一代農民工在社會交往上產生了差異,對于社會融合來說,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在公共權益方面,截至2012年,外出受雇農民工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的占43.9%,與2011年的數據43.8%基本持平,增長不明顯。在農民工被雇主拖欠工資方面,外出受雇農民工被雇主拖欠工資的比例占0.5%,較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拖欠工資的情況持續改善,農民工工資有保障。
(五)政府政策支持情況
在國家政策方面,2007年3月,全國十屆人大五次會議在《關于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當中提出,“我國農民工在全國人大中應有適當的名額代表,尤其在農民工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該有農民工代表。”2012年民政部《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提出農民工融入社區的具體路線,為農民工獲得合法權益提供制度保障。
在社會保障方面,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率有所提高,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工傷、醫療、失業和生育等社會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4.3%、24%、16.9%、8.4%、6.1%。綜合5年內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比例的數據可以發現,除工傷保險較穩定以外,其他四類險種的參保比例均穩中有升。
綜合來看,目前我國新市民社會融合狀況良好,雖然各項指標比城市平均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發展前景積極,新生代農民工的影響不容小覷。
三、城鎮化進程中新市民社會融合存在的問題
(一)新市民就業穩定性較差
農民工進城務工一段時間以后,對工作性質、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等條件逐漸產生一定要求,當工作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時,新市民會選擇辭職或變換工作。再加上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勞動結構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使得新市民群體就業情況十分不穩定。
(二)新市民收入水平偏低
雖然消費觀念不斷進步,但是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受到自身條件和工作條件的限制,新市民的收入與城市職工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與新市民不斷發展的消費觀念形成了矛盾,難于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不利于我國當前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利于城鄉統籌發展。
(三)新市民居住條件簡陋自購房能力弱
雖然居住條件在不斷改善,但是新市民的居住條件遠不如城市居民。“住房難”仍然是新市民融入社會的重大障礙。目前我國房價遠高于新市民的承受水平,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新市民也沒有被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系,“住房難”在無形中增加了新市民的流動性。
(四)新市民的社會接納度有待提高
新市民進入城市是其自身的理性選擇,也是城鎮化發展的必經階段。然而,城市排斥新市民,新市民在城市缺乏安全感、歸屬感也是當前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各種價值觀念的接受程度較高,但是大部分新市民仍然處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力對城市社會產生影響。
(五)新市民政治參與途徑空白
由于常年在外打工,農民工無法參與村民大會,無法表達政治訴求。而在常年生存的城市,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也沒有參與城市政治的權利。同時,由于工作流動性大,農民工一般無法參加工會組織或者黨團組織,難以找到參與政治、行使權利的“落腳點”。新市民政治參與途徑空白,是政治活動的邊緣群體,政治權利普遍缺失。
四、相關政策建議
(一)大力充實新市民的人力資本
不斷完善新市民的職業技能培訓,積極建立繼續教育的培訓渠道,增加新市民的人力資本,真正將新市民作為一種資源和財富,根據市場的需求,培養新市民的勞動技能。同時通過就業登記、就業指導等方式,培養和強化新市民的就業觀念,規劃就業方向,從而穩定就業。
(二)持續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建設創造就業崗位
勞動力市場的供需不平衡是造成新市民工資偏低的重要原因。勞動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造成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只有不斷推進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才能有效緩解新市民工資水平偏低的情況。同時,要拓寬信息渠道,使新市民獲得更多的就業信息,減少盲目擇業。
(三)建立新市民保障性住房工程
考慮到新市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目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實際情況,應盡快將新市民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系,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政府主導,給予有力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同時鼓勵社會力量積極投入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當中,為新市民安居樂業提供有力的物質基礎。
(四)促進農民工和市民互動推動社會和諧
增加新市民與城市居民的互動,有利于新市民接觸到親緣和地緣關系以外的城市人群,一方面使新市民更好地了解城市居民的想法和觀念,融入城市居民的社交網絡;另一方面也改變城市的主流文化,使新市民真正地成為城市中的一份子,融入主流文化,通過互動關系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五)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賦予農民工平等公民權
由于農民工群體龐大并且增長迅速,這部分人的公民權利應該得到重視,其在政治權利上的空白應得到補償。戶籍制度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當代已經充分顯露出來,戶籍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政府應通過戶籍制度的改革給農民工創造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立足點,使農民工擁有平等的公民權。
(作者單位:1.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2.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楊再梅
本文受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重大項目(No.13JJD630011)、2014年西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計劃重大培育項目(No.XDFR201403)和陜西省統計局2015年度陜西省統計學會統計科學研究項目(No. 2015LX10)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