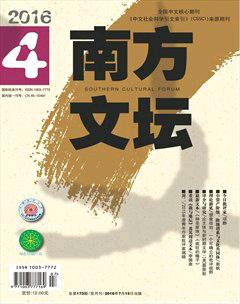文本、理論、世界和自我的重逢
2016-09-07 13:41:05呂永林
南方文壇
2016年4期
關鍵詞:文本
人的許多行動都將滋養自身,或者敗壞自己。人的許多動作、表情、說過的話、寫下的字,莫不如此。人的許多行動無論宏大、幽微,皆事關生命的質地。所謂山重水復、柳暗花明式的“桃源”乍現,并非只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世外奇跡,更是深埋在人的眾多行動深處的愛欲與真理。只不過,出于各種各樣或主動或被動的“功利”考量——襯之以及各種各樣所謂的“苦衷”,無數生命早早就被與現世俱來的匆忙與倉皇浸染,面對自己生活中的人事過往,他們很少也很難用心去打開“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這一不二法門,反倒如宿命般去堆積更多的匆忙與倉皇。然而,人生命中每一次無意或故意的放過和放棄——那些人,那些事,往往會架起更大的空洞,淘出更深的虛無。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這話意味著什么?在《漁人之路和問津者之路》一文中,張文江先生將之稱為“漁人之路”首義,云此深言“極要”,“而能否舍棄一切功利計較,正是漁人之路和問津者之路的根本區別。途中人‘忘路之遠近與目的地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一忘空間,一忘時間,存在著思想上的相應。漁人之路最終能通往桃花源,這是潛在的基礎。”①竊以為,根本中的根本,恐怕還在一個“忘”字,若能依此貫注精力、舍卻旁騖,而不是總有一個欲往他處之我,催逼著你中途折返或棄道而行,那么一個人做任何“有大歡喜”之事,豈非就是“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我一直覺得,所有的桃源故事都密傳著同一個主題:自我對他者(或“主體”對“對象”)的巨大熱情與無限親近。……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20年4期)2020-07-25 02:28:52
甘肅教育(2020年8期)2020-06-11 06:10:02
藝術評論(2020年3期)2020-02-06 06:29:22
制造技術與機床(2019年10期)2019-10-26 02:48:08
新世紀智能(語文備考)(2018年11期)2018-12-29 12:30:58
電子制作(2018年18期)2018-11-14 01:48:06
小學教學參考(2015年20期)2016-01-15 08:44:38
語文知識(2015年11期)2015-02-28 22:01:59
語文知識(2014年1期)2014-02-28 21: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