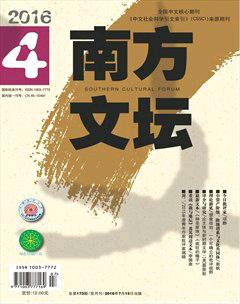主持人的話
主持人季進:蔡榮的專著The Subject in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本集中論述新時期文學主體危機的著作。它以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新時期”為時代語境,通過韓少功、殘雪、余華、莫言、賈平凹等人的作品,探討了在所謂“后毛澤東時代”的思想動蕩中,當代文學作品所呈現出的“主體危機”。全書共分七章,除導論外,分別論述新主體的追尋、韓少功小說中的言說主體、殘雪小說中的自我與他者、新長征中的旅行者、莫言小說中的自我鏡像以及1990年代早期知識分子的自我。既探討小說文本中的文學形象,也論述作為創造者的作家主體,頗多發人深省之論。這里發表的《論主體與新時期文學》就是根據該書《導論》摘譯的,由于篇幅所限,只摘譯了部分內容。
論文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帶有緊迫和復仇之感的重訪”中,現代作家與知識分子延續了五四時期的傳統,視自身為新興啟蒙運動的中堅力量,嘗試通過文本再現的方式,為中國塑造符合“現代性”的全新民族主體。對此,不同于一般的樂觀認識,作者選取了“能動性”作為切入點,以檢驗這一目標在文本層面的實際效用,經由精致的文本細讀,著重討論了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莫言《白狗秋千架》中殘缺和矛盾的主體:大學老師與暖在高粱地的重逢,一方面展示了主觀權利被剝奪的殘缺主體以及知識分子的修復力量,但開放性的結局所遺留的道德困境,也直指后者面對自身合法性危機時的猶豫不決;二是韓少功與殘雪小說中無能的主體:《爸爸爸》和《女女女》中“主人公語言能力的缺失和外部表意系統的控制”使其無法完成塑造新主體的使命,而殘雪筆下的無能自我,則“將存在主義的夢魘轉化為持久的現實”,并“投射到改革后中國的未來”;三是余華與扎西達娃小說中的孤獨旅人:因其始終獨立于激進的社會風氣之外,體現了主體在新的競爭環境中的自我迷失;四是莫言《豐乳肥臀》中的中國自我與異域他者:從二者之間的沖突以及混種私生子的無能,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中國影響力的持續擔憂”;五是賈平凹《廢都》中自我的文學表象:面對90年代的消費主義,邊緣化的知識分子在特殊的表象中討論自身的困境。經由跨越文本內外的主體性分析,作者建構出了新時期文學與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與官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之間深刻的互動。在應對種種社會變革與思想動態的全新挑戰時,新時期文學的主體危機也正好折射出這一批作家與知識分子的精神困惑:對過去夢魘的念念不忘,對當下環境的猶豫不決以及對未來身份的焦慮不安。讓我們重新認識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中復雜與困難的面向。
2014年,麥家的《解密》席卷海外,掀起了一股“《解密》熱”,創造了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奇跡,也極大地提振了當代文學走出去的信心。《解密》為什么會突然走紅國際市場?背后有哪些因緣際會的因素?又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啟示?這些正是《論海外“〈解密〉熱”現象》試圖要回答的問題。論文從《解密》譯本在海外大受歡迎的現象出發,借用布爾迪厄的文化場域理論和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理論,將中國文學的“走出去”視為一個復雜的流通過程,綜合考慮文本內外的諸多因素,以分析《解密》在非漢語市場獲得商業成功的原因。作者指出,首先在翻譯的層面上,譯者米歐敏的出色譯筆和牽線人藍詩玲的推薦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二者的努力,《解密》從一開始就進入英美最出色的出版機構的視野,不同于一般的學術出版,企鵝和FSG出版社將《解密》納入其強大的商業運作體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擴大了知名度。其次在流通的層面上,受惠于“斯諾登事件”引起的話題效應,加之出版社在宣傳語上的推波助瀾,題材類似的《解密》迅速受到評論界和讀者的關注,甚至直接將小說中的紅色間諜英雄與斯諾登相比較,從而引發了廣泛的閱讀興趣。最后在文本的生產層面上,《解密》的間諜(偵探)題材本身是世界性的,不會對西方讀者的閱讀造成障礙,這使得其扎根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的“紅色”元素和傳統概念不會局限在民族文學的帷幕之后,而是喚起了西方讀者對于東方的想象。在敘事中,麥家也明顯地借鑒了博爾赫斯游戲性和迷宮式的敘事方式,并以之來表達對人生終極問題的追問,這也讓其小說更增添了一層世界性的維度。基于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理論,作者認為麥家《解密》在海外的商業成功,證明了“世界文學”概念不是霸權層面的,而更多只是技術層面的,中國文學要想真正“走出去”,還必須是“文學程式、閱讀習慣、地方經驗、翻譯實踐等各種因素的合力使然”。
(季進,蘇州大學文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