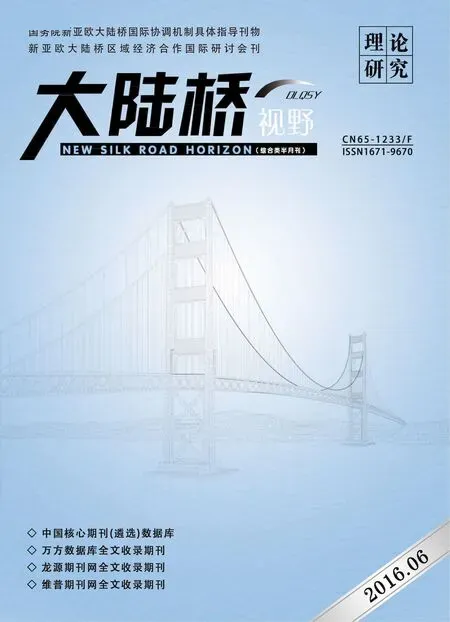翻譯美學視角下泰國小說《畫中情思》漢譯本的語言特色
唐旭陽/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東語學院
翻譯美學視角下泰國小說《畫中情思》漢譯本的語言特色
唐旭陽/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東語學院
本論文主要以翻譯美學理論為基礎,以《畫中情思》原本為參照,以《畫中情思》中譯本為主體進行美學分析鑒賞。按照劉宓慶先生《翻譯美學理論》的原則,將小說譯本內文本進行分析。其語言特色主要體現在大量疊音詞以及部分連綿詞的運用而產生的音韻美以及動詞和成語俗語的使用而產生的美感;句子結構特色主要指譯文句式整齊之美、整散交錯之美,譯文使用了各種句式,對長短句進行巧妙地處理,運用排比、比喻、擬人等句式,使譯文盡量保持與原文的優美和淡雅。
畫中情思;文學作品;翻譯美學;語言特色
《畫中情思》在泰國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由泰國著名的現代小說家西烏拉帕撰寫而成,該小說創作于20世紀三十年代。1982年由欒文華、邢慧如翻譯成中文。《畫中情思》寫作風格是恬淡的、抒情的、散文式風格。所用語言生動、含蓄而又優雅。小說的情節并不復雜,卻寫得波瀾起伏,凄婉動人,令人愛不忍釋。這部作品之所以在藝術上相當完美,和語言的恰當運用不無關系。當這樣優美而經典的作品被譯成中文,筆者認為去研究其中譯本的語言藝術、翻譯技巧是十分必要和有意義的。
一、《畫中情思》簡介
《畫中情思》主要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悲劇愛情故事,女主人公吉拉娣自幼生活在王公之家,卻從小受封建禮儀的約束,沒有人教她獨立思考。時光易逝,當兩個妹妹相繼出嫁,她已經二十九歲,可是憑著優雅的氣質,動人的容貌,她依然對愛情和幸福抱著希望。但除了等待,卻無所作為。寂寞中她學會了打扮、美容和繪畫,并以此度過自己大好的青春時光。三十五歲時,吉拉娣在無奈和失落中嫁給年過半百的紹坤作了續弦。在紹坤帶她去日本度蜜月的時候,遇到了泰國留學生諾帕朋。諾帕朋被吉拉娣深深吸引,而吉拉娣也第一次燃起了愛的火焰。但是由于社會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以及吉拉娣也有意讓諾帕朋安心學習,而獨自忍受愛的煎熬,并多次回避了諾帕朋的愛。五年過去,詔坤病逝,諾帕朋對她的愛已消失不見,而癡情的吉拉娣依然深藏著這段難忘的感情。當得知諾帕朋準備與未婚妻舉辦婚禮時,身體不適的吉拉娣再也承受不住這一打擊。臨終前,向諾帕朋吐露了自己多年來的心聲:“我死了,沒有愛我的人;但我感到欣慰,因為我有了我愛的人。”
二、翻譯美學的定義
朱光潛曾說:“翻譯繞不開美學。”美,有其共性,也有其個性。翻譯美學既關注審美感性在翻譯中的關鍵作用,又重視審美理解在翻譯中的引導作用,它具有較強的理論性,這就是翻譯美學的價值所在。所謂翻譯是將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人類社會實踐活動。而對翻譯美學 的定義沒有那么明確,劉宓慶在《翻譯美學導論》認為就是翻譯學的美學模式,旨在用審美理論描寫翻譯學的各項基本原理、操作原則和發展策略。研究對象是翻譯中的審美客體(原文、譯文),翻譯中的審美主體(譯者、編輯、讀者),翻譯中的審美活動,翻譯中的審美判斷,審美欣賞以及翻譯過程中富有創造性的審美再現都是翻譯美學的范疇。總而言之,翻譯美學是基于美學基礎的研究,作為一門從美學視角研究翻譯的學科,也與每個在翻譯領域進行研究的人密切相關。
三、《畫中情思》漢譯本的語言特色
(一)大量疊音詞的運用
漢語具有音樂美。眾所周知,漢語是聲調語言,由四個聲調組成,抑揚頓挫,具有一定的音樂美,其中,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疊音詞較為豐富,讓讀者聞其音而感覺其美,使語言更加形象生動,讓文章生氣勃勃,不致枯燥。此外,漢語還有連綿詞,連綿詞是雙聲疊韻,可以強化音韻美的構詞方式。在《畫中情思》中譯本中體現如下。

這是我快樂的真正源泉。你大概看到剛剛過去的那兩個孩子,他們圓鼓鼓的小臉紅撲撲的,笑得那么開心,眼睛又是那么明亮!
“紅撲撲”、“圓鼓鼓”這兩個疊音詞很好地表現了小孩子天真可愛的一面,使一個個活潑可愛的小孩形象呼之欲出,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眼前。而原文使用的是(直譯:男孩那粉紅色圓圓的臉蛋),雖然這樣譯也未嘗不可,但會減少不少美感,而且體現不出漢語中的音韻美。譯文用擬聲疊音詞描寫孩子的臉蛋,既生動形象又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美感。另外,“源泉”這個詞看似普通,其實是漢語連綿詞,雙聲疊韻,起到加強音韻美的作用。

蒙拉差翁·吉拉娣神采奕奕地下了車,可是我的心卻砰砰直跳。
她輕輕地問了我一句:“諾帕朋,準備好了嗎?”
這是蒙拉差翁·吉拉娣與諾帕朋在山鷹一吻后,見昭坤前的一幕,將蒙拉差翁·吉拉娣和諾帕朋當時的神態進行對比,將譯為神采奕奕十分貼切自然,襯托出蒙拉差翁·吉拉娣的鎮定自若和大氣十足。而砰砰直跳是個擬聲疊詞,為了襯托諾帕朋的忐忑不安。而原文用的是(心跳有點厲害),“砰砰直跳”這個擬聲詞讓讀者如聞其聲,增添了幾分音韻美。“她輕輕地問了我一句:“諾帕朋,準備好了嗎?”“輕輕”這個疊音詞表現出蒙拉差翁·吉拉娣也看出諾帕朋內心的緊張和不安,盡量用溫和的語氣緩解諾帕朋內心的慌張,同時又富有美感,襯托出蒙拉差翁·吉拉娣的溫柔善良,用得十分恰當。可見,這些疊音詞和擬聲詞的使用都增加了文章的音韻美。
(二)用詞特色
漢語是一門優美的語言,歷經千錘百煉、飽含歷史文化積淀的漢語詞匯呈現出豐富而生動的美。《畫中情思》中譯本在詞的選用上的使用可圈可點。其中在《畫中情思》表現最明顯的是四字成語以及動詞的運用。它是經過長期使用、錘煉而形成的固定短語,充分體現了漢語的博大精深。動詞的美主要在于它的靈活多變,表現力極強。動詞可以盡展“動態之美”,特別在刻畫人物上,給讀者形象、真實、身臨其境的感覺。因此,《畫中情思》中譯本很好地運用了漢語中豐富的動詞進行翻譯,讓語言更加優美形象。
2.1四字成語之美

那天夜里,我懷著成功的喜悅得意洋洋地回到住處,自己也覺得事情辦得出人意料的好。
夫人真是妙語連珠,處處都顯出了過人的聰明,我真是望塵莫及。

2.2動詞之美

我是受之有愧的,夫人對我實在太好了。我說完之后笑了笑,沒有顧忌到我的話是否會刺傷她的心。是以否定句式表達,(直譯:“我怕

我凝視著她的身體,一種愛憐和眷戀的感情涌上心頭,使我肝腸欲斷。
譯本運用了翻譯中的“加法”,增加了“一種”,“涌上心頭”等詞。原文直譯為“我充滿愛憐地凝視她的身體,心都碎了。”譯成“凝視”這個動詞非常貼切,充滿深情。同時,原文并沒有使用“涌”這個動詞,但譯文使用“涌”這個動詞后,讓語言更加形象生動,將諾帕朋在知道真相后,對蒙拉差翁·吉拉娣那種愛憐和傷感的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肝腸欲斷”這個詞也體現了用詞美,表達出諾帕朋內心的懊悔和悲痛欲絕。這句話結合了動詞和成語之美與一身,使譯文更加出彩。

蒙拉差翁·吉拉娣盡管表面上那么溫柔、文靜,但誰也不難看出她的內心的欣喜和總是掛在臉上的淡淡紅暈。
(三)句式特色
句式錯落有致,語言靈動自然是語言有文采所表現出來的一種變化之美,這種變化集中體現在句式的選用上。句式特色,是《畫中情思》這部小說最突出的地方。所以,才能作為泰語語文的必讀書之一。句式美主要體現在譯者根據敘述的需要和表達的要求和漢語的習慣表達,在尊重原文內容的基礎上,靈活將原文翻譯成整句和散句、短句和長句,在句式的變換運用中.所選用的句式得當,會給譯文帶來渲染環境、突出了人物性格、豐滿了人物形象等作用。句式的變換包括整散相間,長短相諧,錯落有致。句式美也包括各種修辭手法的運用,每種修辭手法的運用都具有不同的作用。在《畫中情思》的中譯本中就有不少譯的優美的句式。

在我眼里,夫人好似清晨的彩霞,雖然我不愿意把你比作黎明的曙光,你的容貌將會經久不衰。
譯文很好地傳達了原文所要表達的含義,句式轉換的手法。文中的是清晨的意思,在泰語中的詞義比中文更廣,象征著清晨的一切美好和有生機活力的事物。(直譯:夫人的年輕的美貌還在清晨。)這樣翻譯不符合中國人的表達習慣。因此譯者將這個句型變為比喻句式,用“清晨的彩霞”比喻將蒙拉差翁·吉拉娣的容顏。同時,(直譯:“您美麗的容顏還能保持很長時間”。)直譯平淡無味,譯文用了“你的容貌將會經久不衰”,更符合中文的表達方式,運用了成語,富有美感。可以看出,譯者擺脫了原文語言形式和思維方式的束縛,用優美的中文語句將原文準確地表達出來,顯示了漢語的美感和魅力,體現譯者審美意識之高。

蒙拉差翁·吉拉娣掰開我的雙手,輕輕地推了我一把。我驟然變成了一直羔羊順從地放開了她。她倚在樹上喘息著,好像經過長途跋涉一樣,顯得十分疲乏,原本緋紅的面頰一下子變得更紅了,就好像被火熱的太陽燒灼過一樣。
句子是由詞和短語所組成。詞或短語用得好與壞,直接影響到句子和文章的和諧與優美。譯文用了“輕輕”“驟然”“長途跋涉”等詞語,都是在保持與原文意思一致的情況下選用的,既提升了語言的層次,也增添了句式美。直譯是:
“我順從了,立刻變成一只小羔羊。”這樣翻譯顯得拖沓,不利落。譯文則進行了合譯,將兩小句話變成完整的一句話,長短句錯落有致,語言結構流暢自然。(快速、立刻) 譯文將其翻成“驟然”更加貼切準確。譯文中“被火熱的太陽燒灼過一樣”也譯得十分出色。原文是,原文中省略了(陽光)這個詞,因為在泰語里根據語境可以理解為火熱的陽光灼燒。但中文不能省略,省略了句子將不完整,因此這句話在漢語翻譯中加進了“火熱的太陽”使句子優美完整。短短的一小段話就運用了兩個比喻,可見《畫中情思》這部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比喻修辭方式。

我那顆一直在愛情的王國里游蕩的心也就一點點收了回來。
譯文運用的比喻、擬人的手法和原文運用的修辭手法是保持一致的。譯者增加了“一直”、“一點點”這兩個修飾詞,為的是讓漢語的表達更加優美、貼切。“一直”是為了表達諾帕朋對蒙拉差翁·吉拉娣思念和愛并不是虛假的,短暫的。“一點點”是一個程度詞,表示諾帕朋的愛不是突然消失,而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慢慢的平靜下來。另外,這句話譯文的句式表達、句子結構與原文不一樣。原文是是“讓心(靈)回復原狀”的意思。而譯文是“心收了回來”。譯文用了“收”這個動詞,也是擬人的手法,增加了視角效果,讓語言更加生動形象。這也是兩種語言表達異樣的一個例子,可見譯者的審美意識高,對原文的理解和原語的轉換較好。

“我死了,沒有愛我的人;
但是我感到滿足,因為我有了我愛的人。”
這句話是《畫中情思》最經典而最富深意的。讀過這本小說的人都會記得這一句話。譯文也盡量按照原文的格式直譯,這句話富含深深意蘊,給讀者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傷和感動。前半句(我死了,沒有愛我的人)帶有一些悲傷和自憐的語氣,而后一句筆鋒一轉(但是我感到滿足,因為我有了我愛的人。)一個“但”和“滿足”表現出也暗示蒙拉差翁·吉拉娣對諾帕朋的愛是成熟的、深沉的、無私而偉大的。蒙拉差翁·吉拉娣并沒有因為自己沒有得到諾帕朋的愛而感到憎恨、懊惱,相反,她的豁然大度讓讀者更加為其感動和憐憫,整個烘托出這個人物的悲劇性,不需要用文字做過多的渲染,這句話已經足以總結蒙拉差翁·吉拉娣的一生。在她看來的滿足卻成了世人的一聲嘆息,這句話立意新穎、語言表達樸實動人,意蘊深遠。全文也因這句話而結束,原文和譯文都用簡練、工整和如詩一般的語言詮釋這部小說的內涵。
四、結 語
筆者發現《畫中情思》中譯本運用各種句子結構所創作的美感是最多的,也可以從側面反應在翻譯中運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句式來達到譯本的美感是常用的手段之一。當然,譯者也盡量保持原文的原貌,不做過多添加和詮釋,通過提煉自己的語言,用最貼切的語言再現原文之美,盡量保留原文的寫作風格和文化特色。此外,譯者為了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和達到漢語的語言美感,譯者的使用不少翻譯手法和技巧,在翻譯美學中稱為翻譯中審美再現諸手段。即增詞法、減詞法、引申法、反面著筆法、分譯法等手法,譯者不受原文語法結構的限制,而是要在深入理解原文語法關系的基礎上擺脫原文語法結構的束縛,用地道的漢語將原文內容表達出來。
通過對《畫中情思》中譯本的分析研究后,筆者認為欒文華、邢慧如翻譯的中譯文忠實地再現了原文的內容和審美品質。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泰譯中的優秀文學作品。由此可見譯者的審美意識之高,翻譯功底之深,譯者在深入理解、把握原文的基礎上,用自認為最佳的譯語將其表達出來,形成譯文,是完整的、客觀的對現實的反映,《畫中情思》中譯本也是后人學習和借鑒的優秀譯作之一。
[1] 李健.西烏拉帕及其成名作《畫中情思》 [J].外語教學.1985:84~86.
[2] 劉宓慶.章艷.翻譯美學理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北京.2011: xxv: 29:100:111:119-120~124,339~357.
[3] 毛榮貴.翻譯美學.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1:7:10~13:42.
[4] Smyth David.(2000).Translation of Behind the Painting. Chiang Mai:Silkworm Books.
[5] 西烏拉帕,欒文華、邢慧如譯.《畫中情思》[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
[6] 傅仲選,實用翻譯美學[M],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64.
本文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高層次人才項目非通用語種項目資助的“翻譯美學視角下泰國近現代文學作品漢譯本研究——以《畫中情思》和《四朝代》為例”項目(GWTP-FT-2014-1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