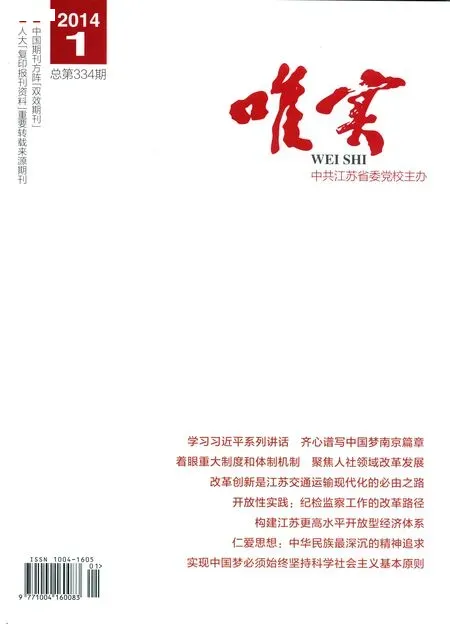新時期全面從嚴治黨的生動實踐
黃紅平
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信念堅定、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政治優勢和力量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肩負起偉大歷史使命,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關鍵在于加強紀律建設,嚴明黨紀。為積極準備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共中央印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簡稱新《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簡稱新《條例》)。新修訂的兩大黨內法規通篇貫穿“全面”與“從嚴”兩個關鍵詞,吹響新時期全面從嚴治黨實踐的號角,值得廣大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認真研讀。
一、修訂邏輯:舊《準則》和《條例》的局限性
古人曰: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相對于許多資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就是紀律嚴明。如果沒有鐵的紀律,黨就會成為一盤散沙,就沒有凝聚力、戰斗力和生命力。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完成十八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和艱巨任務,必須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要求落到實處。“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要靠嚴明紀律,”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把有紀律放在最前面,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是決定黨能否堅持革命、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首要條件。”歷史經驗一再表明,“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如果黨紀成為擺設,“就會形成‘破窗效應’,使黨的章程、原則、制度、部署喪失嚴肅性和權威性,黨就會淪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任憑肆意發展,“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這絕不是危言聳聽”[1]33~34。正因深諳此理,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尤為注重依據不同時期黨內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與時俱進推動紀律建設。這次新修訂的兩大黨內法規,源于1997年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二者分別于2010年和2004年獲重新修訂,正式頒發。但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發展,舊《準則》和《條例》的局限性凸顯,迫切需要修訂。
在屬性上,黨紀與國法混同。從立規的邏輯基點看,“黨紀”與“國法”應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黨規黨紀保證著黨的理想信念宗旨,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底線;法律體現國家意志,是全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底線”[2]。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屬于國家公民中的先進分子,理應對其思想覺悟和廉潔自律等方面的要求嚴于普通群眾。舊《準則》和《條例》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紀”、“法”不分明,用管理國家公民的尺子看待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一個最突出的表現是,黨內規則混同于國家法律,黨規黨紀套用‘法言法語’,原《準則》和《條例》的許多規定都與法律條文重復,難以體現對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堅定理想信念、踐行黨的宗旨上的高標準、嚴要求”,“在實踐中管黨治黨不是以紀律為尺子,而是以法律為依據,黨員干部只要不違法就沒人管、不追究”,這樣就“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紀委成了黨內的‘公檢法’,紀律審查成了‘司法調查’,監督執紀問責無法落到實處”,“任何一個組織的內部規則都比國家法律嚴格”,何況“我們黨是肩負神圣使命的政治組織,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執政地位,更是決定了黨規黨紀必然要嚴于國家法律”,“如果黨員都退守到公民的底線上,就降低了黨員標準,全面從嚴治黨便無從談起,黨的先進性更是無從體現”[3]。因此,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前面,首要任務是解決紀法混同的問題。
在功能上,倡導與懲戒錯位。在國家法律體系內,憲法是根本大法,不同法律法規的內容各不相同。與國家法律體系類似,黨內法規體系以黨章為總章程,各項紀律在內容上應互有側重、在功能上亦各司其職,實現對黨章所倡導與懲戒內容的具體化和進一步闡發,共同筑牢黨紀黨規之籠。但由于最初《準則》與《條例》在屬性問題沒有正確區分,結果導致二者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文本表述出現“正面倡導闕如、反面懲戒繁瑣”的交叉問題。最鮮明的就是舊《準則》,本應緊扣廉潔自律主題,從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等方面開正面清單,重在立德,告訴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做什么、怎么做”,但它卻開出一份負面清單,提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不應該做”的事項——“8個禁止、52個不準”。很顯然,“8個禁止、52個不準”應該屬于《條例》規定的內容。譬如舊《準則》“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內容過繁,‘8個禁止、52個不準’難以記住,也難以踐行;凝煉正面倡導不足,禁止性條款過多,沒有體現自律的要求”,特別是“廉潔”的主題不突出,不能針對當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3]等等。再譬如,舊《條例》有79條的內容與《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國家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諸如此類的內容,使得《準則》與《條例》嚴重錯位。
在效果上,預想與實踐背離。古語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如果紀律不嚴,那么從嚴治黨就無從談起。應該說,無論是舊《準則》還是《條例》,其最初的立規意圖,均要求實現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實際效果。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已經查處的大量頂風違紀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黨員、干部對紀律規定還置若罔聞,搞‘四風’毫無顧忌,搞腐敗心存僥幸”[1]48。這充分說明舊《準則》和《條例》的相關規定嚴重滯后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實踐發展,未能充分考慮到日后黨的建設中可能產生的新情況、新問題,過于脫離實際,結果出現“有紀律條文但卻執紀效果不彰”的情形。譬如舊《準則》適用對象窄,僅針對縣處級以上黨員干部,且只針對廉潔從政方面,未能涵蓋8700多萬全體黨員在廉潔自律方面的總體要求。再譬如,舊《條例》針對黨員領導干部,沒有覆蓋全體黨員,特別是對貪污賄賂行為、違反財經紀律行為和失職瀆職行為等條款的事實描述,把國家工作人員、其他從事公務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作為違紀行為主體,突破黨內范圍,造成適用困惑,影響執紀實效;對許多違紀事實描述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描述,處分標準不清晰,造成執紀自由裁量空間大,處罰可能畸輕畸重,懲處寬嚴不一,影響紀律處分的公信力、約束力和執行力。
二、功能重塑:新《準則》和《條例》的大變身
文本變化。舊《準則》共4個部分、18條、3600余字,而修訂之后的新《準則》僅僅只有8條、309字,篇幅減少90%以上,幾乎是重寫。相對于舊《準則》,新《準則》在文本上主要有四大變化:一是黨紀名稱之變。把《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改為《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二是適用對象之變。由針對黨員領導干部擴大到面向全體黨員。三是要求范圍之變。從廉潔從政擴展為廉潔自律。四是條款內容之變。將舊《準則》中“8個禁止、52個不準”有關內容移入同步修訂的黨紀處分條例中,在宏觀上做出“四個必須”的總體要求,并根據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不同情況分層提出廉潔自律規范。整體表述如同革命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義明確、簡練好記,全然沒有舊《準則》那樣繁雜。新《條例》在文本上同樣有重大變動。舊《條例》共3編、15章、178條、2.4萬余字,新《條例》共3編、11章、1.7萬余字,新增、刪除和修改條文比例高達近90%,有的章節達100%,可謂“脫胎換骨”。同時,新《條例》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紀法分開”的原則,“去除現行黨紀處分條例中與刑法等法律重復的內容”,總共刪除79條涉及國家法律法規重復的條款。總則重申黨組織和黨員要自覺接受黨紀約束。分則規定,凡黨員被依法逮捕的,均中止黨員權利;凡黨員干部違法犯罪的,除過失犯罪外一律受黨紀處分,實現黨紀與國法的銜接。新《條例》將原10類違紀行為整合為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6類,使《條例》內容體現出監督執紀問責特色。
性質變化。這次修訂《準則》堅持“化繁為簡、突出重點、針對時弊”的原則,基于現階段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原則性的要求和規范,涵攝理想信念、黨的宗旨和優良傳統作風、道德情操、傳統美德,展現共產黨人和古今中外高尚道德追求,從高不從低,樹立高標準。相較于舊《準則》,新《準則》在性質上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主要體現為對廉潔自律這一修身問題,變“不準”為“自覺”,強調自律,重在立德,堅持正面倡導,為全體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樹立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高標準。在此意義上說,新《準則》屬于正面清單,是對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提出的義務性要求,有助于促進其修煉不想腐的境界。不同于《準則》修訂,新《條例》圍繞黨紀戒尺的要求,把黨章和其他主要黨內法規對黨組織和黨員的紀律要求進行細化,明確規定違反黨章就要依規給予相應的黨紀處分,開出負面清單,強調他律,重在立規,劃出黨組織和黨員不可觸碰的行為底線。特別是分則中的“六大紀律”,對于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所作所為,可以做到“對號入座”,不僅告誡哪類行為不能做,而且提出清晰的處罰依據和標準。雖然新《條例》在性質上相對以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但其內容規定得更具體化,更符合實際要求,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可以清晰界定《條例》的本來性質,有助于使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不敢腐。
文本之變與性質之變共同促成功能重塑。如果把全面從嚴治黨比喻是流水線,那么各項紀律規章就相當于每個生產單位。每個生產單位做什么,應該有明確的分工定位,否則就會出現雜亂無章的無序局面,導致整個流水線的阻滯,影響生產成效。與之相同,對于黨的紀律建設,清晰的功能定位很重要,什么紀律管什么、不應管什么,應該有分工。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一次對舊《準則》和《條例》的修改和增刪,從文本和性質的變化看,達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準則》和《條例》實現了各自的功能重塑。首先,《準則》的正面倡導功能重塑。新《準則》由過去的負面清單轉為正面清單,只提正面要求,不作任何禁止性規定,要求黨員正確對待和處理公與私、廉與腐、儉與奢、苦與樂“四對關系”,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在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方面有“四個自覺”,糾正了舊《準則》的功能錯位問題。其次,《條例》的反面懲戒功能重塑。無數的案例表明,黨員“破法”無不始于“破紀”,而如果黨員守住了紀律,就不至于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新《條例》堅持問題導向,不僅整合了舊《準則》和《條例》中的有關條款,而且回應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實踐中的新情況,如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非組織活動、不如實向組織說明問題等。其價值在于強化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做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5]。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通過抓早抓小,真正體現出對黨員的嚴格要求和關心愛護。
三、內在價值:實現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的結合
紀律于政黨是生命線,于黨員是高壓線。當前,“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艱巨繁重的任務和人民群眾的期盼,黨自身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正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所指出的,“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黨的領導弱化、管黨治黨不嚴、責任擔當缺失,對黨最大的威脅莫過于此”。因此“新形勢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依然要靠理想信念宗旨的引領,靠嚴明紀律作保障”,重拾革命時期兩大制勝法寶。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所披露的大量腐敗案件表明,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個體出現這樣那樣的墮落情形,從根本上說還是在“德”和“紀”兩個方面出了問題。“不奮發,則心日頹靡;不檢束,則心日恣肆”。鄧小平指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有理想,有紀律,這兩件事我們務必時刻牢記在心”。實踐同時證明,管好治好一個擁有8700多萬黨員、在13億人口大國執政的黨,不靠思想教育不行,光靠思想教育也不行;不靠制度不行,光靠制度也不行。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在本質意義上說,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的辯證統一,即是要求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緊密結合。新《準則》和《條例》的內在價值,就在于既明確崇德向善的高標準,又劃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既賡續“思想建黨”的傳統,又確立“制度治黨”的規矩,自律與他律互補、樹高標與守底線兼顧,讓全面從嚴治黨匯聚道德感召力和紀律約束力,道德有紀律的保障,紀律有道德的認同,體現出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有機結合的管黨治黨新思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認識和實踐認識達到新境界。
堅持思想自律,實現以德治黨。古人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實踐證明,“對黨員、干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6],特別是“如果理想信念動搖,就會精神懈怠、意志消沉,淡化黨的觀念、漠視黨的紀律,最終滑向違紀甚至違法”[3]。黨的十八大以來所查處的大案要案暴露出,當前有不少黨員領導干部“三觀盡毀、知行分離”,做“兩面人”,成為塌方式腐敗的“塌方點”,根癥在于“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缺鈣”,得了“軟骨病”。具體表現是“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認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見的,是虛無縹緲的”[7],或者“有的干部自己認為最缺的是新知識”,忽視經常錘煉理想信念。因此,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邏輯基點,就是要堅持高標準在前,首先把黨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優良傳統和作風立起來、挺起來,這也是實現以德治黨的當務之急,為的是努力解決好“不想”的問題。新《準則》開宗明義提出“四個必須”,頭條就是堅定理想信念,其次才是黨的宗旨、優良傳統和作風、道德情操,足以突顯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這是共產黨人廉潔自律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6],尤值珍視。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像房間需要經常打掃一樣”,時刻拂去思想灰塵,決不做“失魂落魄”的信仰迷徒。
堅持制度他律,實現依規治黨。對于管黨治黨,特別是中共這樣一個黨員數量眾多的超大型執政黨,道德治理固然重要,但若缺失制度保障,哪怕曾經有效的思想建黨,最終也會隨著時代轉換失去作用。“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從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來的一些涉及領導干部的大案要案看”,“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敗,仍然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1]124。反映在黨內,所謂制度治黨就是依規治黨,其中“規”的含義就是加強紀律建設,尤其要把具有懲戒功能的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前面,這是管好黨和治好黨的根本之策。當前,“紀律松弛、組織渙散,正氣上不來、邪氣壓不住,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更有甚者,“有少數黨員干部政治紀律意識不強,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有的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見”,“有的黨員干部想說什么說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1]34,32~33,“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搞“七個有之”[1]50,嚴重損害中央的權威和黨的團結,亟待解決。新《條例》的重要亮點就是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既高度整合了過去行之有效的紀律和規矩,又充分吸納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經驗,明確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行為邊界,不僅體現了“懲”,而且體現了“治”,可以避免“好同志”與“階下囚”涇渭分明的局面。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2]王岐山.把紀律和規矩挺在法律前面[N].新京報,2015-05-11.
[3]王岐山.堅持高標準 守住底線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創新[N].人民日報,2015-10-23.
[4]王岐山.堅持黨紀嚴于國法[N].京華時報,2015-07-11.
[5]王岐山.全面從嚴治黨 嚴明黨的紀律 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N].光明日報,2015-09-27.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140-141.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11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建設馬克思主義廉潔型執政黨研究”(14YJC710020)中間研究成果〕
(作者系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
責任編輯:張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