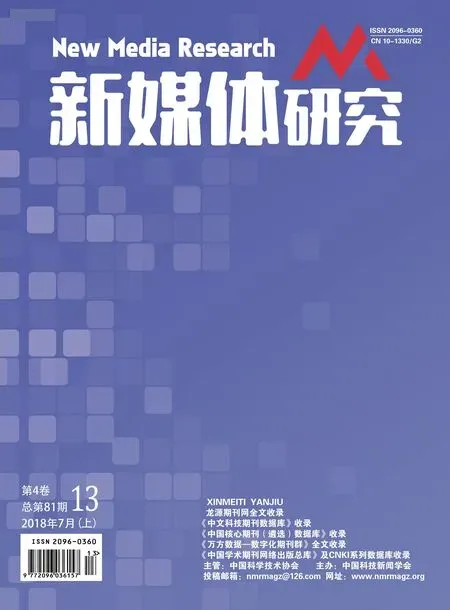大學生社交App使用狀況社會調查報告
羅茂林,呂 倩,孫思琪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大學生社交App使用狀況社會調查報告
羅茂林,呂 倩,孫思琪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本次調研的調查問卷設計在傳統的社交狀況多重要素設計之外,引入了“中庸思維量表”作為雙向測量標準。通過對大學生社交App使用實際情況數據的獲取(互聯網個體思維),與傳統的中庸觀念(群體思維)對比,比較觀察社交App對于大學生傳統的社會社交觀念的影響和差異。
中庸思維;App社交;大學生
在傳統西方傳播學框架下,學者們大多愿意將社會社交的狀況大致分類為“個體性”與“群體性”。與之對應的產生了相應的定義和研究范式。一般來說,我們認為西方人更具有“個體性”強調個性與個人的重要性;與之相反,東方人更注重“群體性”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整體的利益高于個人。
然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社會傳播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社交狀況不能用簡單的西方“群體性”范式來解讀。有學者就認為應當用儒家文化圈“關系取向”來定義這種社交狀況(何友輝等1991;楊國樞2004)。進一步來說更多學者愿意使用“關系”的范式取代傳統西方語境中“關系”(relation)來探討中國社交的取向。
本次調研選取了代表中國傳統社會核心觀念的“中庸思維量表”(吳佳輝2004)作為傳統思維傾向的測量量表。并且設計的調查問卷,就當前大學生社交App使用情況進行的測量。
1 中庸思維量表測定情況
需要注意的是,中庸思維量表在后期經過一次較大的調整,但是因為此次我們的測試不需要過于精確區別“認同中庸”與“反對不中庸”之間的差異,因此,由此造成的誤差對我們的研究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我們仍沿用操作性較強的舊表來完成調查。
“中庸思維量表”的統計方法是這樣的。被測試者可以從每道題中選擇A或者B當中的一個,然后在從1~5的同意量表中選擇一個程度,同意程度由小到大,該題得分為對應數字分數。當被測試者選擇的是反中庸的選項時,計分為反向。最后結果取平均數值。在中山大學2009年的一次大規模測試中,抽取的640個樣本中,由簡單“妥協”與“競爭”劃分出來的低中庸組的最終測試得分仍超過2.95分。以此可為我們的小規模測試提供參考對比。以下是我們此次測試的統計數據。現場參與者為40名志愿者,17男23女,統計數據如表1。

表1
對比2009年中山大學中得出的統計數據我們會發現,此次我們調查中中庸指數的最高值有所降低,即此次調查中顯示出大學生的中庸傾向有所降低。但是同時所有的數值均在2.5(均衡中庸指數)的附近,說明低程度中庸的人數反而也減少了。整個測試結果呈現正態分布的狀況。可見當下在互聯網的影響之下,傳統的觀念與思維對于大學生而言仍然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 大學生社交App基礎信息調研
互聯網所帶來的“個體性”的提倡,對于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種沖擊。本次調查則從社交App滲透時長、依賴替代傳統社交程度、App社交習慣等幾個方面設計問題,完成整個調研。此次問卷共計發放700份,其中有效問卷643份。
2.1滲透時長:年級越低,接觸移動社交App的時間越早
根據數據,2015級學生大多數在小學就接觸了移動社交App,而2011級以前的學生很少有從小學就接觸移動社交App的,這與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有關,而2012級、2013級、2014級大學生則比較
平均,既有從小學就接觸移動社交App的,也有到了大學才接觸的。
2.2對移動社交App的依賴程度
我們設立了三個問題來考察大學生對移動社交App的依賴程度,從數據上我們發現,每日使用移動社交App的時間大多在3個小時以上,而能夠不使用移動社交App的學生只占很少的比例。通過對兩組數據的交叉分析,我們發現,隨著每日使用移動社交App時間的增加,連續不使用移動社交App的時間就越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生對移動社交App的依賴程度和使用頻率有關。
2.3社交App使用習慣
在使用移動社交App的時候,大多數大學生都會去了解好友動態,比例占到了98.28%。這也體現出了現代大學生的交往方式,排名前3位的還有普通同學和家人。除非緊急事宜需要立刻取得聯系,否則App是大學生們聯系溝通的首選。毫無疑問互聯網社交App已經從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通訊交流手段。
在對移動社交App的整體評價上,46.55%的大學生認為利大于弊,但是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同學總數還是超過了半數,達到了53.45%(其中選擇說不清的占到了29.31%)。這說明對于移動社交App對于傳統社交的沖擊,半數的人態度復雜。
由于互聯網移動社交App在溝通連接上帶來的便利,人們對于溝通等待時間在意程度也有所提升。對于對方是否即時回復消息的容忍時間在縮短,有47.5%的樣本選擇不能接受長時間的無回復消息(30分鐘)。
3 總結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互聯網社交當前已經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大學生傳統的社交方式成為主要的溝通交流方式,但是對于其自身特點帶來的一系列改變(“個體化”意識)學生們的態度并非全盤接受,并且互聯網工具更大程度上是在傳統的社交框架下進行,即奉行中庸的傳統思維之下,利用互聯網實現良好的社交溝通。中國社會穩固的“關系取向”幾乎在互聯網時代被放大而并沒有消亡。
[1]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79.
[2]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廣西:廣西文學出版社,2008:2-43.
[3]陳家映.東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35.
[4]翟學偉.關系研究的多重立場與理論結構[J].江蘇社會科學,2007(3).
[5]吳佳輝.中庸量表的編制[D].臺北:臺灣大學,2004.
G2
A
2096-0360(2016)13-0048-01
羅茂林,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3級本科生,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
呂 倩,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3級本科生,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
孫思琪,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3級本科生,研究方向為新聞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