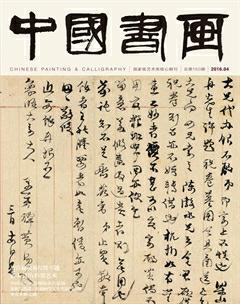潘玉良的彩墨藝術
賈方舟



20世紀之前的中國美術史,幾乎沒有女性藝術家的位置,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國自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畫家卻是一位女性——帝舜之妹顆手,她甚至被推崇為中國繪畫的“創始人”,被史書稱為“畫祖”,《世木,作篇》《畫史匯要》《書塵》《漢書·古今人表》等歷史文獻中均有關于她的記載。盡管中國繪畫由一位女性藝術家所開創,但在數千年的中國繪畫歷史中,顆手卻處在一種“缺席”狀態,即使偶然被提及,與其藝術成就相比也是無足輕重的。進入20世紀,在巨大的社會變革的推動下,中國婦女的歷史境遇也作為一個時代的課題被提了出來。隨著知識女性的覺醒、思想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她們開始走出閨閣,在藝術士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活躍狀態,潘玉良正是這一歷史潮流中的一個佼佼者。
馬克思曾說,全部人類史,就是一部五官感覺的發展史,但在男權社會的知識體系中,婦女的感覺經驗一般被排除在知識話語之外。人類的美術史幾乎是一部男性的視覺經驗史。男人掌握著話語權,而婦女卻像啞巴一樣長期處在“失聲”的沉默之中。所以,女權主義者認為在男權社會中,語言本身就對婦女構成了壓迫,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就繪畫而言,女畫家們也可以和男畫家一樣用相同的語言方式去畫人物、畫風景,或畫山水、畫花鳥。在這個領域,她們也可以在藝術上達到與男性同等的高度,并憑著她們的才氣和藝術造詣,在男性視覺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這些藝術中的明亮音符,終究還不是女性的聲音,只能是男性視覺文化的一部分,它沒有形成女性自己的話語,因而不是女性按照自己的體驗重新來解釋世界的。一個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經驗的群體,必然是一個沉默甚至被埋沒的群體;只有當能用自己的話語重建現實時,她們才能獲得表達個人經驗的權利。而女性藝術家一旦將探尋的目光轉向自身,轉向個人經驗的陳述和心靈事件的表白,這些深潛的情感領域便成為建構女性話語的理想境地。
與數千年的封建專制不同,20世紀中國女性藝術的發展是在“女性解放”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隨著殖民強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和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出現,中國女性作為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群體,也開始從一種蒙昧狀態中覺醒,結束“目不識丁,足不出戶”的歷史,從閨房走向社會,參與到各種政治和文化活動中來,成為新一代的女性。
20世紀前半葉,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最為開放的一個時期,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接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又向傳統文化發起全面挑戰,從而使中國的新文化、新藝術進入廣個勃興時期。在這樣一個開放的文化環境中,中國女性藝術家的繪畫活動也呈現出一種異常活躍的局面。這一時期的女性藝術家,體現為三種不同的取向:一是投身于社會革命,以變革社會為職志的藝術家;二是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以建樹新文化為目標的藝術家;三是以藝術修身養性,作為高雅消遣的“閨閣派”藝術家。其中,第二類藝術家多是受新文化思想影響的“新女性”,她們對傳統文化抱持的態度,決定了她們在藝術取向上不可能再回到傳統的程式之中,她們大多投入西學熱潮,到西方的新藝術中去確立自己的價值取向。
這一類型的藝術家可以舉出不少但最值得提及的,是潘玉良(1895-197力。她是創作最豐富、成就也最高的一位。她的一生經歷坎坷,自幼家貧、父母雙亡,8歲時由舅父撫養,14歲時被賣給煙花樓,受盡屈辱,17歲被蕪湖海關監督潘贊化贖出,前往上海做了潘贊化的二房太太,并改張姓為潘姓。19之。年考入上海美專。1921年赴法留學,先后在里昂國立美術學校和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就讀。1925年入羅馬皇家美術學院深造,曾多次獲得意大利政府給予的獎金。1926年其作品在羅馬國際藝術展覽會上榮獲金獎。1928年回國,應聘為上海美專西洋畫科主任。1929年在中央大學藝術科執教。從1928年起先后五度舉辦個人畫展,也是近代以來第一位舉辦個展的中國女藝術家。1937年因迫于家庭糾葛再度離開故土,定居法國,直至離世。
潘玉良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僅以油畫著稱,還兼作雕塑、中國畫、版畫等。藝術面貌也不拘一格,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探索軌跡,從傳統的寫實風格到印象派、野獸派風格,她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鑒、涉獵。她還嘗試在藝術中融入東方情調,尋找一種與中土文化相聯系的藝術情韻。但是,潘玉良的藝術最具價值的部分我以為還不在于其作品的形式,而在于她用直率的畫筆所表現出來的那些與自身經歷相關的主題。可以說,她是中國女性藝術家中最早將視角轉向自身、最早關注到女人的生存狀態的藝術家。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許多年中,很少再看到如她那樣流露出強烈的女性意識的作品。因此,她不僅是20世紀中國第一位最有影響的女藝術家,也是中國女性藝術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潘玉良生于1895年,與徐悲鴻同齡,又和他先后赴法留學。他們作為20世紀中國早期的開創性藝術家,都面對著相同的時代課題,都處于相同的文化語境之中;所不同的是,他們各自的個人經歷、性格氣質,特別是性別差異決定了他們不同的藝術走向。但在面對共同的時代課題時,他們又不謀而合,在中西融合這條路上走到了一起。
從她的彩墨畫作品中不難看出,她是如何從西方的“油畫系統”逐步轉換到一種東方式的表達。這種轉換不只表現在工具材料的不同選擇上,還在于表現方式和表現觀念的不同,所以潘玉良在畫了多年的油畫之后,開始嘗試用中國的傳統方式作畫并不是偶然的。第一代油畫家中有相當一批人都做過這種努力,用吳冠中的話說叫“水陸兼程”,“兼”到最后有些畫家干脆落腳到水墨畫中來,不再畫油畫。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關良等都是如此。這種情況在日本就不存在。20世紀早期,日本的“洋畫家”和“日本畫”畫家陣線分明,沒有一個洋畫家還兼作日本畫的。明治維新運動的口號是“脫亞入歐”,徹底西化,所以,學洋畫的不會回頭再畫日本畫。但在中國不同,所有到西方學習洋畫的回到國內都會面對一個共同的時代課題:如何把西方藝術融匯到本土藝術中來,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叫“歸根返本”。潘玉良即使又返回巴黎定居,依然沒有放棄對這一時代課題的思考并且付諸實踐性的探索。
潘玉良嘗試在宣紙上作畫是在之。世紀40年代,大部分作品產生于五六十年代。題材基本沒有離開“女性”這個主題,并且多以女人體的方式表達,或站,或坐,或梳妝,或母子對語。基本手法是以線勾勒形體,再施以色彩,并且一般都作背景處理,很少純粹留空白。少數作品也接近“寫意”的筆意,但也非傳統的書法用筆,只是接近速寫的畫法。從風格上看,與徐悲鴻早年畫的那種半工半寫的人物接近。因為要遵從造型的準確,很難放筆直抒胸臆,但從她的以線造型的彩墨作品中,不難看到她堅實的學院寫實的造型功力,且她力圖把這種寫實精神體現在以線造型的中國水墨畫的格局之中,力圖走出一條中西融合的路。
如果從水墨畫的傳統文脈這一角度看,潘玉良彩墨的最大貢獻是通過人體這一西方常見的題材來表達她對女性群體的關注。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水墨畫中,還沒有一個畫家像她這樣持久地、一而再地以女人體的方式展開她的經驗敘事。不能把潘玉良的女人體等同于常見的風景、靜物、人體等學院題材,她是20世紀中國最早具有女性意識的畫家,借助這一題材所訴求的是這個弱勢群體的命運、飽受磨難后的內心孤寂與無助,當然也包括她通過“母愛”這一主題對偉大母性的歌頌。這些畫不僅與她個人的經歷和身世有關,也與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有關。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當代藝術中,女性藝術是廣受矚目、非常活躍的一道風景。女性藝術家在這一時期所展開的自我探尋之路,最早可追溯到女權啟蒙時代的潘玉良。這一歷史階段始于康梁的維新運動。正是康有為、梁啟超這些啟蒙大師首先提出了“廢纏足、興女學”的口號對婦女幾千年來的種種遭遇寄予深切同情。而接下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又使知識女性尋求自立自主的解放斗爭更加深入,從而能以一種平等的身份參與到藝術與文化活動中來,充分展示出一種“新女性”形象。如何評價女性藝術家在這一時期取得的藝術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藝術活動已成為女性參與社會、參與文化的標志,藝術創造已成為女性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的象征。而潘玉良的藝術,正是標志了女性的個性解放和女性意識的萌動。作為一個知識女性來說,潘玉良是最早意識到自己人格尊嚴的藝術家,也是從西方留學回來后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文化活動和藝術教育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藝術家。
責任編輯:宋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