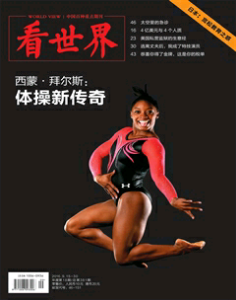太空里的急診
蘇禾
6月18日,44歲的英國宇航員蒂姆·皮克在國際空間站完成6個月的太空任務后回到地球。當6個月前他被送入預定軌道時,他便意識到,在國際空間站停留期間,他必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責——雖然他只經過40個小時的醫療培訓。在那段培訓經歷中,除了掌握一般的急救技巧,他還學會了如何縫合傷口、打針,甚至拔牙。
美國宇航局為宇航員們提供的醫療培訓涉及國際空間站上最常見的醫療問題,包括暈眩、頭痛、背痛、皮膚炎癥、燙傷、牙疼等緊急情況。而一旦面臨更嚴重的醫療緊急狀況,他們又該怎么做呢?在國際空間站內,最基本的醫藥箱包含一個急救箱、一大本醫療指南以及一些實用的醫療設備,包括除顫器、便攜式超聲波儀器、眼部檢查設備以及2升裝生理鹽水等裝置。
雖然這些輕量級超聲設備可以幫助他們生成非常清晰的體內照片,并將它們及時傳回地面尋求診斷幫助,但是在國際空間站上沒辦法解決根本問題。

有一個較優的選擇是利用停靠在國際空間站的聯盟號宇宙飛船,經三個半小時的旅程后將病人送回地球。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倫敦國王學院航空航天生理學系高級講師大衛·格林博士認為:“國際空間站的資源有限,聯盟號飛船上也沒有配套的生命維持系統。如果能夠順利飛回來,宇航員都要承受4到5G的重力加速度重新進入地球大氣層,這對身體正常的人來說都是極不舒服的,更何況是病重之人。”
在被送入太空前以及停留國際空間站期間乃至返回地面后的將近一年時間里,所有宇航員的身體健康一直受到密切關注。地面控制中心的團隊會全天候地監視太空中的宇航員,收集他們在空間站的所有行為數據。格林博士透露,數據結果分析顯示,宇航員感染嚴重疾病和需要重癥監護的風險是非常小的,不過仍有1%-2%患重病的幾率,這也意味著遲早有可能發生醫療緊急狀況。
今年4月24日,2016年倫敦馬拉松比賽日,蒂姆·皮克在國際空間站的跑步機上也完成了42.2公里長的馬拉松賽程,歷時3小時35分,只比他此前參加過的倫敦馬拉松比賽最好成績慢16.5分鐘。在40萬米的高空、圍繞地球旋轉了大約兩圈半,皮克打破了太空宇航員的馬拉松紀錄。幸運的是,在國際空間站期間,蒂姆·皮克并沒有遇到任何健康問題。
面臨醫療問題嚴重挑戰的并不局限于國際空間站。美國馬里蘭大學重癥醫學科博士弗雷德·帕帕里,曾在海地和南蘇丹的醫院急診部門工作過一段時間,目睹過在沒有自來水沒有電力供應的簡陋醫院里,如何通過超聲波檢測快速診斷并挽救生命的醫療急救案例。他表示來自世界各地許多偏僻地區的經驗值得借鑒。
在他看來,與世隔絕的國際空間站,與貧窮國家醫療匱乏的農村偏遠地區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處。醫生通過視頻或音頻進行遠程治療,對國際空間站的宇航員來說非常重要,而這種遠程醫療應該在發展中國家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如果在緊急情況下能夠通過遠程醫療向有經驗的醫生請教或獲取相關信息,這種低成本的干預措施往往可在生死關頭起到積極作用。
這并不奇怪,航空航天技術能給受災地區、高海拔地區以及偏遠地區帶來極大益處。這些地區對醫療設備的需求與太空醫療設備非常相似,都要求小巧、輕便、堅實、智能和低功耗。因此美國宇航局和歐洲航天局找到了新的業務增值點,它們將與醫療和科學組織展開更廣泛的合作,分享航天科技創新所帶來的便利。
訓練人員正確運用航天技術也很重要。就如蒂姆·皮克接受培訓使用醫療設備,使他能基本勝任太空護理任務一樣,類似的培訓可以在醫生和醫護人員短缺的地區大力開展,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
隨著載人航天飛行任務的計劃已經從月球擴展到火星以及其他星球,配備更加完善的太空醫療緊急救護措施也是迫在眉睫。
讓宇航員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或可能部分解決離地球萬里之外的緊急醫療狀況。這頗有點像科幻電影《星際穿越》中“企業號”飛船的宇航員那樣。但是,在太空中進行緊急手術能成為現實嗎?目前來看,在微重力環境下進行手術是不現實的,因為血液和體液會從病人體內流出來,漂浮在空中,很有可能會感染其他宇航員、污染飛船。
美國科學家一直在做實驗,想用一個透明圓頂罩住傷口上部,然后用生理鹽水將其填充,以阻止血液流動。這種方式被認為可以用來止血,給外科醫生留有充足的時間來封住傷口。
美國宇航局還計劃把機器人送入太空擔任外科醫生。太空機器人2號已經登上國際空間站,執行來自地球遠程控制的基本醫療功能。而科學家最終的目標是要讓機器人通過編程能執行復雜的手術。當然這仍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由于執行太空任務時間過長,因此對太空醫療提出了更高要求:更智能的醫療設備,更長保質期的藥物,以及更廣泛的醫療培訓。當然,如果有一天人類登陸火星,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間的單向通訊會延遲20分鐘,快捷的遠程醫療指導也不太可能幫得上忙,一旦遇到緊急醫療情況,宇航員們又該怎么辦呢?只得說,航天醫學家們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