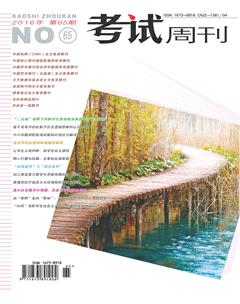語言學的任意性和理據性研究
臧志文
在哲學界,一直以來就存在唯名論與唯實論之爭。此爭議延伸到語言學界,演變為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與理據性之爭。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原則是頭等重要的原則,支配著整個語言的語言學。但國外以韓禮德和海曼為代表的諸多學者卻持不同看法。自20世紀80年代《普通語言學教程》在中國出版以來至今,國內語言學者對任意性原則持三種不同觀點:
一是以索振羽、徐通鏘等為代表的,持肯定觀點,堅持任意性是頭等重要的原則。語言的多樣性說明語音與語義的結合沒有必然性。從不同語言來看,同樣的意義在不同的語言中用不同的語音來表示,“魚”在英語和漢語中讀音不同,聽不出它們和水中游動的生物的形象之間有任何形式或功能的關聯。同一語言來看,同一個意義的語音形式在不同時期可能不同。比如眼睛,在古代漢語中稱為“目”,而后代稱為“眼”。即使是在同一時期,同一意義也可以有不同的稱說。如漢語中“父親”、“爸爸”都指同一對象,方言中還有“爹”、“大”等說法。如果語音和意義有必然聯系,就不會出現一義對多形或形式變化的情形。
二是以許國璋、李葆嘉為代表的,與之截然不同,認為語言符號不是任意的,是可論證的,李葆嘉甚至認為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原則實際上是一個虛構的原則。隨后很多學者從理據性和象似性的角度對語言符號任意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質疑。
三是以岑運強、張紹杰為代表的,持肯定并補充的觀點,既肯定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又承認語言符號具有象似性和理據性,認為它們之間是辯證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為了語言學的繁榮與發展,我們要對任意性重新加以審視,經過一定的整理和研究,我們對任意性和理據性之間的關系作總結。
1.理論基礎不同
任意性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框架中的一個基本原則。理據性是認知語言學和系統功能語法的一個基本原則。
2.研究角度不同
任意性考察的只是語言符號內音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自然聯系,必然聯系如生理的、本能的、或物理的,如“月亮”、“茶杯”、“桌子”等詞并不反映所指事物的任何物理屬性或特征,即我們不能從“月亮”、“茶杯”、“桌子”等詞的語音上知道它們的色彩、形狀、大小等屬性。“two”的聲音序列并不是one的兩倍,narrow的聲音序列要比wide長得多,我們學外語時遇到一個新詞,是無法從語音推知意義或者聯系的。在這一點上,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不同,非語言符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和所指事物的物理特征相對應,如交通標志中的右轉彎、十字路口、減速等和它們的所指對象在物理特征上就非常近似。非語言符號由于自然聯系的制約,缺少自由性與靈活性,功用非常有限。語言符號則超越了這種制約,任意地創造了自己的音義,形成了強大的自組織系統,可見,沒有任意性就沒有語言符號的存在。
對于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反例是擬聲詞和感嘆詞。擬聲詞感嘆詞所指是對某種自然聲音的模仿,但它們的存在并不能說明任意性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擬聲詞在語言中數量極少,并且從來就不是語言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它們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就是任意的,因為它們只是某些聲音的近似的,而且有一半已經是約定俗成的模仿。這些聲音只是為語詞的獲得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可能性,而不是像零度必然結冰、達到沸點水必然燒開那樣是事物物理屬性決定的必然結果。同一語言用不同的聲音模擬同一個事物發音,正是語言符號任意性最好的證明。比如,“喵喵”表示貓的叫聲,同時貓的叫聲既可以模擬為“喵喵”,又可以模擬為“喵嗚”,還可以模擬為“咪咪”、“咪嗚”。從不同語言對同一事物的模擬來看,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就更加明顯。鴨子的叫聲,漢語是“嘎嘎”,英語是“quack”;漢語把咳嗽這種癥狀叫做“咳”,英語則叫cough;漢語擬聲為“咔嚓”的,英語則是“crash”。美洲土著阿薩巴跟休部落語言幾乎沒有或者全然沒有擬聲詞。
擬聲詞感嘆詞一旦被引進語言,就或多或少要卷入其他的詞所經歷的語音演變,因而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某些特性。這種現象的產生還與人類的發音器官所能發出的聲音有限、語言運用的經濟原則有關,它們導致人們喜歡利用現有的聲音形式指稱新的事物。
理據性是指語言的音義之間的結合總是有一定的聯系、道理。語言符號是在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和認知水平制約下的必然產物,必然受社會、文化、心理等因素制約的理性的聯系,這些聯系就是語言符號的理據,隱藏在語言背后。理據性已將語言的內部機制與外部因素如社會、心理、符號和文化等方面研究相結合。當今的語言學的研究中心實際上已經由微觀語言學轉向宏觀語言學。
3.研究層面不同
任意性屬于普通語言學,世界上所有的語言無一例外;理據性屬于個別語言學。任意性體現聲音和意義結合的多種可能性,理據性體現的是一種結合現實。任意性總要變現成一種理據,理據性只是一種可能的實現,有了任意性,才使語言符號的理據生成具備了廣闊的選擇余地,語言才會如此豐富多彩,正是因為它的存在,語言符號才有機會不斷地發展演化。
人類盡管有基本相同的認知心理,但由于新事物與原有事物有多種多樣的聯系,各語言的原有面貌各不相同,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在各自理據的基礎上產生的語言符號各不相同,沒有通用于各種語言、各個詞的理據規則。目前,似乎還沒有人能夠舉出一個理據性具體例子后,能證明該例子的音義關系完全適合一切語言。
4.研究對象不同
任意性研究的是單個符號的音義結合的關系;理據性研究的是符號與符號之間的理據性,超出了單個符號的范圍。
單個符號的音義結合是不可論證的,但這些具有任意性的單個符號之間的組合卻是非任意的。例如,“美”與“瓶”不能組合成“美瓶”、“燙”與“額”不能組合成“燙額”、“香”與“衣”不能組合成“香衣”。復合詞內部語素之間的組合是非任意的,是可以論證的,這是造詞的理據。新詞的產生可以有多種途徑,可以借用外語,也可以利用原有材料重新組合,怎樣組合,也會有多種選擇。比如“一般按時間或里程收費的小型載客汽車”,借用英語詞就是“的士”。漢語自造的詞則有兩種:出租汽車、計程車,前者著眼于“供人臨時乘坐”,后者著眼于“按里程收費”,各有理據,但都合理存在。都合理的情況,恰恰說明哪一個也都不是唯一的、必然的結果:正因為語音和語義的聯系不是必然的,所以才會容許根據不同的理據來稱說。可見,同一語言內部,音義結合的任意性是基礎,而理據性則是相對的。
英語中“re”詞綴表示“再次”“重新”等概念,其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任意性含量就比用兩個形位組合而成的詞語reprint要高,因為該組合詞似乎與“再”和“印”在真實世界里的實際操作序列吻合,故其形式和內容兩者之間表現出一定的“序列象似性”,從而增強該符號的理據性。
在同一語言內,后起的詞語一般是以原有詞語為基礎孳生的。如漢語的“子”、“字”、“孳”讀音相近,意義上有聯系,一般認為是同一個詞“孽乳”分化的結果。為什么根據聲音可以推出同源詞呢?這是因為人類語言發展的初期,詞的音義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是社會約定俗成的。但是,在詞不斷增多的過程中,隨著詞義的引申,要在原來詞的基礎上分化出新詞,新產生的詞是由舊詞派生的,所以語音必然與舊詞相同或相近。
雖然在合成詞和派生詞及句法層面上的確存在理據性,但就單個符號而言,任意性依然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5.研究作用不同
任意性決定了語言的多樣性、語言的發展。理據性主要解決個別語言的探源問題,是探索性、解釋性的。
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取決于社會的約定俗成。同一社會在不同的時代,不論是語言符號的聲音形式,還是所表示的意義和二者之間的結合關系,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語音的演變,詞匯中新詞的產生、舊詞的消亡和同一個詞在不同歷史時期語義的演變,等等,都是社會約定俗成變化的具體反映。語言就是在社會約定俗成的任意性中逐漸豐富、日益精密起來的。音義結合的任意性是形成語言多樣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它使得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語言,使得語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
理據性關系的研究實用性很強,對語言教學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索緒爾的理論促進了漢語內部結構和關系的研究,對于人們了解漢語的內部構造起到了驚人的作用。理據性反映的是不同語言的文化背景、認知特點和語言特性,給語言的學習和使用帶來記憶的方便。這種語言的附屬價值,是語言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鑒于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與理據性之間的關系。
6.辯證統一、相互依存
通過對任意性原則及理據性理論的分析,我們發現,任意性與理據性是同一個語言符號的兩個方面。語言符號,孤立看待其本身的話,是任意的或者說沒有理據的,語言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時,是相對有理據的。理據性是對符號之間關系的一種描述或是符號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與任意性是兩個層面上的問題,兩者可以兼容。
結構主義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之間存在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可把理據性看做是任意性的發展補充。語言符號是任意性、理據性的統一。二者不可偏廢。夸大普遍的任意性,否定具體的理據性,這會使研究帶上神秘主義的面紗;夸大理據性而否定任意性,則必然走上唯心之路。古時候人們不明白詞語與客觀事物之間的約定性,而是把詞語與所指代的人或事物等同起來,從而產生了語言崇拜、語言禁忌等現象。總之,近幾十年來,索緒爾任意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們既要看到前人的不足,又要關注當今語言科學的新發展,相信在不斷地爭鳴與探討中必然促進語言研究的深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鳳,高航.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象似性與理據——索緒爾的任意性觀點和皮爾斯的象似性觀點解讀,山東外語教學,2005.
[2]劉曉明.語言符號任意性與理據性辯證關系研究,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3]何英.談索緒爾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原則.新疆財經大學學報,2010.
[4]高潁潁.語言符號任意性理論綜述及相關思考,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5]郭建芳,關于語言符號任意性、象似性和理據性的哲學思考,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0.
[6]岑運強,李海榮.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索緒爾語言符號任意性研究評介,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