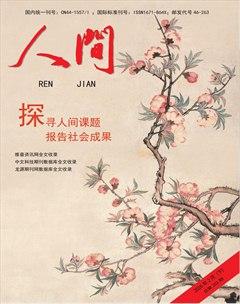追憶上海繁華舊夢
郭珺琪
摘要:王安憶是海派文學極具代表性的作家,在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不斷地把上,為我們展現了上海多樣的風情風貌,而她自己也儼然成為了上海的形象代言人。本文對王安憶的經典作品《長恨歌》展開,由這部作品實現了對上海的追憶,在老上海典型景觀上精彩描繪了弄堂、愛麗絲和平安里。在弄堂日常生活上著意表現了吃喝、打扮。在女性性格上深刻發掘了上海小姐的品格。從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上海文化特質。
關鍵詞:王安憶;《長恨歌》;上海;女性
中圖分類號:RSS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010-02
“現在上海已成了新話題,當時在圖書館,藏書樓,辛苦看到的舊書,如今大批量地印刷發行,用最好的銅版紙作封面。可在那里面,看見的是時尚,也不是上海。再回過頭來,又發現上海也不在這城市里。”
——王安憶:《尋找上海》
“我生活在上海,我對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語言,包括上海人的世界觀等一直都是潛心關注的。這些在我寫作時,都變成了有用的資產,必要的準備。”書寫上海是王安憶的人生情結,她不止一次的表示她對上海傾注了源源不斷的深情和關注。上海,是她的美好精神領土,在她筆下,上海這個繁華的都市不再是一個巨大的排斥其他城市的力量,而是可以被人們喜愛、傾情和認知的對象。
“《長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寫實的東西,在那里面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但事實上這個女人只不過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寫的其實是一個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 那《長恨歌》是如何追憶上海的繁華舊夢?王安憶通過弄堂、閨閣、愛麗絲公寓、平安里為上海樹立了典型的意象,為我們勾畫出一副上海的典型空間景觀,并呈現出了上海的獨特風度。
一、弄堂
《長恨歌》開篇提到:“站在一個至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
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街道和樓房凸現在它之上,是一些點和線,而它則是中國畫中稱為皴法的那類筆觸,是將空白填滿的。當天黑下來,燈亮起來的時分,這些點和線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上海的弄堂進入了《長恨歌》,并成為上海敘事的重要背景。上海的弄堂形形色色,王安憶在《長恨歌》中把弄堂概括為如以下三種:
第一種, “石窟門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權勢之氣的一種,它們帶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遺傳,有一副官邸的臉面。”這里居住著上海最普通的市民階層。《長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瑤家就坐落在這樣的弄堂里:前客堂里,多數有著一套半套的紅木家具;客堂里的光線卻總是有點暗,太陽在窗臺上找出一層層光圈;梳妝臺上,胭脂水粉總是容易受潮的樣子;樟木箱上的銅鎖倒是很亮,常開常關的樣子;地板下面,夜夜是有老鼠出沒的……
第二種,“上海東區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門是鏤空雕花的矮鐵門,樓上有探身的窗還不夠,還要做出站腳的陽臺,為的是好看街市的風景。”這樣充斥著歐洲風情的設計,閃現出上海曾經的繁華,也反映出上海人生活的精致。在這里生活著的,大多是新興的中小產業主,家底比較殷實,王琦瑤的小姐妹吳佩珍就是是在這樣的新式弄堂里長大的。
第三種,“西區的公寓弄堂是嚴加防范的,房間都是成套,一扇門關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架勢,墻是隔音的墻,雞犬聲不相聞的。”這種弄堂,在那個時代算是高級住宅,匯集在上海的西區,生活的多數是中上階層。蔣麗莉就是出生在這樣的上層家庭,在申江女中同學中屬于家庭條件最好的。
弄堂里的生活正是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的縮影,它呈現著上海市民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歸宿。因此,王安憶極力細致地刻畫弄堂,意義便在于展現上海繁華背后的市民精魂。
二、愛麗絲公寓與平安里
愛麗絲公寓和平安里是王綺瑤度過其傳奇一生的兩個重要地方。“這是個續羅和流蘇織成的世界,即便是木器,也流淌著綢緞柔亮的光芒。操盆前是繡花的腳塾,沙發上是繡花的蒲團,床上是繡花的帳幔,桌旁是繡花的桌圍。這又是花的世界,燈罩上是花,衣柜邊雕著花,落地窗是檳柳玻璃的花,墻紙上是漫灑的花,瓶里插著花,手帕里夾一朵白蘭花,茉莉花是飄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羅蘭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鳳仙花的紅,衣裳是雛菊的苦清氣。”住在這里的王琦瑤充滿了迷茫與彷徨,充滿了無盡的等候與守望。把她帶到這座公寓的李主任是當時社會上有身份的人物,既是軍政要人,也是商人,在老家有正房妻子,在北平和上海還有兩房妻室。在李主任心里,王琦瑤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對于王琦瑤來說,李主任則是她的一切生活,她在這座公寓里的所有守望都是為了他。像愛麗絲一樣的公寓,上海有許多,它們還有一個別名,叫做“交際花公寓”,“交際花”是上海這座都市的特殊產物。在這里,孕育了交際花們悲劇的人生。與紙醉金迷的愛麗絲公寓相比,平安里則是簡陋樸實的,王琦瑤在這里度過了一生中最為平實的日子。平安里的天生計,是在喧囂之中拉開序幕的,當夜幕降臨時,平安里又恢復了它往日的清潔寧靜。這是上海最普通市民的住處,人們吃喝拉撒全在這里,日子雖然拮據卻仍不失一分雅致。
如果說,奢侈浮華的“愛麗絲”是交際花文化的體現,那么樸實無華的平安里則是“石窟門”文化的體現。一個是上流社會的生活形態,一個是普通平民的尋常日子。交際花文化終究會跟隨歷史政治的洪流的幻化成為浮云,而石窟門文化則是印入到了上海普通百姓心中的上海文化精魂。
三、弄堂里的日常生活
王安憶在《長恨歌》中精心書寫了一個個上海的小人物,將他們日常的生活連接成一部獨特的上海日常生活史,呈現了上海的世俗風情,揭露了上海的文化特質。
(一)吃喝
《長恨歌》里對食物的描寫特別多,尤其是在平安里這個更接近上海普通人的弄堂里,王安憶讓小說中的王琦瑤做出各式各樣的吃食,雖不及饕餮大餐,但絕對是誘人可口的佳肴:用爐子烤山芋、朝鮮魚干、年糕片;用開水涮羊肉、下面條;用小湯匙做蛋餃;用小磨一點一點磨精米粉;用鐵鍋炒曬干的西瓜子……無論是正式的午飯晚飯,還是休閑的下午茶,他們都能吃出一份與眾不同的精致來。所以無論是像嚴家師母這樣的老一輩上海人,還是像老克臘這樣的新一代都喜歡到王琦瑤家吃喝,體驗老上海的細膩與別致。
(二)打扮
都說上海女人精致,懂得梳妝打扮。這與上海這座城市氣蘊是息息相關的。王琦瑤就是有自己的一套講究。她說過:“衣服至少是女人的文憑,并且這文憑比那文憑更重要。”嚴家師母也說過:“要說做人,最是體現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興趣和精神,是最要緊的”,這足以證實舊上海的女人們,把穿衣打扮看得極為重要,不單單要穿,還要穿出品位來。王琦瑤必然是這類會穿衣的代表。盡管搬到了簡陋嘈雜的平安里,她仍舊把自己料理得大方精致。焗了頭發,又從箱底翻出昔日的衣服,改一改又是新的了。她依舊化妝,修眉毛的鉗子、眉筆、粉撲一件件找出來擺 ,在鏡前打量自己,好像鏡子里的都是自己的老朋友,能與自己說話。她確實是明白打扮,無論出席什么場合,她都是收放自如,留有余地;出行置辦行頭依照她說的去做,總不會錯。縱然闊別了往日的繁華舊夢,王琦瑤對待日常生活的那份精雕細琢 ,那份考究的趣味是不會改變的。王琦瑤領悟了上海女人的精髓,保持著上海女人的姿態,總有著那份優雅從容。
四、王琦瑤——上海女性的代言人
《長恨歌》里王安憶寫到:“上海的繁榮其實是女性風采的,風里傳來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櫥窗里的陳列,女裝比男裝多。那法國梧桐的樹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夾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這城市本身就像是個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銀,五彩云是飛上天的女人的衣袂。”王安憶以她與眾不同的女性視角審視著這座城市,從城市與女人互相交融的深層關系中,發覺出上海的城市精魂。這精魂的集大成者正是“王琦瑤”這個上海女人。王琦瑤與上海這座城市相互映襯,她的一生命運就是上海日常生活的見證和上海性格的化身,而恰是上海的這種城市性格成就了王安憶的一生。那么剖析一個王琦瑤,便可懂得上海女人,便可看見整個上海的精魂。
(一)精致的女性
上海女人尋求時尚、講求精致是出了名的。但她們的精致與細膩,并不僅僅只是體現在穿衣打扮上,而是一種對自我和生活的要求,這種對于精致的執著己經成為他們的審美態度,貫穿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是把這種精致情調當成日子來過的。譬如旗袍的樣式,發髻的形狀,拍照的姿態,咖啡的香味,點心的花樣,帳幔和桌圍的繡花,香水的香型,這些小細節她們都很有講究。王琦瑤是上海女人的代表,她就深深領悟到了這優雅精致的精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時尚理念。這種精雕細作的態度,這種無處不在的優雅情調穿梭在王琦瑤的生活中。
(二)功利的女性
王綺瑤的骨子里天然地有一股驕傲和自尊,但這種驕傲又不是張揚踐唐,目中無人的,而是有張有她的矜持;她的精明,不是斤斤計較,小氣無理的,而是恰到好處的自我保護。她深諳人情世故,總能巧妙地處理好各種人際關系。上海這座城市是繁華和功利的,它的時尚是以這繁華和功利來打底的,這顆功利的心也驅使著人們在瑣屑的日常生活中蒸騰出一顆奮斗的心。
(三)樸實的女性
上海這座擁有著百年歷史的東方大都市,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較深,盡顯著時尚與繁華,但同樣也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務實、獨立、自由的風格,這尤其體現在上海女性身上平凡的上海女性,有著堅朝務實的精神。王琦瑤是個不一般的女人,在她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她可進可退,可攻可守,身上總有一股初勁和硬氣。在她的攻守之間,是一份不相信奇跡,只相信自己的自信。
王安憶在這部小說中創作的一幕幕的平淡無奇的私人生活場景,回避了浪漫、落寞的傳奇式的敘事模式。用反浪漫的敘述來描繪一個海派傳奇故事。正是清醒的、帶有輕微的反諷意味的反浪漫敘述才使得王琦瑤的私生活場景的現代性獲得了帶有后現代意味的反思色彩,否則,這個王琦瑤的故事將只能成為二、三流言情故事的骨架。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王德威教授由此欣喜地論斷“海派作家,又見傳人”,并且第一次將王安憶置于現代中國小說的一個流派傳統中考察辨析,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對于上海的追憶,王安憶是感性的,但在這種感性的想象中,她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這座城市的感受,既有對精致優雅氣質的追懷,也有對它逐漸走向粗鄙的不滿。王安憶希望通過自己的筆,寫出上海這個城市的氣質和神韻。
參考文獻:
[1]李歐梵.上海摩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王安憶.長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0.
[3]蔡豐明.上海都市民俗[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4]李潔非.城市像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5]王安憶.尋找上海[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