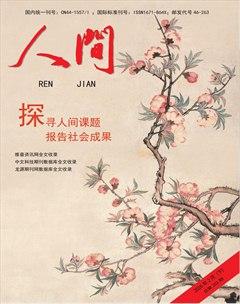從舞臺劇到電影
王自連
摘要:1986年,賴聲川等人集體創作的話劇《暗戀桃花源》在臺灣臺北市首次公演,反響熱烈。對于這樣的經典劇作賴聲川并沒有停下探索、發掘新意的腳步,時隔六年,賴聲川結合當時的社會因素將舞臺劇《暗戀桃花源》改編成電影,搬上了熒幕,影片《暗戀桃花源》用有別于舞臺劇的藝術形式將原著所要表現的內容“原汁原味”的呈現出來,這種忠實于原著精神的改編是值得肯定的。從舞臺劇到影片的變化,更讓觀眾喜聞樂見,擴大了傳播范圍及影響層面,這次的改編是成功的。
關鍵詞:《暗戀桃花源》;改編;話劇;電影
中圖分類號:J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2-0243-02
話劇《暗戀桃花源》講述的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劇組——《暗戀》劇組和《桃花源》劇組,由于劇場管理員的安排不當,導致兩個劇組同時在一個舞臺上排戲,就出現了《暗戀》劇組與《桃花源》劇組爭搶舞臺而互相干擾的局面。《暗戀桃花源》以其戲劇沖突的復雜性、結構的新穎、語言的極富表現力以及開放性的主題贏得了不僅是“下里巴人”觀眾層的喜愛,也受到了“陽春白雪”觀眾層的贊賞。面對眾多的殊榮和演出盛況,賴聲川并沒有停止對這個舞臺劇的更深層次的探索與挖掘,后來不斷創新的版本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情節的刪減
電影《暗戀桃花源》由林青霞擔綱主演,除了考慮形象氣質等因素外,無疑還有商業化的原因,因為這樣的明星效應會讓電影更加賣座。賴聲川并沒有因為要迎合市場而對《暗戀桃花源》展開大刀闊斧的改編,對于這部經典劇目,賴聲川是幾乎將他最初所要表現的思想都包含在了影片里。《暗戀》還是《暗戀》,江濱柳與云之凡的苦戀依然與時局相連,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微妙關系也由此傳達;《桃花源》還是《桃花源》,老陶對于春花和袁老板的失望讓人們聯想到自己對于生活的無力感,桃花源是老陶理想的家園,也是我們追求的“烏托邦”;《暗戀》與《桃花源》的碰撞依然讓人們看到了無序中的有序,暫時從混亂的生活中找到平衡點,兩劇的融合依然將主題升華到了大陸比之于臺灣就如劇中人所思念和追尋的“桃花源”。所以說,影片是“原汁原味”的展現給了觀眾的,最初要表現的主題思想與人文關懷一樣也沒落下,我認為,這是改編成功最重要的一點。
《暗戀桃花源》舞臺劇時長為三個多小時,而影片時長不到2個小時,受到時間的限制,不得不刪減其中的一些情節。《桃花源》中,1、在春花與袁老板故意用話激老陶去上游打大魚之后的一段對話:關于誰該離開這個家,誰該先開口捅破那層袁老板與春花私通的窗戶紙,被刪除了。這一情節的表演包含有戲曲中的一些身段表演和功夫表演,但是緊接下來的戲份中會有對上段表演的重復,甚至是更加精彩的表演(戲劇中的功夫“十三響”),所以舍去這一情節也無傷大雅。2、老陶在桃花源中與白袍男子、白袍女子討論關于打大魚與老婆偷人之間的關系這一情節也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袍男子的一句:“家里還有點小魚干……”(同時用小拇指比劃)。這一動作行為恰好戳到了老陶的痛處,讓他再次想到他的無能——既沒本事打大魚養家,也沒本事生孩子。白袍男子的這一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比較之前話劇的長對話,同樣能讓老陶“發瘋”。
但是,有些細節的刪去也讓人感覺稍有遺憾。《暗戀》中,江濱柳與云之凡在上海公園告別時,兩個人對于未來的憧憬以及云之凡回憶之前的逃難經歷被刪除。江濱柳云之凡是因為戰爭而在上海相遇,在最初的話劇演出時,劇作者可能更注重歷史對于人們的創傷的揭示,而在時隔6年之后,臺灣與大陸關系的緩和讓劇作者將這一情節刪去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云之口中所描述的那個滿山野花的地方,不正是《桃花源》中老陶贅述的“桃花源”嗎,這是呼應《桃花源》的一個很好的細節,讓人感受到世外桃源不僅僅存在于陶淵明時代,現代社會中也可以存在,這一情節的刪減讓人覺得有點可惜。
而在《暗戀桃花源》排演的最后一幕,當年邁的云之凡探望過病重的江濱柳離開后,影片的鏡頭便轉向了話劇排演完后的化妝間,而沒有了江太太進來安慰江濱柳這一情節,的云之凡的離去,江濱柳的內心是悲苦的,江太太釋然地走過去安慰他,可是他卻拒絕了,然而面對久立在身旁的太太,這個陪伴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江濱柳最終還是伸出了手,他的手向空中乞討,江太太默默地走過去拉住他,江濱柳無以為靠地把頭倚在她的懷里,這個生命中的小片段讓人唏噓不已江濱柳對于這夢中戀人的離去,這一生的等待竟是以這樣的結局收場,而陪伴在自己身邊的一直是江太太,在這一刻,他終于接受了這個事實,也許他的內心里還不能真正接受江太太,但他必須從夢中醒來,這時的江濱柳心里是多么的悲涼凄苦啊。影片中刪去了這一情節,無形中消解了這出現代悲劇的悲劇意味的結局,顯得不夠完整。
二、新的元素
除了刪除部分情節之外,在影片中還增加了一些新的東西,以求更好地表現當下時局的變化,符合時代潮流的發展。《暗戀》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臺北病房中,江濱柳在夢中與當年的云之凡在上海公園相會,影片中的江濱柳手中多了一沓信,全是寫給云之凡的信。這一情節的加入讓觀眾從這厚厚的一沓信中看出江濱柳對于云之凡的深深思念,化意象為具體的物象。“在中國的電影傳統中,電影首先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其次是一門藝術,最后才是一種大眾娛樂”。①賴聲川在面對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臺灣時是深有感觸的。當時的臺灣,政黨林立,各自為政社會處于無序的狀態,到處充斥著奢靡和墮落的現象,面對這樣一種社會生活狀態,賴聲川在影片中加入了“你要是有想法就拿出勇氣出來做,你不要老是想,你要知道,新中國就是被你這種人拖垮”,借云之凡的口揭示當下人們的精神文化是每況愈下的,是不利于社會發展的,從而鼓舞人們重新振作起來,用積極的精神狀態投入到建設社會的行列中。云之凡這朵象征純潔的愛的“白色山茶花”不再只是江濱柳的夢中的戀人,她的眼光也投向了社會和國家,這是賴聲川關注政治的眼光。
而在《桃花源》中也有情節的變換和增加,下面這幾個小細節的改動就很有意思。一個是關于布景的設置,影片中除了保留原先舞臺背景的“留白”外,還增加了一棵“逃”出來的桃樹,這種一棵“逃”出來的感覺實際上還是隱射當時臺灣民眾在解除戒嚴令之后想要回到大陸探親的迫切心情,也可以理解為,人們想從這混亂的時局逃出去,去尋找“桃花源”這樣的棲息原地。另一個是關于老陶在桃花源中喝水的情景,話劇原本是白袍女子與白袍男子都相繼讓老陶喝水,安撫發狂的老陶,讓他放輕松,平靜下來。可是影片中的情節有所改動,當白袍男子讓老陶喝水時,老陶拒絕了,自己上前去用手接水喝,這時水流停止了,老陶喝水失敗,這一橋段和他在家里打不開酒瓶蓋子,吃不動餅的戲是如出一轍的,都表現了老陶對于日常生活的陌生感和無力感,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范圍內,這是非常態的生活。賴聲川借此又再次強調了當時社會的混亂不堪以及人們想要而不可得的生活狀態。還有一個是關于春花疊尿布的情景,影片中將地點從屋內換成了屋外,當時春花是在屋外頂著大風艱難的收拾晾在竹竿上的尿布,空中飄著在桃花源中飄落的桃花瓣,這是老陶從桃花源回到武陵的一個很好的銜接,過渡自然,不顯得過于突兀,符合電影的欣賞要求。而春花在大風中艱難行進也預示著即將到來的讓她感到恐怖的事,即她認為早已死去的老陶變成鬼回來了。賴聲川在小細節處的改動讓《暗戀桃花源》更符合電影的欣賞要求,也補充了時隔6年戲外環境的變化,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處于電影的需要,賴聲川還拓展了舞臺空間,增加了戲劇之外演員與演員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突破舞臺劇的畫框限制,增加場外情景的鏡頭,這樣更符合電影的攝制要求。
三、結語
從1986年到現在將近30年的演出歷程,期間版本變更多次,近年來話劇與越劇的聯姻更是將《暗戀桃花源》推向了另一個巔峰,而電影版的《暗戀桃花源》在上映了二十幾年后仍然是一個不倒的經典。1992年的影片與最初的話劇版相比,賴聲川在整體思想的把握上拿捏的很好,沒有失掉最初的創作精神,雖然刪減去了一些與所保留下來的部分同樣精彩的情節,但是出于影片時長不得不忍痛割愛也是可以理解的。賴聲川以他敏銳的目光,在戲中還加入了一些新的能反映不同于1986年的時局的東西,讓整部戲在塑造經典的同時與時俱進。從最初有著讓人引以為傲的演出盛況的舞臺劇到電影版上映的成功,賴聲川偕同這部《暗戀桃花源》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欣賞藝術的愉悅,更讓人們的心靈得到溫暖,這也許也是他最想要帶給觀眾的,而讓觀眾的精神得到洗禮,心靈得到慰藉就是他最大的成功之處。
注釋:
①馮錦芳:《缺席與在場的辯證圖景——新時期中國電影觀眾問題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4頁。
參考文獻:
[1]孫希娟:《<暗戀桃花源>主題意蘊探微》,文藝爭鳴,2012年第12期。
[2]李杜若:《電影<暗戀桃花源>主題探究》,中國電影評論,2014年第6期。
[3]馬小青:《在古典文化與現實生活之間——談臺灣電影中敘事與空間拓展》,電影文學,2009年第17期。
[4]裘文意:《第五代改編電影:新時期文學與電影現代性的共同表達——中國當代改編電影現代性解讀之二》,電影文學,2007年1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