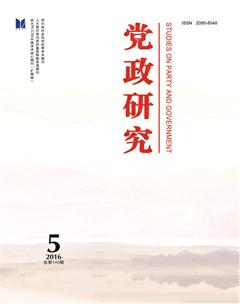中國農村扶貧發展歷程與扶貧戰略的綠色轉變研究
沈茂英
〔摘要〕消除貧困是全球面臨的共同任務,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中國政府大規模扶貧成功解決了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實現了從溫飽型貧困向發展型貧困的轉變,成為世界反貧困領域的翹楚。我國扶貧目標也從解決溫飽到解決低收入人口的發展問題,扶貧理念從救濟式扶貧到資源開發式扶貧繼而轉入綠色生態扶貧階段。我國農村扶貧經歷了體制改革帶動型扶貧、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八七扶貧攻堅和制度化扶貧等階段。扶貧戰備從開發式扶貧向綠色生態扶貧轉變。
〔關鍵詞〕農村扶貧;階段貧困特征;扶貧戰略;綠色生態扶貧
〔中圖分類號〕D42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6)05-0122-07
中國大規模的扶貧起于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中期,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立為標志,將貧困以及扶貧置于專門的機構之下,進行持續時間較長的扶貧開發。回顧30余年的扶貧開發工作,無論是貧困區域還是扶貧類型,都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同階段,貧困所呈現出的特點是完全不同的。我國農村扶貧開發先后經歷了80年代中后期的大規模扶貧、八七扶貧攻堅以及新世紀的扶貧開發,制定了三次扶貧開發規劃(計劃),分別是《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和《中國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成功解決了農村大面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實現了從溫飽型貧困向發展型貧困的轉變,成為世界反貧困領域的翹楚。我國農村扶貧目標也從解決溫飽到解決低收入人口的發展問題,扶貧理念從救濟式扶貧到資源開發式扶貧繼而轉入綠色生態扶貧階段,扶貧戰略從開發式扶貧向綠色生態扶貧轉變。
一、 我國農村扶貧發展歷程
我國大規模的扶貧經歷了體制改革帶動型扶貧、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八七扶貧攻堅和制度化扶貧等階段。
1.體制改革帶動型扶貧(1978-1985)。體制改革帶動型扶貧是通過土地經營制度的變革(即以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體經營制度),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解放了生產力,實現勞動力與土地的有效結合,提高土地產出率。同時通過實施農產品價格逐步放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等多項改革,為解決農村的貧困人口問題打開出路。這些改革,促進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并通過農產品價格的提升、農業產業結構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轉化以及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領域就業三個方面的渠道,將利益傳遞到貧困人口,使貧困農民得以脫貧致富,農村貧困現象大幅緩解。據統計,期間農村人均糧食產量增長14%,棉花增長73.9%,油料增長176.4%,肉類增長87.8%;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6倍;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占農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貧困人口平均每年減少1786萬人。〔1〕
2.大規模開發式扶貧時期(1986-1993)。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釋放的扶貧效應開始遞減,一些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較差的區域貧困問題十分突出。
1986年,全國范圍內確立了18個連片貧困區①〔2〕,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實施連片開發與國家貧困縣相結合的開發式扶貧策略,以集中有限的扶貧資金解決連片貧困區的基礎設施問題,讓連片貧困區富裕的資源得到開發和利用,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解決“捧著金飯碗討飯”問題。經過八年的不懈努力,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06元增加到483.7元;農村貧困人口由1.25億人減少到800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40萬人,年均遞減6.2%;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14.8%下降到8.7%。但剩余貧困人口的地緣性特征十分明顯,貧困人口分布進一步向西部地區集中,西南大石山區(缺土)、西北黃土高原區(嚴重缺水)、秦巴貧困山區(土地落差大、耕地少、交通狀況惡劣、水土流失嚴重)以及青藏高寒區(積溫嚴重不足)等幾類地區成為重點區域。
3.扶貧攻堅時期(1994-2000)。以1994年3月《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公布實施為標志,中國的扶貧開發進入了攻堅階段。《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提出,從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個時期貧困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國家重點扶持的592個貧困縣,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高寒山區、黃土高原區、地方病高發區以及水庫庫區,而且多為革命老區和少數民族地區。
脫貧標準是絕大多數貧困戶年人均純收入達到500元以上(按1990年的不變價格)。扶持貧困戶創造穩定解決溫飽的基礎條件(有條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畝到一畝穩產高產的基本農田;戶均一畝林(園),或一畝經濟作物;戶均向鄉鎮企業或發達地區轉移一個勞動力;戶均一項養殖業,或其他家庭副業。牧區戶均一個圍欄草場,或一個“草倉庫”)。與此同時,鞏固和發展現有扶貧成果,減少返貧人口。
①18個連片貧困區分別是:努魯爾虎山地區、太行山地區、呂梁山地區、陜甘黃土高原地區、隴西高原地區、西海固地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地區、烏蒙山地區、橫斷山地區、滇東南山地區、桂西山地區、九萬大山地區、井岡山地區、武夷山地區、大別山地區、沂蒙山區、西藏地區。
扶貧手段是依托當地資源的開發性扶貧。積極發展能夠充分發揮貧困地區資源優勢、又能大量安排貧困戶勞動力就業的資源開發型和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通過土地有償租用、轉讓使用權等方式,加快荒地、荒山、荒坡、荒灘、荒水的開發利用;對極少數生存和發展條件特別困難的村莊和農戶,實行開發式移民。這一時期,四荒(或五荒)資源開發利用是極為重要的扶貧方式。
4.新世紀初農村扶貧(2001-2010)。以《2001-2010年農村扶貧開發綱要》為標志。在首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中,確定了農村扶貧的基本目標是“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進一步改善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鞏固溫飽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加強貧困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態環境,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落后狀況,為達到小康水平創造條件”。農村扶貧的對象是“未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和初步解決溫飽問題的脫貧人口”。農村扶貧的重點是“貧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邊疆地區和特困地區作為扶貧開發的重點,并在上述四類地區確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以縣為單位、以貧困村為基礎的瞄準性扶貧,整村推進一體兩翼是扶貧開發的主要戰略(以貧困為重點,以勞務輸出扶貧和產業化扶貧為支撐兩翼)。明確了將扶貧開發與生態相結合,提出了“扶貧開發必須與資源保護、生態建設相結合”……“要以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為原則,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5. 打贏脫貧攻堅時期(2010-2020)。進入21世紀,我國農村扶貧更加制度化和規范化,編制實施了《2011-2020年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其扶貧總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扭轉發展差距擴大趨勢”。綱要確立“在扶貧標準以下具備勞動能力的農村人口為扶貧工作主要對象”,“六盤山區、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大興安嶺南麓山區、燕山-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等區域的連片特困地區和已明確實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三地州是扶貧攻堅主戰場”。在整村推進上提出“以縣為平臺,統籌各類涉農資金和社會幫扶資源,集中投入,實施水、電、路、氣、房和環境改善‘六到農家工程,建設公益設施較為完善的農村社區”。在行業扶貧上提出“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合理開發當地資源,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承接產業轉移,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貧困地區發展內生動力”。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其基本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從三次國家扶貧開發的計劃、規劃綱要和兩次攻堅決定來看,農村貧困的基本內涵在不斷發生變化,貧困維度在不斷拓展,貧困人口界定不斷清晰,扶貧手段不斷拓寬,對貧困地區資源的認定不斷發展。《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的貧困人口是未解決基本溫飽問題的農村人口,是處于饑餓生存線上的貧困人口,大部分還屬于絕對貧困狀態。2001-2010年的扶貧對象為少數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和鞏固溫飽,絕對貧困狀態明顯改善,重點是鞏固溫飽和提升發展能力。到2011-2020的扶貧對象,進一步明確收入水平低于國家貧困標準的有勞動能力的農村人口,扶貧對象的瞄準性進一步提升,目標從扶貧轉向脫貧,扶貧資源基礎從開發利用資源向保護利用資源轉變,扶貧策略更加向綠色化、生態化,綠色發展型扶貧成為脫貧攻堅新亮點。
二、 不同階段農村貧困的基本特征
1. 農村貧困人口總量變動
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1985年的1.25億,經過大規模的八年扶貧開發(1986-1993),貧困人口再次下降到8000萬人(國家貧困線為200元/人);《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實施成功解決了剩余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但因貧困標準的提升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在2000年下降為3000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其中,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的貧困人口從1994年的5858萬人減少到2000年的1710萬人。這些人主要是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的特困人口、少數社會保障對象以及部分殘疾人。2000年,國家將農村扶貧標準調高到865元,貧困人口數量從1710萬增加到9422萬人。2003年,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還增加了80萬人,首次出現貧困人口不降反升的現象,扶貧工作遇到瓶頸〔3〕。2010年,貧困標準再次從2000年的865元人民幣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人民幣,此標準衡量下的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萬人;農村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比重從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4〕。進入2011年,農村扶貧標準再次提升到2300元①,農村貧困人口達到1.28億人。經過5年的努力,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2015年的7000萬左右。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實現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2.20世紀農村貧困基本特征
從縱向發展來看,各個階段農村貧困的標準與貧困特征是呈現出較大差異的。文獻對各個階段的貧困特征描述如下:
改革帶動扶貧時期的貧困特征:1978年-1985年為農村改革帶動扶貧,期間農村處于普遍貧困狀態,農村大多數人生活在“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房不遮風雨”的絕對貧困。依靠農業經營制度改革、農產品價格改革以及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期間農村人口的收入快速增長,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水平超越城鎮,大部分農村居民成功脫貧。這個時期的貧困為整體性貧困,全國并未專設扶貧機構,對極端貧困人口的關注體現為救濟。救濟是最基本的制度性扶貧,解決極端貧困人口和失能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救濟解決了部分絕對貧困人口的吃飯問題但難以解決貧困人口的發展問題。
大規模開發式扶貧階段的農村貧困特征:貧困地區相對集中連片,農村貧困人口為主,分布在山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老、少、邊、窮”特征明顯。貧困地區大多“地形復雜,氣候多變,災害頻繁,生態脆弱”“人均耕地少,生產條件差”“人口增長過快,人口素質偏低”“社會發育程度低”“經濟發展落后,生產力水平低,財政困難”〔5〕。絕對貧困人口仍然處于一種“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房不遮風雨”狀況。貧困人口分布呈現出連片貧困特征,連片貧困區內基礎設施差、交通通訊不便、社會封閉、貧困人口思想保守、傳統地域文化對貧困人口的影響大。
①2009年,中國國家扶貧標準從2008年的1067元上調至1196元,2010年隨CPI上漲而再上調至1274元,2011年提升到2300元,提高了80%。
扶貧攻堅階段的農村貧困特征:貧困人口分布的區域集中度依然比較高,“老少邊窮”地區的貧困問題依然十分突出,但貧困人口進一步往西部和少數民族、山區集中,全國592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集中了全國貧困人口的70%。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有了明顯改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現象有了比較大的改善,但與非貧困人口的差距在拉大,因災致貧、因病致貧等現象比較突出。貧困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占比較高,在592個縣中有259個少數民族縣,少數民族地區貧困發生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貧困地區地方病嚴重。貧困人口的分布在地域上出現了明顯的大分散、小集中的趨勢,以較大行政區域為單元的大面積貧困區逐漸減少,以縣為單位的貧困地區逐步轉變為鄉、村級小區域的貧困區,并在行政區域交接地帶及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的小流域相對集中。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中絕大多數分布在自然資源貧乏、生產生活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的高山區、深山區、石山區、黃土高原區、邊緣荒漠化地區、地方病高發區以及自然災害頻發區,共同特征就是地域偏遠、交通不便、生態失衡、經濟發展緩慢、社會發育程度低。〔6〕
3. 21世紀農村貧困特征
進入21世紀,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較20世紀已經實現了較大改善,但貧困人口仍然固守的共同特征為:貧困人口的生活入不敷出,食品消費量嚴重偏少,家庭支出恩格爾系數高,自給性消費比重大,家庭設備少,檔次低,文化消費支出少,社會服務水平低,農業生產水平低,沒有長效投資,健康狀況不良,兒童輟學風險大等一系列問題〔7〕。老人、女性、兒童等群體的貧困發生率高。另一方面,貧困與生態環境的聯系更加緊密,或者說生態與貧困進一步交織,生態貧困、生態難民等概念頻繁出現在相關文獻與政策建議中。特別是21世紀相繼強化實施的系列生態建設工程,如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以及自然保護區在數量上的不斷增加和面積上的不斷擴大,因生態建設而返貧的現象在生態建設區密集出現,全國80%以上自然保護區被貧困社區所包圍(或者說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貧困現象突出)。文獻研究也不斷證實,貧困問題是一個生態問題,貧困狀況的發生和貧困程度的大小與生態環境狀況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最貧困的人口生活在環境破壞最嚴重、恢復能力最低的地區。我國廣大的貧困地區,其表層特征是經濟貧困,而深層次原因往往是環境貧困。〔8〕
政府為保護環境而采取強有力的政策,實施密集生態工程,劃定自然保護區,建立巡查隊伍,形成新的生態保護型貧困。2006年編制完成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與2011年編制完成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將貧困與生態的關系進一步聯系起來,全國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在地理空間上與全國重點生態功能區分布高度重疊,大部分連片特困地區同時是國家生態安全屏障的重要區域,生態保護與扶貧開發成為這些區域面臨的兩大主要任務。可以說,21世紀的貧困是主體功能區制度建設背景下的新型貧困,是資源貧困、政策貧困、能力貧困與發展貧困等多種貧困的復合體。
三、 我國農村扶貧戰略的綠色生態轉變
實踐證明,自然資源(或生態資源)是農村貧困人口最基本的生計資本。在我國的農村扶貧歷程中,十分重視對貧困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僅實施了基礎設施改善型扶貧、資源開發型扶貧,還不斷拓展資源開發扶貧內涵,走綠色扶貧和生態扶貧之路,從注重提高貧困人口的發展環境到提升貧困人口的內生發展動力轉變。扶貧政策實現了從解決溫飽為主的生存型扶貧向解決發展為主的能力扶貧和制度扶貧轉變,從農業扶貧向非農業扶貧與農業扶貧并舉轉變,從資源開發型扶貧向資源持續利用轉變,從資源的直接利用向資源的多角度利用轉變。尤其是在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之后,依據國家主體功能區制度推進貧困地區發展的綠色扶貧、生態服務扶貧轉變,實現綠色惠民、綠色富國,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綠色生活方式。
1. 資源開發扶貧是上世紀中國農村扶貧的主旋律。從1987年1月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將全國最貧困地區劃分為18個集中扶持貧困片區開始到1994年實施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扶貧開發的重點是設置專項資金改善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以工代賑是極為重要的扶貧舉措,一是加強基本農田建設,提高糧食產量,使貧困地區多數農戶有穩定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二是發展多種經營模式,進行資源開發,建立區域性支柱產業,使貧困戶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三是重點解決飲用水和通路等基礎設施問題,四是增加林區木材采伐指標,將部分國有林的經營管理權限下放到鄉鎮村,建立三級管理的責任制。對貧困地區的“五荒”資源(荒地、荒山、荒坡、荒灘、荒水)實施有效利用,成為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重要舉措之一。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在《關于加強貧困山區經濟開發的決定》中明確指出“貧困山區的農林牧土特產品(除麝香、黃柏、杜仲、厚樸外),不再下達指令性收購計劃,出口產品按計劃實行合同訂購,建立長期穩定的購銷關系,價格由購銷雙方商定最高限價和最低保護價”。在《關于加速貧困地區開發步伐的通知》(川委發〔1988〕8號)中指出“要進一步穩定荒山、荒坡、荒地資源的權屬關系,健全承包責任制”,對貧困地區的支柱產業發展要求“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相對集中、重點突出、連片發展、形成規模”(川府發(1991)145號)。在《四川省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要求“重點發展投資少、見效快、覆蓋廣、效益高的種植業、養殖業和相關的加工業,發展資源開發型和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加快小流域、荒地、荒山、荒坡、荒灘、荒水的開發利用,對極少數生存和發展條件特別困難的農戶實行開發式移民”。在《關于盡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決定》(川委發〔1996〕43號)中提出“把有助于解決群眾溫飽問題的種植業、養殖業和林果業作為扶貧開發的重點”,“把國家和省的大中型區域開發項目與扶貧開發項目相結合,優先向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安排一批水利工程、交通設施、礦業開發等資源開發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帶動當地農牧民就業,解決溫飽”。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農村扶貧,對貧困地區資源采用“有水快流”的開發模式,立足資源優勢培育支柱產業,基礎設施建設配合資源開發,目標是保障貧困農戶糧食需求、增加農戶經濟收入。盡管在扶貧手段上十分重視科技扶貧作用,在資源開發利用上也強調因地制宜、立足資源條件,但包括對四荒(或五荒)資源開發利用在內的資源開發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貧困地區的人口、資源、經濟失調。
2.21世紀是以綠色為基調的綠色生態扶貧。綠色扶貧萌芽于退耕還林(草)工程,完善于第二個扶貧開發綱要。1998年,包括長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發生了洪災,全國29個省(市、區)遭遇不同程度的洪災,受災人口達到2.23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60億元,長江上游森林砍伐過度和毀林開荒等被認為是洪災的直接原因。當年即在長江上游實施了天然林禁伐工程,繼而在2000年轉變為天然林保護工程(一期)以及2000年試點啟動退耕還林(草)工程,生態建設與扶貧開發緊密結合。在《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中明確提出“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將“扶貧開發必須與資源保護、生態建設相結合,與計劃生育相結合,控制貧困地區人口的過快增長,通過退耕還林、自愿移民等方式,減輕貧困地區的生態和資源壓力,實現資源、人口和環境的良性循環,提高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在2011年頒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明確我國農村扶貧已經進入了“改善生態環境”階段,扶貧開發要與“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相結合,充分發揮貧困地區資源優勢,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增強防災減災能力”,要求貧困地區“到2020年,森林覆蓋率比2010底增加3.5個百分點”,貧困地區要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要“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合理開發當地資源,積極發展新興產業,承接產業轉移,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貧困地區發展內生動力”。特別強調要“加快貧困地區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因地制宜發展小水電、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推廣應用沼氣、節能灶、固體成型燃料、秸稈氣化集中供氣站等生態能源建設項目,帶動改水、改廚、改廁、改圈和秸稈綜合利用。提高城鎮生活污水和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加大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力度。加強草原保護和建設,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和管理,大力支持退牧還草工程。采取禁牧、休牧、輪牧等措施,恢復天然草原植被和生態功能。加大泥石流、山體滑坡、崩塌等地質災害防治力度,重點抓好災害易發區內的監測預警、搬遷避讓、工程治理等綜合防治措施”。綠色扶貧成為貧困地區發展的重要戰略。不僅如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考察貧困地區時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強調要像保護眼睛一樣愛護生態環境,扶貧要立足生態環境條件。
3. 綠色扶貧和生態產品扶貧的制度不斷完善。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進一步強調“堅持保護生態,實現綠色發展。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生態保護放在優先位置,扶貧開發不能以犧牲生態為代價,探索生態脫貧新路子,讓貧困人口從生態建設與修復中得到更多實惠”。要求“國家實施的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防護林建設、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濕地保護與恢復、坡耕地綜合整治、退牧還草、水生態治理等重大生態工程,在項目和資金安排上進一步向貧困地區傾斜,提高貧困人口參與度和受益水平。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增加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結合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創新生態資金使用方式,利用生態補償和生態保護工程資金使當地有勞動能力的部分貧困人口轉為護林員等生態保護人員。合理調整貧困地區基本農田保有指標,加大貧困地區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力度。開展貧困地區生態綜合補償試點,健全公益林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完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
《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在制度上保障了以綠色發展來推動生態功能區扶貧,不僅確立了“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基本路徑,而且強調“樹立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理念,自然生態是有價值的,保護自然就是增值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過程,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就應得到合理回報和經濟補償”,通過“逐步增加對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完善生態保護成效與資金分配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建立鞏固退耕還林還草、退牧還草成果長效機制”。生態保護的內化成本有望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等的完善得到補償;碳匯交易市場的完善將促成生態產品貨幣化,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從40余年的農村扶貧開發歷程來看,對貧困地區資源的認識從索取到索取與保育并重再到保育為重的持續利用階段,從重視資源的直接價值到資源的直接價值與間接價值并用轉變,從重視資源的使用價值到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并重轉變。綠色成為脫貧攻堅的主色調,生態成為脫貧攻堅的前置條件和基本載體,主體功能區制度成為脫貧攻堅的約束制度。要實現綠色扶貧、生態扶貧,還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完善和政策構建,需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持續發展能力的提升,需要構建綠色生態扶貧的社會環境氛圍。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R〕.2001.
〔2〕 陳國階,等.2003中國山區發展報告〔M〕.商務印書館,2004.250-253.
〔3〕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4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白皮書)〔R〕.2011年11月.
〔5〕 安樹偉.中國農村貧困問題研究—癥結與出路〔M〕.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8-10.
〔6〕 趙曦.中國西部貧困地區扶貧攻堅難點問題與戰略選擇研究〔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79.
〔7〕 李小云,張雪梅,唐麗霞,等.中國財政扶貧資金的瞄準與偏離〔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50-51.
〔8〕 丁文廣,陳發亮,等.自然-社會環境與貧困危機研究——以甘肅省為例〔M〕.科學出版社,2008.8-9.
【責任編輯:朱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