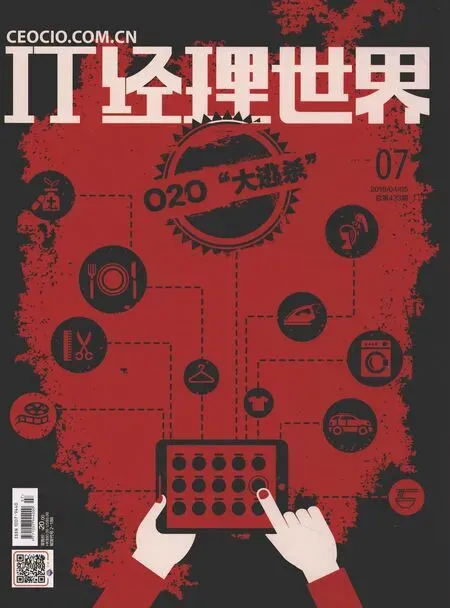公關的數字化生存
栗建
最近的公關圈很熱鬧。在著名傳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魏武揮老師發表了《公關到底重要么?》一文認為“公關就是打雜的”之后,公關行業的大牛、通用電氣(GE)中國有限公司公關總監要和他“玩命”。
終于,當我們談論公關的時候,關注點已經不再局限于“車馬費”、“黑公關”和“315Plan B”了。當一個行業在反思“自我價值”的時候,正是這個行業面臨生存危機的時刻,也是這個行業轉型并新生的機會。
我們不能低估公關的價值,公關依然是企業的戰略核心部門,負責企業的“顏值”,賦予一個品牌溫度和價值。
我們也不能高估公關的地位,把需要跨部門協作才能取得的“功勞”單獨留給公關,比如品牌建設和維護,比如產品定位和推廣。過一下嘴癮可以,現實中卻不是這樣。從品牌形象到產品推廣,市場、銷售、品牌管理、數字營銷、雇主品牌、渠道、供應鏈管理、售后以及各個商業部門(Business Units)等部門都有自己戲份,公關只是其中一個角色。不服看預算。
無論是甲方還是乙方,正在經歷一場自我“危機公關”。所有公關人都得承認,世道變了。當傳統媒體紛紛倒閉,當輿論和影響力“下放”,當世界變得“小”而“透明”,公關不能獨善其身,也沒有免死金牌。
公關的價值
對公關的定義和理解不同,對公關價值的認同也就各異。無論是百度百科還是Wikipedia,關于公關的定義和假說有無數的版本。在公關作為一門“手藝”誕生后的100年多年時間,關于公關的定義以及公關的價值的探索和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歇。
但是,它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打雜的角色。
在學院派看來,現代意義上的公關行業誕生于上個世紀,以1900年George Michaelis建立第一家公關公司Publicity Bureau作為開端。盡管這家公司于1911年就倒閉了,但在隨后的幾十年中,公關行業經歷了快速的發展。
早在1932年,公共關系學科化的先驅愛德華·伯尼斯(Edward L.Bernays)就提出公關的價值在于影Ⅱ向公共政策和公共輿論,或者在兩者之間建立微妙的聯系。
從那時開始,公共關系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就已經從新聞和傳播領域中分離出來,形成了獨立的理論和體系。
世界上最大的兩家的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和博雅(Burson-Marsteller)分別與1952年和1953年成立。從那時起,公關就在實踐中突破了“媒體”和“發稿”的范疇。愛德曼以“The Toni Twins”項目讓公關開始走出“發稿公司”的圍城,讓公關成為代替廣告成為營銷和銷售引擎的另一個重要工具,也因此逐漸奠定了業界企業傳播老大的地位。
而博雅則以危機公關和政府公關見長,讓公關成為保護和重塑企業品牌形象的戰略工具。幾乎在同時,另外一家公關公司偉達(Hill &Knowlton)開始了全球化,讓這個行當迅速全球化和標準化。
1948年,早期公關先驅Eric Goldman在《雙向街(Two-Way Street)》一書中,總結了企業公關的三個階段:造勢宣傳(spin)、公關傳播(publicity)和以互動為目的的雙向互動(Two-way communication)。
從50年代開始,大眾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和印刷媒體的繁榮誘惑著企業公關在公關傳播(publicity)和雙向互動(two-way communications)之間選擇了公關傳播,大眾傳媒媒介的強勢地位讓公關選擇與大眾媒體和記者“結盟”。
在接下來的50年,公關圍繞媒體制定戰略,在某種意義上是“新聞稿”、“媒體關系”和“媒體活動”的同義詞。這種“趨利”的行為也讓人們對公關的價值產生懷疑。在很多人看來,公關只是“速記員”、“傳聲筒”和“發稿機”。
在中國,公關和所有的外來行業一樣,經歷著快速而又扭曲的發展。
“車馬費”是中國式公關最大的特點。它究竟是“媒體賄賂”?還是“誠意表達”?或者是為了營造發布會現場滿坑滿谷升平景象的“簽到捧場獎勵”?很難說得清楚。除此之外,中國特色的公關和“水軍”、“五毛”、“大概八點二十發”、“黑公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更加扭曲的是行業的生態。甲方和乙方,本土公司和外企,價值觀不同,方法論各樣。
在甲方看來,乙方都是白癡。在乙方看來,甲方都是傻×。好創意不如好關系,好關系不如好交易,甲方和乙方的相愛相殺摻雜著私人恩怨和個人利益交換。
野蠻生長的本土公關公司和中西結合的外來者無論在價值觀還是方法論上從來就沒有統一過。在外企眼中,本土公司不僅“吃相難看”,而且讓“水軍造假”、“效果虛報”和“一手發負面一手做危機”的“下作”公關透支了行業信任,破壞了整個行業的健康。而在本土公司看來,外企就是水土不服的裝×犯,既沒有接地氣的玩法,又沒有走高端的能力。
這個行業也并不缺乏圈子,歐美邦瞧不上港臺腔,港臺腔看不起大陸仔,大陸仔和歐美邦聯合對付港臺腔。這個行業入門門檻不高,但成為專業人士卻很難。
但無論如何,公關的價值不容置疑。
比爾蓋茨曾經說“假如我只剩下最后一美元.我要把它用在公共關系上”。維珍集團的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認為公關“極其”重要,好的公關故事(PR Story)比頭版廣告作用更大。在維珍航空歧視中國乘客的事件之后,理查德·布蘭森在社交媒體及網站迅速回應,稱維珍航空“不會容忍種族歧視,亦不會容忍殘疾歧視。”
最后以沃倫·巴菲特的名言“鎮樓”:要贏得好的聲譽需要20年,而要毀掉它,只需要5分鐘。
死亡的預言
當傳統媒體集體調零,傳統公關也難逃死亡的陰影。
“公關是否已經死亡?”要比“公關是否重要?”這個話題更加深刻和殘酷。
公關行業資深從業者Robert Phillips認為公關正在死亡的邊緣。他在《Trust Me,PR is Dead(相信我,公關已死)》一書中說,公關的盛宴已經結束了。這是一個個體賦楓IndividualEmpowerment)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控制權”和“影響力”正在從政府流向個人,從雇主流向雇員,從企業流向消費者。
這本書不是嘩眾取寵之作,它基于企業、政府和媒體的訪談以及200多個企業案例的研究和分析,樣本即包括聯合利華、諾和諾德、John Lewis Partnership這樣的行業巨頭,又包括Handelsbanken、Patagonia、Mond ragon、38 Degrees以及Porto Alegre這樣的中小公司。
在個人賦權的時代,信任是最堅挺的社交貨幣。但是信任不是一個口號,它超越了公關的職能和能力。依靠信息不對稱獲得信息控制優勢的新聞稿和官方聲明,是公關“引導”輿論的有力武器,但這個在社交媒體上無用武之地。
此外,在危機處理上,從惠普的“蟑螂門”到華爾街的信任危機,公關在幫助企業重建信任上的作用日漸式微。
此外,在企業越來越依賴數據進行決策的浪潮中,公關的地位尷尬。在大多數情況下,公關缺乏有效的效果衡量體系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并在制服組的會議桌上為自己爭取一個座位。暫且不說“轉載率”、“Share of Voice”和“廣告價值”的計算如何不靠譜,你就是發一個整版的企業報道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公關的轉型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公關正在面臨一次徹底的轉型。盡管大多數甲方的世界依然波瀾不驚,乙方的天地早巳天翻地覆。
大多數的公司都選擇停止觀望,擱置爭議,并加速轉型。
你可能驚奇的發現,很多公關公司正在變成他們曾經“仇恨”的廣告公司。為了博得更多的甲方預算,公關公司正在模糊自己“公關公司”的定位,為自己明目張膽地加上“營銷”和“數字化”等標簽。
在過去的幾年,擅長內容的公關公司以“EPR”的形式融入到數字化的浪潮中,而如今他們更愿意以“數字營銷”的形式介紹自己。
除了傳統的優勢項目——內容和意見領袖關系一之外,公關公司正在擴軍備戰,把手伸向廣告公司和數字營銷公司的后院,把媒體投放、數字產品開發甚至Social CRM納入自己的業務范圍。除了數字營銷部門成為大多數公關公司的標配,在公關公司的辦公室,新來了很多擁有創意總監、媒體購買甚至設計頭銜的員工。
模糊“公關”的定位,并向新型數字營銷公司的轉型,是絕大多數公關公司的選擇。
公關人協會(The 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ts Association,PRCA)、《Holmes Report》以及YouGov的年度數字公關報告顯示,在2014年,來自社交媒體和數字服務的收入已經占公關公司總收入的11%到20%,在2015年,這個數字提升到了30%。
愛德曼公關在其官網介紹中寫道:我們相信在這個日益復雜的世界上——當媒體環境經歷巨變,當權威被稀釋分散,當輿論從任何地方產生,當所有人都有權利參與——公關本身已經遠遠不夠了。在今天,我們需要Public Engagement來代替Public Relatlons。Public Engagement是Paid Media主導的廣告和Earned Media主導的公關的第三條路徑。它將幫助我們的客戶更加積極更有效地與消費者進行互動,增加信任,增強關系,改變行為,并著眼于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Public Engagement的核心包括:每一個公司都要成為媒體公司(Every Company is a Media Company)、共同創造內容(Create and co-create content)、以社會責任為目標的伙伴關系(Build actwe partnerships for common good)以及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媒體關系的社交化(Know the socialized approach to media relations)。
仔細想想,這不就是數字營銷公司嗎?
乙方如此,甲方依然。
道路曲折,但前途未必光明。因為廣告公司和數字營銷公司也難養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