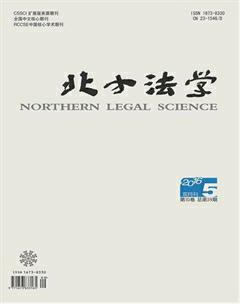從權利對象和權利客體之別析外觀設計專利權和版權的保護
朱楠
摘要: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是民法基礎理論中的一個艱深問題,核心是兩者是否在語義表達上是一致的。對其的不同解讀在民法領域以及知識產權法領域均產生了理論的分歧,同時也使司法實踐尺度不一。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實屬權利領域的不同范疇,權利客體內化于權利,反映權利的本質,即利益;權利對象是權利的外在指向,是具體的事實要素。兩者的恰當區分是解決版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重疊保護”的重要理論基礎,兩權的對象同質,但保護的利益各不相同,在此意義上也就并不存在所謂的“重疊保護”。
關鍵詞:權利對象權利客體重疊保護外觀設計
中圖分類號:DF5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5-0061-08
一、權利對象和權利客體的民法探源
(一)同一說
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同一說即無區別說,該說認為權利客體即權利所指向的對象,包括物、行為、智力成果、人格利益及其他財產利益。①這是我國民法學界的通說。有論如此的包括,鄭玉波認為:“權利之客體有稱為權利之對象者;有稱為權利之標的者(日學者稱目的);亦有稱權利之內容者,用語雖殊,意則無大異,故不可互訓,否則即發生以問答問之結果。”② 史尚寬認為,權利以有形或無形之社會利益為其內容或目的,為此內容或目的之成立所必要之一定對象,為權利之客體。③
梁慧星主編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中認為:民事權利客體,是與民事權利主體相對應的概念。按照民法理論上關于權利本質的通說,權利是由特定利益與法律上之力兩要素構成,本質上是受法律保護的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體即為權利的客體,也可以稱為權利的標的,或權利的對象。轉引自劉德良:《民法上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的區分及意義》,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9期,第3頁。日前公布的中國法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第五章即以“民事權利客體”命名,其中列物、有價證券、其他民事權利客體三節,人身利益、智力成果、商業標記和信息、財產權利、企業財產等均列入此章。
(二)區別說
區別說認為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并不相同,但是兩者如何相區別,學者則各持己見。這其中有以拉倫茨為代表的“雙重構造論說”及其演化。拉倫茨認為,權利客體使用于三種意義,一是指支配權或利用權的標的,此種狹義上的權利客體,稱為第一順位的權利客體;第二種是指權利主體可以通過法律行為予以處分的標的(權利和法律關系),為第二順位的權利客體;第三種是指作為一個整體并且可以被一體處分的某種財產的權利,即所謂的第三順位的權利客體。[德]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378頁王澤鑒也有類似觀點:物、精神上的創造或權利作為權利支配的客體是第一階層的權利客體;權利、法律關系作為權利人處分的對象是第二階層的權利客體。王澤鑒,《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方新軍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權利客體“層次說”,認為“權利的客體是權利設立的基礎,權利的標的是權利行使的對象,權利的內容是權利主體自由意志的行使方式。權利的客體要結合權利的層次作不同的分析,第一層次的權利客體包括物質客體和觀念客體。第二層次的權利是第一層次的權利動起來的結果,第二層次的權利客體原則上是第一層次的權利,但是通過第二層次權利創設出來的新權利種類有例外。第三層次的權利是第二層次的權利動起來的結果,其客體原則上是第二層次的權利,其后依此類推”。方新軍:《權利客體的概念及層次》,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2期,第36頁。 李揚專門針對知識產權運用了“雙重構造論說”,認為知識產權客體實際上也是一種雙重構造體系,主要包括兩大類權能作用層面上的客體:一類是靜態的知識產權支配、使用客體,一類是動態流轉性的知識產權處分客體。知識產權的支配、使用客體即信息,知識產權的處分客體是知識產權(利益)本身。李揚:《經驗抑或邏輯:對知識產權客體與對象之爭的反思》,載《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109頁。
區別說的另一種解讀則是認為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本身屬于不同的范疇,劉春田提出知識產權的對象是指那些導致知識產權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因素,是“知識”本身。劉春田:《知識財產權解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第110頁。 知識產權的客體是指“基于對知識產權的對象的控制,利用和支配行為而產生的利益關系或稱社會關系,是法律所保護的內容”。劉春田:《知識產權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劉德良在解讀個人信息的商業化利用時提出“在法學上,應該區分權利客體與權利對象:前者是一個抽象的范疇,是指體現在各種權利對象上的人格利益或財產利益;后者是一個相對具體的范疇,包括物、行為、信息等承載各種財產利益或人格利益的載體”。前引④,第1頁。
導致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理解分歧的基礎原因在于它們本就是人類為了定紛止爭而高度抽象出的概念,所謂“權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時也是對法律生活多樣化的最后抽象”。[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 此外,語言的翻譯也導致了問題的產生,翻譯對語言表述的取舍本身就代表了譯者的解釋,如張俊浩先生指出:“法學中的‘客體移自于哲學,英文為object,德文為objekt,其原義為主體的認識對象。”方新軍指出“爭論幾乎全部集中在對該條中的德語單詞Ggenestande 的翻譯上”。前引⑦。另見朱虎:《權利客體的解釋框架研究——邏輯和價值的區分》,載中國知網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政法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熊文聰:《超越稱謂之爭:對象與客體》,載《交大法學》2013年第4期。 中國、日本學者對德國民法相應詞匯翻譯上的不一致也使得這一問題愈加復雜。
(三)權利客體即權利的本質
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是否具有相同的語義反映了人類對于權利在不同層面的解讀。權利客體是從抽象價值的層面解讀權利,權利對象則是在具體事實層面描述權利。
權利對象是權利的外在指向,是具體化的,是人類從實踐和感知的角度確定的具體要素,是權利這一抽象概念指向的客觀事實。正如學者所言,“物本身只是一個事實的描述概念,它并不能說明與其有關的權利的內容,但它可以將建立在其上的權利與建立在其他對象上的權利區分開來,如果這種區分是有必要的話”。方新軍:《財產死亡了嗎?》,載《華東法律評論》(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民法采權利對象作為對權利加以區分的基礎主要是源于經驗和感知,具體化的要素更容易為大眾所認識和理解,其是第一性的,用具體事實很容易區分此權與彼權。
然而權利客體內化于權利,反映的就是權利的本質,是抽象出來的利益關系,是第二性的。邊沁在其《立法原理》一書中曾經指出:“根據自然法則,財產是在訴訟中受到法律保護的,從物中獲取利益的期待。”Roger ACuningham,William BStoebuck, Dale AWhitman, Tne Law of Property,2d Ld(StPaul MN:West Publishing,1993), p1 無論是物還是知識,都是第一性的事實,而不是第二性的財產,只有將對其的利用資格在不同主體間進行利益的配置,形成法律認可的關系,才是財產或權利。王伯琦先生認為:“予以為權利之內質,原屬一種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體,謂之權利之客體。”王伯琦:《民法總則》(第八版),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版,第103頁。 胡長清先生認為民事權利一般可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1)權利之內容,即為法律所認可的利益。法律在調整利益時只能規范人們據以實現其需求的措施和手段即人的行為。因此,法律所認可的利益就是法律所認可的人的行為及行為的后果。(2)權利之外形,即為法律上的力。法律因充實其所認許之利益,不能不付與一種力。胡長清:《中國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頁。 由上可知,權利作為法律上的高度抽象概念,是基于具體事實對人與人社會關系的配置和調整,而權利客體展現的正是權利分配社會資源的這一屬性,可見,權利客體化于權利之內,是“里”;權利對象展現權利外在之支配,是“表”。此權利區別于彼權利的根源實際上在于客體這個“里”,而非對象這個“表”。
筆者認為權利客體就是法律保護的特定利益。然法律要保護某種利益,就必然是帶有一定的價值觀對諸多利益進行取舍。選擇權利就是選擇利益。[美]愛倫·斯密德:《財產、權力和公共選擇》,黃祖輝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如為了實現物盡其用,在物這一對象上建立了物權;為維護人的尊嚴,在各種人格要素上確認了人身權;為了激勵創新,保護創造利益,產生了以智力創造成果為對象的知識產權;為鼓勵交易,規范物的流轉活動,確認了債權。誠然對于何為權利,除利益說之外尚有諸多學說,但筆者認為在知識產權領域,用利益說來解讀權利較其在其他民事權利領域更具說服力。從知識產權產生的歷史來看,商人階層對統治者的游說起到重要作用,商人憑借封建特權壟斷圖書市場、技術革新和行業產品,這樣的壟斷初始為習俗、習慣,而后則演變為成文法中的知識產權,同時統治者也因為公共利益的約束而不得不給商人壟斷設置限制。參見黃海峰:《知識產權的話語與現實:版權、專利與商標史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澳] 布拉德·謝爾曼、[英] 萊昂內爾·本特利:《現代知識產權法的演進:英國的歷程(1760—1911)》,金海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康添雄:《私權邏輯的否定:專利法史的公共政策線索》,載《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可見,知識產權產生的過程正是統治者對利益加以取舍、平衡的結果。在選擇利益的過程中,保護何種智力創造成果、保護的范圍、保護的期限無一不體現利益的博弈,知識產權制度既保護因創造物而產生的新的產業利益,即壟斷;也保護公眾獲取、分享新知識的利益。
二、知識產權領域區分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的意義
(一)解決知識產權權利重疊保護的爭論
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均具有規范意義,權利客體的本質即為權利。客體的另一個功能就是用以區分權利以及法律關系,客體的不同決定了權利的不同。客體和對象不分,在以有體物為對象的權利體系中,并未產生太多的理論分歧,也沒有影響規則的適用。但在知識產權的權利體系中,客體、對象同一說明顯遇到了適用上的障礙,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學者均認為在知識產權領域存在權利重疊保護。其常見于美術作品、實用藝術作品、外觀設計和商標這些對象,本文要解決的是外觀設計專利權到期或失效后,相關的設計是否還可以獲得著作權的保護。
知識產權重疊保護的原因是什么?學者多提出三個權利的客體有重疊和交叉,加之知識產權客體需要界定,而泛權利化的觀念導致各知識產權邊界模糊。譚華霖:《究本與溯源:知識產權權利沖突原因考》,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3 期,第62—65頁。 還有學者認為這個問題“關涉彼此不同的法益。當同一對象承載了彼此不同的利益,法律應當允許權利人獲得多重保護,這是公平正義的應然之義”。張玉敏:《三維標志多重保護的體系化解讀》,載《知識產權》2009年第11期,第19頁。 也有學者提出:作為知識產權的客體,“實用藝術作品”與“外觀設計”事實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張偉君:《實用藝術作品著作權法保護與外觀設計專利法保護的協調》,載《知識產權》2013年第9期,第51頁。 再有“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不斷擴張,三個領域之間一些既有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在實踐中,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為了獲取更多的權利保護,制造了一系列重疊保護現象”。何煉紅:《知識產權的重疊保護問題》,載《法學研究》2007年第3期,第62頁。 如果承認著作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權利的對象或者客體是一回事、或有交叉,那么必須回答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其權利的對象或客體是什么?甚至如果認為其權利對象重合的話,第三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何在同一事實上要確認兩種權利?權利客體和權利對象的不分正是上述諸問題的根源。
(二)解決司法分歧
權利客體和對象不分除了在理論層面給知識產權的理解帶來困惑外,在實踐層面也帶來了司法的不一致,下文三個案例便是例證:
案例一:常州淘米裝飾材料有限公司訴北京特普麗裝飾裝幀材料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一審判決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常知民初字第85號,二審判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蘇知民終字第00037號。
本案原告申請了壁紙的外觀設計專利,糾紛發生時該外觀設計專利已過保護期,被告未經許可生產銷售了和原告壁紙圖案相同的壁紙,原告起訴認為雖然其專利權已終止,但壁紙屬于美術作品,應當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被告構成侵權。被告則認為專利權已經終止,公眾即有理由相信該外觀設計進入了公有領域,是公共財富,不構成侵權。法院對原告的主張予以了肯定,認為其構成美術作品。法院提出:法律不禁止權利人在同一客體上享有多種民事權利,每種民事權利及其相應義務由相應法律分別調整。本案的外觀設計不論是否處在保護期中,被告未經許可都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權。如果因為該圖案已被授予外觀設計專利權而對著作權不予保護,則意味著兩種民事權利相互排斥、不能并存,會阻礙智力成果的傳播。
案例二:謝某訴葉某、海寧市明揚食品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一審判決海寧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知初字第10號,二審判決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浙嘉知終字第5號。
涉案食品包裝袋(老謝榨菜)獲得外觀設計專利授權,后因未繳年費而終止。原告認為被告生產的榨菜包裝上使用的圖案與其享有著作權的上述外觀設計中的圖案相似,且未經其許可,因此構成著作權侵權。被告認為原告享有著作權的圖案作品依附于原先的外觀設計,該外觀設計已失效,進入公知領域,原告不應再對該圖案享有著作權。一審法院認為,“該項外觀設計權利的授予,意味著原告享有著作權的該包裝圖案在食品包裝袋上的使用獲得壟斷權利,同時該權利所涉的圖案須向公眾公示。授予該圖案作品的外觀設計專利權,其保護范圍是與其附著的產品緊密相連的,只局限于與外觀設計專利產品在相同或相近類別的產品上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圖案。同時,在該保護范圍以外,涉案圖案作品仍然可以依據著作權利受到保護,兩者并不沖突,且正是由于其保護范圍的不同而同時存在。而本案專利已經失效,已失去了壟斷性,即涉案圖案在食品包裝袋上的使用已進入了公共領域,在該外觀設計并未仍然受其他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其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案例三:深圳市王三茂食品油脂有限公司與深圳市福田區永隆商行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一審判決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深中法民三初字第670號,二審判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粵高法民三終字第236號。
原告對涉案的包裝標貼申請了外觀設計專利權,使用在食品上。后因未繳年費而致專利失效。被告在涉案專利失效后仍然生產銷售和原告標貼包裝類似的麻油產品,為此,原告提起著作權侵權之訴。本案二審法院維持原判,認為:“三茂公司自愿將涉案標貼申請并獲得外觀設計專利權,從版權的保護進入工業產權的保護。該外觀設計專利因未繳納年費,已經失效,進入了公有領域,已經成為社會公眾均可以使用的公共財富,因此,三茂公司的外觀設計專利權不再受法律保護,不能禁止他人在相同或類似的產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外觀設計。永隆商行使用與該失效的外觀設計專利相近似的包裝標貼,使用方式與三茂公司失效的外觀設計專利標貼使用方式相同,都是香麻油產品包裝標貼,這屬于對已經進入公有領域的公眾財富的使用,沒有侵犯三茂公司的專利權,同時,這種工業性使用也未侵犯三茂公司的著作權。”
上述三個判決雖然在涉案對象上有別,但均屬于失效外觀設計能否受到著作權保護的問題。案例一顯然認為失效的外觀設計圖案仍然受著作權保護,原權利人可以憑借著作權阻止他人在原專利產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設計。案例二和案例三雖然論證略有區別,但結論比較一致,即認為失效的外觀設計即進入公有領域,原權利人不能憑借著作權阻止他人在原專利產品上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設計。造成司法判決相左的根源仍在于對知識產權的客體和對象的模糊認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晨光筆”案中也有客體、對象混用而成的說理:“多數情況下,如果一種外觀設計專利因保護期屆滿或者其他原因導致專利權終止,該外觀設計就進入了公有領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但是,在知識產權領域內,一種客體可能同時屬于多種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其中一種權利的終止并不當然導致其他權利同時也失去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2010)民提字第16號。 筆者贊成案例二和案例三的判決結論,其比較準確地界分了外觀設計專利權和版權的客體范圍,因為各知識產權的客體本就不相同,他種權利是無法延及至原客體繼續進行保護的。外觀設計專利權失效,就使得設計和特定產品結合產生的市場競爭優勢不再處于專有權的范圍,至于設計上存在的著作權也只能阻止除卻該特定產品以外的復制或制造行為。案例一的判決結論令人不禁要問:如果“外觀設計不論是否處在保護期中,被告未經許可都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權”,那么外觀設計制度的意義何在?
三、外觀設計專利權和著作權的分野
(一)客體的分野
著作權的對象是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智力表達,即作品,客體則是表達上產生的審美價值。美感雖然高低有別,但只要源自于作者,反映作者的審美視角即產生著作權,這就是“獨創性”的內涵。著作權對作品之審美價值的保護就是法律選取了這一利益以激勵創作。著作權的保護既不關乎作品的符號形式,文字、線條、節奏、畫面均得采之;也不關乎作品的載體形式,紙張、布料、塑膠、金屬俱能再現。
外觀設計專利權的權利對象實際上也是某種美學表達。我國《專利法》第2條第3款規定: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適于工業應用的新設計。法條將外觀設計作了平面化的處理,直接將其界定為某種新設計。外觀設計專利中“產品的”表述往往為人忽略,“依托于產品”往往隱在了法條之后。不可否認,設計確實和著作權對象同質,甚至產品設計活動從本質上說就是創作活動,設計創作產生的作品一旦應用于實用產品就產生了新的利益,這個利益就是設計表達和實用產品之結合產生的市場競爭優勢,即外觀設計專利權的客體。在我國《專利法》的立法過程中,對于外觀設計入法所起到的作用作了清晰的定位,如1979年12月22日第6稿《專利法》認為:保護外觀設計專利,有利于促進我國商品式樣的改進,豐富人民生活,加強出口競爭能力。趙元果:《中國專利法的孕育與誕生》,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頁。 1981年2月第11稿同樣提出其“有利于促進我國商品式樣、色彩的改進,使產品適銷對路并增強出口競爭能力”。前引B28,第238頁。 可以說,設計所具有的審美價值成為推銷實用產品的重要手段。但設計若脫離了實用產品,其自身并不具有在市場中進行交換的獨立意義,或者說一旦其脫離了產品,單獨的設計都不是一個市場要素。設計是為作為載體的實用產品而生成和應用的,特定載體是外觀設計的構成要件之一。郭禾:《外觀設計與專利法的分野》,載《知識產權》2015年第4期,第11頁。 設計是產品的一部分,脫離了產品的線條、形狀、色彩等要素不再具有大眾為之消費的市場功能,無論該設計是否在物理上或是觀念上能夠與產品的實用功能相分離。至于觀念上的可分離性本身指的就是產品的美學功能與其實用功能在物理上不可分割,美學表達僅在觀念上可以和其他載體相結合,這更加表明“分離”后的美學表達對產品整體的不可或缺性。可見,外觀設計專利權中設計和產品之結合產生的市場競爭優勢恰恰是法律從自由競爭活動中將其選擇出來允許壟斷的一種利益。因此外觀設計專利權雖然和著作權有著歷史的糾葛,有著創作上的同源性和對象上的同質性,但其終點不會是回歸于著作權,設計結合于特定實用產品產生的市場競爭優勢就是外觀設計專利權存在之意義,這個領域著作權不應涉足。
由此推之,產品設計這一對象上可以存在多種利益,其裝飾性的設計表達體現的是美學創新上的價值,和具有實用功能的產品相結合體現的是大眾消費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如果經不斷地宣傳還可能產生顯著性,那么設計可以具有識別來源的功能。正是不同的客體利益決定了同一對象上可以存在多個權利,同一個設計對象上都可以存在著作權、外觀設計專利權、甚至商標權或特有裝潢權,每一個專有權保護的利益均有不同,從客體角度而言這并非多重保護,而是“各自為政”。一種權利的過期或失效當然并不影響他種權利,但是同時他種權利也無法延及已經過期或失效的客體利益上。正如有學者所言:“外觀設計專利權排斥的只是同類商品的外觀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的設計,而不排斥不同類商品或根本不存在特定商品的情況下,他人使用相同設計,因為那是著作權的任務。”熊文聰:《知識產權權利沖突:命題的反思與檢討》,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3期。
可見,工業品外觀設計一旦獲得外觀設計專利授權,權利人僅能憑借該項專有權去控制他人在相同或相似用途產品上使用相同或相似設計的行為。如果行為人將相同或相似的設計在不同產品上應用,這種行為則不再是外觀設計專利的權利范圍。如弓箭國際與義烏市蘭之韻玻璃工藝品廠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再審案中(下稱“弓箭國際餐具用貼紙案”),最高人民法院明確指出:“外觀設計應當以產品為依托,不能脫離產品獨立存在。因為外觀設計專利必須附著在產品載體上,所以外觀設計專利需要和產品一并保護。確定被訴侵權產品與涉案外觀設計專利產品是否屬于相同或者相近的種類是判斷被訴侵權設計是否落入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前提。涉案專利產品是‘餐具用貼紙(檸槺),其用途是美化和裝飾餐具,具有獨立存在的產品形態,可以作為產品單獨銷售。被訴侵權產品是玻璃杯,其用途是存放飲料或食物等。雖然被訴侵權產品上印刷有與涉案外觀設計相近的圖案,但該圖案為油墨印刷而成,不能脫離玻璃杯單獨存在,不具有獨立的產品形態,也不能作為產品單獨銷售。被訴侵權產品和涉案專利產品用途不同,不屬于相同種類產品,也不屬于相近種類產品。因此,被訴侵權產品的外觀設計未落入涉案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弓箭國際的申請再審理由不成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2)民申字第41號。 可見原告即再審申請人試圖以外觀設計專利權控制他人在不同產品上使用同一設計的行為未獲法院支持。此種情形下,能夠獲得法律保護的另一個途徑就是著作權,當然前提是工業品外觀設計構成“作品”,符合“獨創性”,著作權人就可以禁止他人在任何載體上進行復制、發行。如沈某訴金某紅包設計侵權案,涉案原告沈某設計的“紅包”獲得了外觀設計專利授權,被告則在糖果盒上使用了相同的設計,雖然案發時涉案外觀設計專利尚處在保護期內,也并未被認定為無效專利,原告提起的則是著作權侵權訴訟,法院依法認定了涉案紅包圖案的獨創性,從而認為被告金某未經許可,在其向公眾銷售糖果時使用了印制有“紅包外觀設計專利顯示的圖案的糖果盒,侵犯了原告沈某的著作權”。參見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杭民三初字第65號和第66號。 著作權僅保護要素表達上的審美價值,審美價值并非當然產生市場競爭優勢;外觀設計專利權僅保護要素表達結合于特定產品產生的市場競爭優勢,兩案清晰的表明了著作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各自的權利范圍和保護客體實無重疊可言。
(二)權利客體的區分有利于避免“后門專利”的出現
外觀設計專利權和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并不相同,也不會交叉重疊,一種專有權無法延及另一專有權的權利范圍,如果著作權的保護延伸至工業品外觀設計必然會出現“后門專利”,即未經審查、公示的專利權,其實質上獲得的是類著作權的法律保護。“后門專利”會使得所保護的權利在不經公示的情形下獲得專有權,而且是保護期限最長、權利內容較廣的著作權保護。然而帶有設計的工業產品均是要投入市場進行消費的,同類產品的市場競爭者為了回避他人的“后門專利”,就要等待他人產品上市后才能獲得相應信息,同時其還必須進行相關的市場調查,這將大大增加設計成本,而所有的設計成本最后都是要轉移至消費者身上加以實現的。
在歐可寶貝公司兒童座便器、座便器墊和沐浴躺椅案中,原告為其設計的小兔、小鴨坐便器和小熊沐浴躺椅主張版權保護,被告抗辯其既沒有申請外觀設計專利權,也不具有審美意義和藝術性,不應獲得著作權保護。法院認定了原告的三種產品均不屬于慣常設計,造型獨特,具有審美意義和藝術性、獨創性和可復制性,應當受到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二中民初字第12293號。 顯然法院在本案中用著作權保護的是原告設計上的審美價值,然而原告起訴被告則是因為被告銷售相同產品的行為損害了其市場利益,容忍被告行為會使得其設計的產品在相關市場中不再獨特,甚至于“普通化”,而這個利益是外觀設計專利權保護的客體,本案被告未申請外觀設計專利就不應該保護,法院的判決是明顯將著作權延伸至了外觀設計專利權的范疇。
再如“宜家兒童椅”案,原告宜家公司主張其設計生產的兒童椅應獲得著作權保護,被告則抗辯其屬于實用產品,由此訴訟的爭議焦點即在于兒童椅是否構成實用藝術品,從而獲得著作權的保護。當然法院認定“系爭的瑪莫特(Mammut)兒童椅和兒童凳的設計要點主要體現在造型線條上,但從整體上看其與普通的兒童椅和兒童凳在外形上的區別不大,屬于造型設計較為簡單的兒童椅和兒童凳,在藝術性方面沒有滿足構成美術作品的最低要求,因此不屬于美術作品范疇中的實用藝術作品,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因而,被告的上述行為不構成對原告著作權的侵犯”。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8)滬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87號。 法院在本案中雖然并未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但是原告的訴訟請求即通過版權獲得工業品市場競爭優勢必然在訴訟中引發“實用藝術作品”的認定,而這個問題不但在我國,在國際上也是無法取得一致的爭議性問題,只會帶來訴訟的復雜化。筆者認為實用藝術作品實際上就是工業品外觀設計,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應當建立未注冊設計制度。
結論
“對象指法律關系產生的事實因素,而客體是法律所保護的特定利益關系”。劉春田:《知識產權的對象》,載《中國知識產權評論》(第一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124—125頁。 權利客體區別于權利對象,因此著作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重疊保護是個偽命題。即便是同一個設計表達,其上的權利也絕不是多重,而只能是多個,多個權利之間并不發生重疊。當法律規范均以激勵創造為目標時,同為創造類知識產權的版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均對各自不同的利益進行激勵,彼此并不疊加。在承認知識產權的權利客體各不相同這一前提下,所謂權利的重疊保護并非多重保險,也不會對創造有多重激勵,知識產權是雙刃劍,多重保護意味著公有領域的資源會進一步被剝奪,意味著公眾本應從知識產權向公有領域流動中的獲利遭到阻隔,這只會阻礙智力成果的傳播,損害自由競爭。
Abstract:With regard to basic theories on civil law, the subject matter and object of the right are difficult issues to understand and the key to the issue is that whether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object of the right are semantically consisten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by civil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have both caused theoretical disput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standards for judicial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object lie in different scopes of the right, that is, the former is the internal factor of the right, which refers to interest;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external factor of the right, which refers to specific facts. The prop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elements can contribute to resolve the “overlapping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and industrial design patent with the same natures but different interests to protect. Therefore, in this sense there is no overlapping protection of these two rights.
Key words:subject matter of the rightobject of the rightoverlapping protectionindustrial desig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