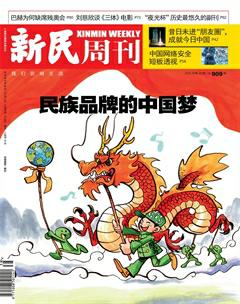信息時代需要怎樣的信息文明匹配?
劉洪波
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正在武漢進行,政府部門、業內專家、國內外安全企業濟濟一堂,大量網絡安全案例公布。在新近發生過準大學生徐玉玉因網絡詐騙而自殺后的這個活動受到了大量關注。
今天是所謂信息時代,這個時代就是建構在網絡之上的。但人們對網絡的認識,并沒有達到“時代基礎建構”的高度。人們更多地還是在從個人與網絡的部分交往來看待網絡,而沒有形成一種內化為基礎認知結構、世界觀層面的網絡觀。人們或者認為網絡是“新媒體”,或者認為網絡是“娛樂平臺”,或者認為網絡是社交空間,如此等等。人們還沒有將信息文明上升到與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等量奇觀的地位來認識。
當人們說到“網絡文明”時,想到的大概就是“文明上網”,怎樣在網上做一個負責任的人,怎樣上網有度而不染上網癮,怎樣在網上約束自己而不要認為網上沒人管得著,等等。而當人們想到農業文明時,會想到人與自然的合一與沖突,時令節氣、播種收獲、自然經濟、田園牧歌、君主制度;當想到工業文明時,會想到大工廠、大公司、組織化生產、全球貿易,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體制、文化生活。事實上,信息文明也應是這樣,它不只是指網民該怎樣上網,還包括被信息所改變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形態,和個人生活方式、生活觀念,以及植入個人意識深處的思維基質。
僅僅從安全觀念上來說,農業文明有農業文明的安全觀念,工業文明有工業文明的安全觀念。在農業時代,安全問題是天災人禍、猛禽野獸、瘟疫蟥蟲等。在工業時代,安全變得復雜起來,機器、電力、車輛、輻射等等,使生活安全、生產安全問題變得突出,安全用電、安全駕駛、安全操作成為重要技能,人與人關系的復雜化,導致了隱私安全觀念的出現,城市生活、陌生化社會改變了每個人在舒適距離內知根知底的交往模式,使得交往中的安全距離、法律契約等規范興起。
在信息時代,網絡安全也不應只是一種技能,而應成為一項素質。就像我們在工業時代已經把安全用電作為常識,在“信息文明”這樣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下,網絡安全也應當成為不言自明的素質。在這個時代生存,就不僅要能夠通過網絡獲得生活和生產的便利,還要懂得網絡安全的常識。
信息文明已經很深地改變了工業文明的安全環境,也內在地約定了新的安全規則,但人們未必深切地了解。現在,個人失去了數據所有權,失去了控制自身信息的權利,數據挖掘的行為及結果的使用都是不在主體控制之內的。個人身份數據、社交數據、刷卡和消費數據、手機通信記錄、就醫記錄等等,往往是在辦理事務中自動生成的,素材一般是個人主動提供,人逐漸成為透明的電子人格體。網絡的根本特征是共享,這意味著當你接入網絡,就隱含地同意把自己作為被共享的一部分,交出自己的隱私。
人被數據表征出來,而不是數據被人表達出來,主體想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樣的人不重要了,客觀累積的數據顯示著你是什么樣的人。人們對隱私泄露的劃分與接受底線都在移往出讓隱私的方向,個人隱私觀在信息文明下將不得不開放,要絕對保護隱私,只有離開網絡,而這意味著你與社會脫離。你在網絡上留下的一切零碎足跡,都在泄露著你的隱私,或者在書寫著你的隱私,數據整理可能還原一個比你自己認為的更加真切的你,所有數據足跡都無法根消除,于是你還失去了“被遺忘權”。
工業文明下的隱私觀,與信息文明下的隱私消失形成了巨大的沖突,安全觀念的信息文明升級版還未成熟。不僅個人安全在變化,工業時代的知識權、商業機密等等,乃至亙古以來的疆土安全、政權安全、社會安全等等,在信息文明下都面臨新的態勢。從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來適應信息時代,現在恐怕還談不上已經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