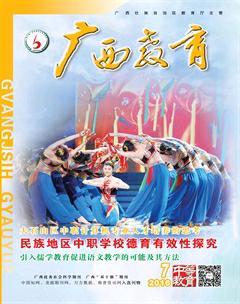重視、尊重和超越:中學語文教材使用方法談
周瑩
【摘 要】從重視教材、尊重教材和超越教材等方面探討語文教材使用方法,促使教師更好地理解和創造性地使用教材。
【關鍵詞】中學語文 教材 使用方法 尊重 超越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07B-0094-02
語文教材是課程目標與教學實踐活動之間的媒介,是對學生進行聽說讀寫訓練的依據和憑借,是學生德智啟迪、語文歷練、語言積累的重要載體。因此,作為語文老師,只有了解語文教材的特性和使用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創造性地使用教材。這里說的語文教材是指根據語文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編寫的,供語文在課堂上指導學生學習和掌握母語文本材料,即常說的語文教科書。筆者結合教學實踐和語文學科的特點,提出語文教師要正確使用語文教材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重視教材,并將其作為“例子”使用
那些入選語文教材的篇目,往往都是經過這方面的行家里手根據教學大綱和課標反復權衡篩選出來的,自有其經典性和典型性,也有其相對的歷史合理性和代表性。在某一歷史時期,它們無疑是最好的。我們既然要重視教材,當然可以將其作為“例子”使用。甚至可以說,就像數理化里的“例題”,通過對“例題”的學習,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若簡單地以“教材無非是個例子”為由隨意地對待教材,毫無疑問是一種輕率行為,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新課標語文教材與其他教材尤其是理科教材不同,語文知識方面,語文課本本身不直接介紹語文知識,語文知識是滲透在課文中的,它所選用的課文不是以知識解說形式出現,而是以知識的運用形式出現。比如,要教授修辭知識或表達技巧的知識,不是講解修辭知識或表達技巧的知識本身,而是要讓學生通過對課文的學習來實現。如必修一《記念劉和珍君》課文里的句子:“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教師可在教學中可以這樣設置問題:這里運用了什么手法?是如何運用的?說明了一個什么道理?作者對“請愿”持什么態度?通過啟發、探究和分析,很容易得出結論:作者在這里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作者將人類前行的歷史比作煤的形成。大量的木材——喻代價巨大的流血斗爭;結果卻只是一小塊——喻才能前進一小步。木材變成煤需要付出很大代價,那么,人類前進也需要付出很大代價和犧牲。“但請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其中”指流血斗爭。這就表明,請愿是不在這種需要付出代價和犧牲之列的,徒手請愿就更不起作用了。這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向反動派請愿難以換來人類歷史的前進,請愿不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斗爭方式,必須吸取血的教訓,改變戰斗方法。這樣,把課文這段文字作為例子,通過探究學習,學生對比喻修辭手法的表達技巧自然掌握了。當然,教師不能停留在僅僅要學生掌握該句的修辭手法,而是要拓展延伸、鞏固。
教師只有重視例子,并通過對一個一個典型的“例子”精心設計教學,才能達到教學目標,如語文積累、思維發展、智力開發、能力訓練、情感培養、人格完善、審美教育、個性發展,等等。
可見,語文教材的突出功能是教師傳授知識的憑借和載體。“語文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葉圣陶語),說的就是教材只是開發學生智力、培養學生能力和學生語言積累、知識擴展的中介。教師在教學中主要不是讓學生掌握教材本身,而是要把教材作為例子,借助教材并使學生掌握某一類知識的規律或培養某方面的能力。
二、尊重教材,學會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
所謂尊重“例子”,就是需要語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根據編者意圖或作者創作意圖充分挖掘文本里隱含的語文元素,而不是隨心所欲天馬行空般任意發揮。如《記念劉和珍君》,是魯迅對“三·一八”慘案的述評。文章第一、二節是說寫作的緣起,側重于探求本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魯迅的筆觸涉及三類人:反動勢力、愛國青年和處在中間狀態的所謂的“庸人”。憤怒地控訴段祺瑞政府虐殺愛國青年的暴行,痛斥走狗文人下劣無恥的流言,無比沉痛地悼念劉和珍等遇害青年,奉獻他的悲哀和尊敬。一方面告誡愛國青年要注意斗爭的方式,另一方面頌揚“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的勇毅,激勵人們“更奮然前行”。文章其中一段詳寫了烈士遇難經過:劉當時中彈,是“彈從背入”,可見并不是與軍警面對面地搏斗,證明她完全是無辜的,她不是什么“暴徒”,倒是執政府衛隊的卑鄙。手槍是軍官使用的,證明這次屠殺是有人指揮的,事前籌劃好的。這些鐵的事實,有力地戳穿了段祺瑞政府對死難者所橫加的種種罪名——這就是作者的用意——對遇害經過的詳細、客觀的記敘,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使軍閥的滔天罪行和流言家的無恥讕言不攻自破。
扣緊并正確解讀教材,是尊重教材的前提。既然教材是個“例子”,那么,當然需要師生能對例子精確解讀(當然允許個性化解讀,這另當別論)。根據課標和教學目的,既要扣緊“例子”,也要有所取舍。假如連文本這個“例子”都掌握不好,一知半解,這種對教材的不尊重,在教學中將“例子”擱置一邊而去奢談延伸拓展,豈不是自欺欺人?
筆者曾經觀摩一次優秀年輕老師語文課堂教學比賽,上的是人教版新教材必修四第二單元《念奴嬌·赤壁懷古》。其中一執教者在教學過程中,一開始叫學生誦讀3分鐘后,就板書他的教學主要提綱:豪景—豪人—豪情。接下來給10分鐘學生“合作探究”后提問:寫了哪些豪景?寫了什么豪人?抒了哪些豪情?在師生的一問一答中,教師基本上架空“例子”,至于詞中究竟是如何體現“豪”字的解讀教師只是輕描淡寫、蜻蜓點水。這種將“例子”撇在一邊的教學有點“顧左右而言他”之嫌。試想,假如沒有“淘、穿、卷”等字詞的探究解讀,又如何得出“雄渾壯闊,撼人心魄,氣勢磅礴”的詞的意境呢?對于“豪人”、“豪情”的解讀亦然。對于這種因為“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而拋開對教材文本的解讀的做法,筆者不敢茍同。
三、超越教材
要超越教材(即“例子”),在教學中就不能只教學生學會“例子”而已,而是應將其看成中介和橋梁,通過這個中介和橋梁讓學生到達更廣闊的語文空間。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對寫景字詞的學習,如果只是讓學生停留在“淘、穿、卷”等字詞寫景作用的探究解讀,那毫無疑義是偏離了語文教學的根本。應在指導學生學好教材“例子”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將語文的觸角伸得更廣更深,學得更扎實些。指導學生由一篇課文的閱讀推及同一作家的同類作品,或由一位作家而觸及同類作家或擴展到同時代作家的對比性閱讀;包括引導學生在語文“例子”中學到的知識和能力創造性地運用于生活實踐中,等等。之所以說要超越“例子”,就是要教師不因拘泥于“例子”而墨守成規不敢越雷池一步。教有限的“例子”就是為了讓學生自己去學習“無限”的“例子”。如必修四第二單元,選了宋朝柳永、蘇軾、辛棄疾、李清照四位詞人各兩首詞。宋朝是詞的鼎盛時期,名家輩出,風格各異。選文有限,只能是兼顧豪放和婉約兩種風格,不可能也無必要囊括全部,這就需要教師把入選的四位詞人的各兩首詞作為“例子”,待學生掌握宋詞的特點及賞析方法后,再引領學生去涉獵他們四人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詞人的詩作。如“三蘇”、歐陽修、姜夔、周邦彥、范仲淹、晏殊、秦觀,等等。學了必修三第一單元《林黛玉進賈府》《祝福》《老人與海》后,可以引領學生課外瀏覽曹雪芹《紅樓夢》、羅貫中《三國演義》、錢鐘書《圍城》、巴金《家》、魯迅《吶喊》、雨果《巴黎圣母院》、托爾斯泰《復活》、屠格涅夫《獵人筆記》等名著。這就是教材例子的作用。
既然要超越“例子”,應允許教師對教材做合理補充、重組和提升。因為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知識更新迅猛,新思想新科技新成果層出不窮,而教材又是某一時期的產物,難免存在過時的觀點和陳舊的知識,教材不可能時時更新。這就需要教師根據實際情況和教學需要做補充,使教材變成活的教材。
當然,要把語文課上好,除了重視、尊重和超越教材外,還要吃透編者意圖,了解教材特色。教材前言都有編輯說明,編輯說明闡明編輯指導思想、編寫的意圖和理論基礎。不同的編輯思路,形成教材不同的特點、不同的風格。教師從編輯說明中知道了編輯指導思想,知道了教材的特點、風格、總體結構和體例,從而更好地把握教材。每一套語文教材,都有一個完整的教學目標體系,這個目標體系又都被逐一分解到每一冊、每一個單元中。教材中的每一篇課文(或教學內容)都是每一冊書每一個學段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教師在正確把握整套教材的總體構思的基礎上,按照編者在教材中體現出來的整體思路來設計教學過程,運用相應的教學方法。如人教版《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結構體例,在編輯說明中都說得很明確,如該實驗教材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類,1-5冊為必修。每冊必修教科書的內容分為“閱讀鑒賞”、“表達交流”、“梳理探究”、“名著導讀”4個部分,前3個部分納入課內學習計劃,“名著導讀”可在課外自主安排。每一部分學習要求、方法及側重點都做了說明,等等。教師只有從編輯說明中了解教材的總體構思及整個目標體系,才能對整套教材的教學成竹于胸,使用起來既切合實際又得心應手;才能找到好突破口,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精心選擇教學內容,合理安排教學程序;才能把教材教活。只有吃透編者意圖,才能懂得該從教材里教些什么,為何而教,如何教。
(責編 江月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