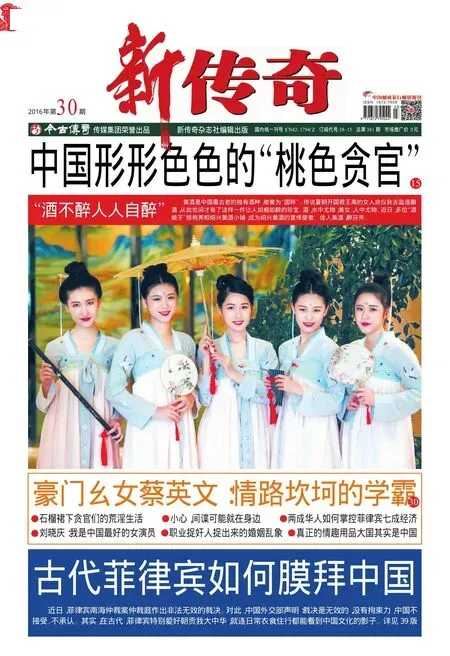越南勞工的“中國夢”
越南勞工的“中國夢”
從碩龍到大新,再到東莞,越南在華務工人員追逐著越來越大的夢想,也承擔著越來越大的風險。
2015年10月28日,黎明之前,天灰蒙蒙的。越南高平省下瑯縣一間農房里,38歲的黃春蘭已經起身。她用了半個小時做好早飯,叫醒了要下田耕種的丈夫,換上綠色工作服,走向中越邊界。繞過一個小山坡,黃春蘭只用了不到10分鐘就走到中方檢查站。中方武警隨便看了看邊民證,打了聲招呼,“返工啦!”她笑著應了一聲。一分鐘后,她就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大新縣碩龍鎮的老橋頭飯店——她的工作單位。

越南在華務工人員
九百米,越南勞工的希望
碩龍鎮位于大新縣城西面。地處中越邊境,邊境線長30余公里,鎮的中心是一條老街,鎮政府、商店飯館都集中在這里。老街西端是一座橋,橫跨歸春河,橋西是邊檢站,老橋頭飯店坐落在橋東。黃春蘭的家離老橋頭飯店僅有900米。早晨六點的光景,除了她,還有許多騎著三輪的越南人越過這座橋,車上裝滿越南特產——盔式帽、酸奶及香煙等,越南煙很便宜,十塊錢一條,但未經過烤制的香煙味道非常沖,非大煙鬼不能適應。這些越南商販在過境時要向中方交納一元人民幣的稅款。無論是黃春蘭,還是來來往往的越南商販,他們的衣著打扮都與中國人無異,甚至摩托車都掛著中國的“桂”字頭牌照。
碩龍鎮有一萬一千人,據碩龍鎮街道辦主任梁海燕透露,僅僅在老街上,有固定工作的越南人就接近一百人,他們或者當服務員,或者搞裝修,從事最底層的體力勞動,填補碩龍鎮的人力資源空缺。梁海燕自己也開著一間飯店,在老街的中心。在她的飯店里,有兩個越南服務員,月工資都是一千多。碩龍鎮飯店的顧客主要都是游客,這些越南工人的語言和壯語接近,和當地人可以交流,但無法勝任與游客的對話。
碩龍鎮上隨處可見飄揚的五星紅旗,無論是邊民的住家樓房,還是酒店、商店,也不論這樓房是高聳豪華,還是低矮簡陋,一律在樓房頂部用電焊固定鋼筋制成旗桿,上面高揚國旗。大新的交通主干道是325縣道,與老街成直角,這原本是一條軍用公路,為配合1979年的對越反擊戰所修建。
黃春蘭有兩個半大兒子,都已經不再上學。除了種地,阿蘭的丈夫和兒子都沒有其他固定收入,有時候爺仨會一起到中國打雜工。她在老橋頭飯店每月一千二的工資是全家最大的一筆收入。
每逢陰歷的2、5和8日,是中越雙方邊民的趕集日,這一天,前往碩龍賣東西的越南村民格外多。2013年以前,黃春蘭也是趕集大潮中的一員,將挖到的草藥野菜運到碩龍老街。經過的次數多了,看到老橋頭飯店生意興旺就有了打工的念頭。“雖然只有一河之隔,越南那邊還是比較窮的,她丈夫那段時間生病,急需錢用。”飯店老板寧女士告訴記者。2013年國慶節,由于生意繁忙,寧女士就收下了她。剛開始是按天算錢,過年后轉為固定工。
在碩龍,雙方村民過境不用護照,而是用邊民證,向當地的派出所申請核發,每年年審,成本20元。出入境只需在邊民證上蓋章,理論上必須當天往返,但偶爾停留幾天也不會有問題。由于邊境線太長,很多越南人甚至都不辦理邊民證,劃著竹排跨過歸春河就入境了,中方的邊界警察對此查得并不嚴格。
除了工資外,黃春蘭并沒有別的福利,寧女士逢年過節會給她包個幾百元的紅包。她知道當地人做一樣的工作工資是她的兩倍,也知道中國員工有五險一金,但她還是愿意留下來。“老板很好,客人也很好。”她反復說。雖然被客人罵過,她依然很滿足。在越南,女性地位很低,黃春蘭在家要等到丈夫兒子吃完飯才能用餐,中國女性地位之高讓她非常驚奇,“在我們店,都是老板娘說了算。”
九十公里,能干者的聚集地
當黃春蘭在打掃衛生時,她的丈夫正在距離碩龍鎮九十公里的大新縣城中做房屋外裝修。這里不但盛產龍眼,鉛礦和鋅礦都有很高產量,當地也有很多人挖山采石,早早就富裕了起來,幾乎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樓。
從2008年開始,越南的外墻雕飾開始傳到大新,很多大新人蓋樓后,外裝修指明要做越式風格——小洋樓一般會做個尖頂,窗欞比較精致,紅色為主色調,外立面做飛龍雕飾。“我們生意非常忙,基本上就是一單接一單,很少有空閑。”大新縣某雕飾公司的老板李福軍(化名)告訴記者,天龍是當地最大的越式裝修公司,李手下有二十多個越南工匠。
“現在大新有五百個左右的越南工匠專門從事外裝修。”李福軍說,他們一般由工頭帶領,進入國內。工頭會說中國話,了解國內裝修行情。
阮文賢三個月前來到大新,他沒有護照,也沒有邊民證,從山區小路進入中國的德天邊境,然后坐車到了大新。他是越南永福省人,今年17歲,有著一雙很濃的眉毛,矮矮胖胖,看上去很敦實。當記者見到他時,他穿著紅色T恤和牛仔褲,正蹲在腳手架上粉刷天花板。
抽煙是阮文賢生活中最大的開支項。平日里,他和同伴住在郊區的平房當中,兩人一張床,一間房住8個人。每天工作9個小時,沒有休息日,每月能拿到一千六百元。阮文賢并不喜歡中國,甚至有些敵對情緒。他覺得中國煙太貴,而且沒有勁,中國電視不好看,中國女孩太丑。他告訴記者,“胡志明市也有賺大錢的機會,我春節后要去那里。”
這種敵對情緒來自那場戰爭。大新商人李紅前些年經常去越南做進口木材生意,“很多越南人都滯留在大新,警方都不會管,但我們在越南多留一兩天都不行,酒店都會舉報你,把你抓起來。做生意聽說你是中國人就刁難你,到現在他們還認為我們是侵略者。”
然而,敵視與否并不能改變碩龍、大新勞動力逐漸短缺的現實。李紅最近租下了三百畝農田,打算種木瓜,但他怎么都找不到年輕勞動力,最后只好雇了十二個老年人幫他打理。“年紀最小的都五十六了,我挺害怕他們生病出事。”十一月是大新甘蔗成熟的季節,每當此時,漫山遍野的越南農民就從邊境涌過來當小工砍甘蔗,最多時超過五萬人。
越南勞動力逐漸憑借著各種的優勢占據了大新的市場,他們不僅年輕,而且還有技術專長。“很多人點名要求越南人裝修,他們不信任中國人的手藝,”李福軍說,他手下的“頭牌”是一對越南父子,父親從事外墻雕飾已有二十年,“那個效果中國人根本做不出來。”
雖然如此,賺大錢的還是李福軍這樣的中國老板。由于掌握了客戶,李福軍接單后再轉給越南人,30元每平米接的活25元轉包出去,這些越南人成為他的搖錢樹。雖然李福軍不夠光明磊落,但相比九百公里外的東莞,他已經是一個非常仁厚的老板了。
九百公里:越南打工者的終極夢想
東莞是越南打工者的終極夢想,每年的9月和10月,他們在越南工頭的帶領下,乘坐各種交通工具,以每批數十人的規模來到這里。
東莞的勞動力成本一路攀升。“新勞動法規定了工人底薪與加班費的標準,企業賺錢的利潤空間就縮小了。”一位電子廠的老板告訴記者,目前他手下的工人月平均工資在四千元。2015年年初,東莞市還調整了全市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包括平時及周末的加班費用,但越南工人并不在此列,他們的普遍時薪只有每小時10元,沒有任何加班補償。
引入便宜的越南勞工,成為東莞制造業的現實需求。據不愿透露姓名的當地公安介紹,電子廠和制衣廠集中的厚街和常平成為引入越南勞工最多的兩個鎮。“他們沒有護照,更沒有工作簽證,屬于非法勞工,老板不讓他們外出,所以很難統計具體數字。”
與碩龍的打工者不同,東莞的越南勞工存在著明顯的剝削階層——工頭。除極個別單獨闖蕩的越南人,越南勞工都由工頭介紹。他們懂中國話,在越南物色老鄉,并提供入境、聯系工廠的一條龍服務,最后還幫助東莞老板管理工人。老板每月會把工資發給工頭,工頭從中扣除20%,再轉發給手下。“這些工頭對手下經常恫嚇,不聽話就威脅要把他們交給警方,有時還有暴力毆打。”上述公安說。
從碩龍到東莞,越南在華務工人員追逐著越來越大的夢想,也承擔更多風險。即便如此,黃春蘭仍想將兒子送過去,她也想一直在老橋頭飯店做下去,攢錢為家里蓋一棟樓。寧女士卻已經在考慮解雇她,“稍微要說話的活就做不了,我在旁邊做事時常要被叫過去幫忙,”寧女士說,“只要能招到本地人就不讓她做了。”
(《看天下》2015年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