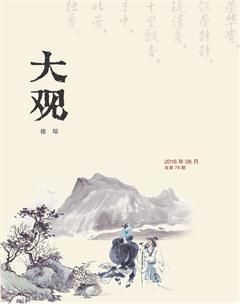論樓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特色
摘要:樓棲的作品創(chuàng)作與他自身的經(jīng)歷和性格有密切聯(lián)系。這使其作品在語言和技巧的妙用下,主題得以深化;把滿腔的熱情融入客家的風(fēng)俗文化中;對時政熱點予以人生的思考。樓棲的作品以其獨有的創(chuàng)作特色而獨具一格。
關(guān)鍵詞:樓棲;意蘊;人文風(fēng)俗;赤子之心
在《我是怎樣走上文學(xué)道路的》一文中,樓棲寫道:雖然從小生長在梅縣貧困山區(qū),但是童年在書本的陪伴下卻是快樂的。長大后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終得以升學(xué),并直言“我喜歡讀書,愛好文學(xué)”。在九一八事變后所發(fā)表的《西湖堤畔》激發(fā)了他的創(chuàng)作文思。此后,樓棲頻繁參加各類文學(xué)活動,發(fā)表各種文體的文章。在中大遷入石牌新校后,樓棲就從未間斷,不斷寫作,從而開始他的文學(xué)生涯。可見樓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僅與他的成長環(huán)境和求學(xué)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更是與個人性格愛好緊密相連。樓棲作品的創(chuàng)作特色,可從以下三方面探求。
(一)語言通俗易懂,技巧潤物無聲,深化主旨意蘊
在樓棲讀初中三時,學(xué)校突然由慣用的文言文改寫為陌生的語體文。或許正因為這個契機,樓棲不僅得到文言文的洗禮,而且諳熟白話文的運用,所以,樓棲兼顧二者之所長,既發(fā)揮古文的平仄韻律之感,又彰顯現(xiàn)代文的通俗易懂之意,并靈活嵌入各種表達技巧以層層推進,使文章簡潔明了又暗含深意。
冬殘了。河邊的蘆葦綴上了白色的毛茸茸的花絮,河流如負重荷的旅行者慢慢蠕動著漂浮的白沫。郊野連接著山林,凄惶地呈露著衰老枯黃的姿態(tài)。只有蒼綠的松林,還在凜凜的風(fēng)濤中描畫著秀逸俊拔的傲然的風(fēng)姿,蒼老中活躍著年少的青春。河床上的竹林,青蒼的綠意,已掩不住凋殘的衰老了。枯萎了的片片黃葉,在蕭殺的寒風(fēng)里顫抖、凄迷。一片田疇,交錯著新綠的麥苗,與冒著黃花的碧綠的油菜。[1]
《歲暮》的開篇描繪了殘冬歲暮的凋敗景色。開頭第一句“冬殘了”,以短而有力的概括性句子奠定全文悲愴的基調(diào),暗示這凋殘的何止是冬天,更是林太太的生活,更是“中產(chǎn)以下的人家”的生活。樓棲描繪入微,以情景交融的方式,以景物的衰敗暗喻生活的艱辛,以常見的事物(如蘆葦、河流、山林、黃葉等)用淺白的話語組成我們?nèi)粘5木吧嬀怼!鞍啄薄ⅰ八ダ峡蔹S”、“凋殘”、“凄迷”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冬確是殘了。隨著文章的節(jié)奏發(fā)展,發(fā)現(xiàn)生活也跟著氣候一樣是殘的。樓棲用質(zhì)樸的語言把四季氣候、日常生活情景在文學(xué)的世界里重新雕砌,在技巧的潤澤下凸顯主旨意蘊,并使讀者有即視感般的感受。
在《鬻兒之夜》中夫婦倆為賣兒鬻女而猶豫不決的爭吵情景,同樣刻畫得栩栩如生,此情此景宛如在眼前。亞泉媽要抱著兒子一塊死,走到門口前的動作更是一氣呵成,十分符合人物思想的發(fā)展邏輯,毫無矯揉造作,仿佛作者親臨現(xiàn)場,親眼目睹般自然。
(二)描繪家鄉(xiāng)的衣食住行,表達對家鄉(xiāng)人文風(fēng)俗的熱愛
樓棲是土生土長的梅縣人,從小接受的是客家的風(fēng)俗習(xí)慣和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樓棲認為,客家民間的“民歌搖籃,哺育著我的童年,成為我的文學(xué)養(yǎng)料”。[2]兒子鄒啟明也回憶道“父親是客家人,一輩子都改不了他的客家鄉(xiāng)音。無論是說普通話還是講廣州話,都像說客家話”,“在家鄉(xiāng)也沒有什么親人,但他對家鄉(xiāng)卻有著很深的感情”。[3]因此,樓棲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穿插了大量的客家文化。
在《楓林》中的六七個婦人家的客家服飾:“她們的頭裙,鑲白竹布邊,系紅絲帶,好像幾朵山茶花,迷死人”。在《外婆——童年雜憶》中“外婆家是一座祖居老屋,正座三廳,橫屋四棟。從左邊第二棟橫門進去,踏入一個灶下間”;“午飯后,我們出來禾坪上曬太陽。母親納鞋底……”;“母親把帶來的年糕、煎堆、雞腿、熟肉等禮品點給外婆”;“回到房里,外婆要母親留一些年糕、煎堆帶回去,壓壓篾籃底”。客家人獨特的生活起居、飲食習(xí)慣以及過年禮節(jié)景象都躍然紙上。關(guān)于客家的勞動工具,在《春茶》中有簸箕、竹蘿、松膠火、“涼河”,而茶葉本身就是客家地區(qū)常見的經(jīng)濟作物;在《木匠阿筧》中有火斗、打谷板。甚至在語言方面也充斥著客家方言和客家民間俗語,《春茶》采茶人不時唱的山歌:“上山采茶茶葉青……摘葉留心等后生”;《楓林》中展現(xiàn)的歇后語“草里攢壽星公吊頸——嫌命長”,諺語“丑人多作怪,癩痢好花戴”,俗語“二貢頭”、“腳踏馬屎傍官勢”。
作品中信手沾來的客家習(xí)俗,印證了樓棲對客家風(fēng)情和人文情懷的熟悉程度;字句中暗藏的真情實感,抒發(fā)了樓棲對家鄉(xiāng)的人、事、物的無限眷戀之情。
(三)對時政的關(guān)注和人生的思考,顯露赤子之心
從樓棲《我是怎樣走上文學(xué)道路的》一文可知,他第一篇散文《西湖堤畔》的發(fā)表,以及產(chǎn)生創(chuàng)作文學(xué)欲望的緣由,是因為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故樓棲的文學(xué)作品大部分為抗日戰(zhàn)爭前后所寫,作品基本都烙上了家仇國恨、救亡圖存的印子,并從中引發(fā)自身對社會價值、人生真諦的思索。
樓棲的詩歌主題幾乎都為面對非正義戰(zhàn)爭時,對敵人賊國以憎恨鞭撻,對人民祖國以同情鼓舞。在《錘石婦》中,描述婦人日以繼夜的錘石粒,最終婦人只是錘壞了健康,卻沒有錘走饑荒,抒發(fā)作者對錘石婦一類的底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對長期處于“吃人”狀態(tài)的社會的強烈斥責(zé)。《征懷》一詩贊美了中國兒女的豪情壯志、勇敢殺敵的英姿:“南國佳人而今換了戎裝……誰說中華兒女會俯首低頭?……恃強者授首而血流成渠了……眉梢猶剩喋血的微慵……”《南方的城市》講述紀念廣州淪陷兩周年的事件,而《島國的世紀夢》則講述香港淪陷并進行保衛(wèi)戰(zhàn)的事件,兩首詩歌都表達“屈辱的日子從此消亡,光榮屬于新生的南方”、“而那蟄伏了千萬年的九龍,將在激浪里翻滾更大的巨浪”。樓棲以一個捍衛(wèi)者的身份,宣誓對祖國的每一寸土地的堅守,表達對祖國前程似錦的美好愿望。雜文《奴才的嘴臉》中,樓棲借用我國古人的媚外風(fēng)氣,痛斥現(xiàn)今帶有媚外嘴臉和狐假虎威的奴才,諷刺“侵略者沒有進步,倒是奴才進步了”,在此樓棲對奴才們大有“恨鐵不成鋼”的痛心之感,從而篤定所屬國籍要對祖國忠誠,肯定國情懷的重要性,可見作者愛國愛民的昭昭之心。
綜上所述,樓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在扎實的語言和技巧的功底下,是在蘸滿自己的真情實感的過程中,描繪家鄉(xiāng)的傳統(tǒng)民俗民風(fēng),書寫時政人生的災(zāi)難與思索。雖然樓棲一生的作品數(shù)量不多,但是仍以僅有的優(yōu)秀作品為中國文壇的繁榮盡一份努力。
【參考文獻】
[1]樓棲.歲暮.樓棲作品選粹[M].花城出版社,1994.
[2]樓棲.我是怎樣走上文學(xué)道路的[J].新文學(xué)史料.1997(04).
[3]蔡宗周.中大童緣(上冊)往事篇[M].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14:58.
作者簡介:周瑞婷(1990~),女,廣東廣州人,廣東技術(shù)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