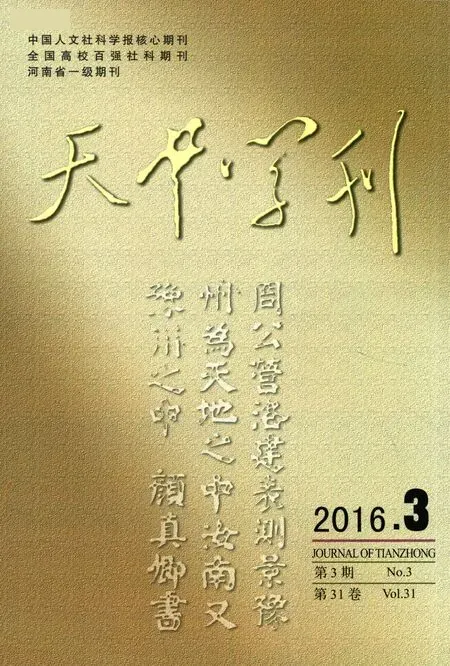切爾卡斯基的漢學研究置喙
侯海榮,宋紹香
(1.吉林師范大學 博達學院,吉林 四平 136000;2.泰安學院 外國語學院,山東 泰安 271021)
切爾卡斯基的漢學研究置喙
侯海榮1,宋紹香2
(1.吉林師范大學 博達學院,吉林 四平 136000;2.泰安學院 外國語學院,山東 泰安 271021)
切爾卡斯基對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新詩的研究成為海外漢學界的一座高峰。切氏以其鮮明的比較、開放、建構、批判、整合意識對中國文學展開文化理解與文化想象。緣于意識形態、文化心理、詩學觀念、時空距離、先在結構、思維范式等諸多差異,切氏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探尋為中國學界打開一重要窗口。在中國當代學術建設生成與敞開的參照系中,理性的態度是以反思的姿態關注漢學一隅的批評話語,在“視界融合”后形成創生張力,進入雙方文化對話和重建的主流。
俄羅斯漢學;切爾卡斯基;域外文化交流;中國新文學研究
20世紀下半葉,俄羅斯出現了兩位堪稱“雙子星座”的世界頂級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和切爾卡斯基(1925—2003年)博士,他們將其對中國文學與文化情有獨鐘的熱忱貫穿于漢學研究的始終。切爾卡斯基憑借豐贍的學術論著成為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研究的權威學者。然而,正如俄羅斯漢學文藝理論家熱洛霍夫采夫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人們對俄國文學的認識由來已久……但是俄國對中國的文學文化的研究成果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反應,這不禁令我國的學者對自己工作的真正價值產生懷疑。”[1]漢學作為中外文化的“混血兒”,既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亦是反觀自身的“文化之鏡”,因此,對切爾卡斯基的學術軌跡進行歷時考察,將其對中國文學的翻譯、研究搜羅裒輯并加以公允評析,尤為必要。
一、切氏之學術成果要覽
切爾卡斯基中學畢業時恰值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因視力欠佳不能入伍而進入軍醫學校,曾任炮兵營副軍醫。戰后因其母親的努力他得以進入莫斯科軍事外語學院學習漢語,該院乃俄蘇漢學的重鎮,切氏漢學之路由此開啟。他以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作為研究的客體,以本土文化語境為基點,輔以來華進修的優勢,探驪得珠,成果頗豐。縱觀切切爾卡斯基的漢學成就,其治學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發端期(20世紀50—60年代)
1951年,切爾卡斯基被派到西伯利亞赤塔市蘇軍司令部任職,他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一些中國文學作品,點燃了漢學研究的星星之火。50年代末切氏考取了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師從漢學家艾德林,規定課題是曹植研究。切氏真正的漢學研究就是以研究曹植為肇始的,1963年他在漢學界嶄露頭角,寫出了成名作《論曹植的詩》。該著專題論述了曹植詩歌與樂府民歌的有機聯系,尤其對《洛神賦》及曹植詩歌的典故作了精辟考辨,闡釋曹植詩歌的創新特質及審美價值,并通過對曹植創作道路的剖析,展示了以漢朝末代皇帝年號命名的建安文學的成就及其對后世詩壇的影響。切氏認為,曹植作為“建安之杰”,他的辭賦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之一,“在公元2—3世紀,這種詩體正由鋪敘事物的敘事詩轉向抒情詩(短賦)”,“在民歌基礎上創立樂府詩體,極具研究價值”[2]。切氏初試鋒芒,跨越了中國古漢語的瓶頸,可以說《論曹植的詩》是其漢學里程中首部標志性著作,具有界碑意義。此后,他在中國現代文學這塊學術陣地,鍥而不舍,鉆之彌堅,將學術重心轉移到了中國新詩的編譯、著述、詮釋、闡論方面,力作迭出,見表1。

表1 切爾卡斯基20世紀50—60年代漢學成果匯總
(二) 高產期(20世紀70—80年代)
切爾卡斯基從20世紀70年代起奮力墾拓,其漢學研究臻至巔峰狀態。這一階段切氏對現代新詩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度開掘與廣度覆蓋,翻譯與研究平分秋色,堪稱切氏學術生命的黃金期與學術成果的豐收期。從翻譯總量來看,切氏譯詩歌千余首,涉及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詩歌包括不同社團、不同流派代表詩人的代表作品,選譯詩歌之廣、詩人之全、詩篇之準、質量之精,堪稱世界之最。《雨巷》《五更天》《蜀道難》三部譯作含編選并作序,組成一個年代系列,勾勒出詩歌演進的嬗遞動態,共選入95位詩人的434首詩歌,提供了中國20世紀20—80年代現代詩歌創作的概貌。《中國新詩論》《中國戰爭年代的詩》《艾青:太陽的使者》,實現了對中國現代詩歌發展史“點面結合”的一種描述。《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國》和《俄羅斯文學在東方:翻譯理論與實踐》是切爾卡斯基別開生面的一類著作,作者從翻譯學的視角提出了制約文學翻譯的文學傳統、翻譯心理、原文形象、民族傳統諸多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問題。切氏這一時期的漢學成果見表2。

表2 切爾卡斯基20世紀70—80年代漢學成果匯總
(三) 平歇期(20世紀90年代至2003年)
眾所周知,以發生在1991年12月25日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為標志,長達69年的蘇聯政權解體。俄羅斯國內政治風云的動蕩變幻,亦殃及漢學家的命運。自20世紀90年代起俄羅斯漢學界逐漸蕭條,漢學研究隨之落潮。切爾卡斯基身為猶太人,1991年移居故國以色列,任教于耶路撒冷大學,由著述轉向講學,以另一種方式傳播中國現代文學,延伸著漢學研究。1993年,他的專著《艾青:太陽的使者》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而其專著《徐志摩:在夢幻與現實中飛行》則成為遺作,在俄羅斯一直沒有發行,直到2015年才出現中譯本,由中國知名翻譯家宋紹香完成。由此可見,切爾卡斯基的漢學成就一方面受到作者自身學術歷練的規約,同時與國內政治環境和蘇中關系起伏(蜜月期——冰封期——解凍期——升溫期)密切相關。切氏這一時期的漢學成果見表3。

表3 切爾卡斯基20世紀90年代后漢學成果匯總
二、切氏的現代學術意識
海外漢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豐富的認識框架與多元的學理空間,此乃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層面。“正因為‘漢學’在知識譜系上屬于‘東方學’,能夠‘全息’地舶來外緣文化觀念,才反而更值得好好研讀,以便既取其具體結論又取其具體方法為己所用”[3]。切氏以其執著的學術個性形成了自身漢學研究的獨特格局。觀其特點,茲舉犖犖大端。
(一) 比較意識——中俄互鑒
作為稱職的漢學家,切爾卡斯基的研究對象不僅是中國的文學文本,而且包括其文化背景。比較文學是以跨國度、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文學內部、外部的透視與匯通。切氏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在中俄兩種異質文化間總能尋捕到某些牽系、耦合與啟發。譬如,徐志摩創作的《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戀愛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去罷》《灰色的人生》等,在切氏看來,這些作品中流露的人性與情感具有同義性,如同屠格涅夫的作品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一樣[4]。再如,在《中國戰爭年代的詩歌(1937—1949)》中,他不僅著墨于詩歌的形式、風格、審美,且探討了這一時期中國詩歌與俄蘇詩歌的關系;在《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國》中,他對中國詩人如何向馬雅可夫斯基學習、中國文藝界對馬雅可夫斯基的論爭以及馬雅可夫斯基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等做了全面論述。事實上,比較研究對漢學家來說不啻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只有對比較對象有深層的理解,才能產生真正的比較話語。對此,國內學者錢中文認為“所謂發言權,就是你真正研究過你所要比較的對象,本國的、外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現象,在對中外的某幾個作家、某段文學史的研究中,你確有心得,有見解”[5]305,否則這種所謂的“比較”就會陷入隔膜與膚廓。
(二) 開放意識——內外貫通
其一,切氏對西方文論與世界文藝學理論傾心研讀,關注藝術方向、文體形式、傳統與創新等問題。他指出,中國詩歌是世界文學交往中的積極參與者,它與東西方各國文學間直接或間接的交往在擴大、深化。譬如,切氏在《中國20—30年代的新詩》第一部分“五四時期的詩歌”中,不僅闡釋了五四時期詩歌的人道主義思想,而且從模仿與借用西方形象、歌頌西方偉人等視角厘清了中國新詩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并且在第八章把中國的小詩與日本的俳句、印度泰戈爾的短詩進行了比較,探討了外國作品對其的影響等。李福清認為,該著“是首次運用世界文藝學理論分析中國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詩人創作的美學思想和藝術特色的開山之作”[2]。再如,切氏在《徐志摩:在夢幻與現實中飛行》中指出,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詩集中,已經顯示出借用西方題材的痕跡。中國詩人不是簡單地“重復”外國作品的思想和形象,而是超越它們,有所創新。西方浪漫主義通過海涅、雨果、裴多菲、米茨凱維奇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國后,以某種方式發生了變形。所以,中國的浪漫主義較之西方,“批判的”比重增加了,導致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的均衡發展。西方詩人的思想和詩藝如哈代、斯溫伯恩、羅塞蒂使徐志摩的詩歌具有勇猛的反抗精神。愛情抒情詩具有“贊美愛情”與“毀滅愛情”兩個極端。其中,拜倫和雪萊詩歌的感情與靈感在徐志摩的心中鳴響并發出回聲,閱讀徐志摩的詩歌《去罷》與拜倫的鴻篇巨制長詩《唐璜》,會感到二者之間內在的血緣關系等。切氏的以上結論是足以成立的,因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是“詩體大解放”的產物,“它不是傳統文學自身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出現的一種新質文學”[6]。
其二,中國新詩作為中國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鋒,引發了海外漢學界的矚目。切氏絕非畫牢自囿,既不唯我獨尊,又能在同仁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他不僅揣摩中國學者的態度,而且以犀利的學術眼光、開闊的學術視野、求真的學術品格在國際學術呼應中敢于爭鳴。譬如,切爾卡斯基認為蘇霍魯科夫在《聞一多論》中對聞一多唯美主義的批評過于偏激;對于英國海羅魯德·艾克頓的《中國現代詩歌選本》,培恩認為該本很出色,而切爾卡斯基則覺得該本序言中某些評論不夠精準,從而使得全書黯淡。在切氏心目中,對中國新詩研究不乏佳作,法國路易·米歇爾的《墻上蘆葦·西方眼中的中國詩人》、美國許芥昱的《二十世紀中國詩選》和林明暉的《中國新詩導論》皆為珍本。切爾卡斯基稱許芥昱的選本是“西方第一本,也是比較完整的一本中國新詩集”[7]195,同時切氏對書中關于詩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理解表示不滿,因為“編者顯然把表達細膩情感的文學同粗糙簡單的‘喇叭式’文學對立起來”[7]198。
(三) 建構意識——譯研相融
切爾卡斯基青年時代輾轉學習漢語的動機,就是為了翻譯中國詩歌。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僅中國新詩選集,切爾卡斯基憑借一己之力就翻譯出版了十余種。費德林曾指出,蘇聯漢學家們將翻譯視作一種藝術,是運用祖國語言準確轉達原作的思想和藝術表現力,翻譯不是“原作的反光”,這一點與歐洲(英、法、德)翻譯原則不同。遠不是所有漢學家—翻譯家都同時掌握原文語言與俄羅斯文學語言的豐富多樣的藝術手段[8]。這一點上,切爾卡斯基的翻譯水準無人比肩。譬如,切氏在《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國》中,指明了俄譯漢的諸多問題,有曲解原意、前置詞缺省、形象毀壞、成語錯位、同音詞變異等。他在《俄羅斯文學在東方:翻譯理論與實踐》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翻譯理論問題,“為國際譯介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切爾卡斯基的中國新詩研究與其翻譯同步進行,他的每部譯集序言,都是一篇很精致的研究論文。“雖然他翻譯了許多中國現代詩歌,但是翻譯決不是他的最終目的,目的是研究中國現代詩歌”[9]。在翻譯的同時,切氏潛心學習詩學理論,以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國詩歌史的發展脈絡。他對中國20世紀20—40年代的詩歌,不是一般性介紹,而是評析各流派的代表詩人及其代表作,揭示詩人的創作道路、藝術特質與價值,非常到位和深邃。
(四) 批判意識——賞評共參
切氏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并沒停留于感性層面,而是對作品、作者加以定性、定位,核心質素數語破的。一方面,切氏對作品本身給予恰當的評判。譬如,在《太陽的話》中,他評價艾青“《北方》里雖然不見戰爭場面與士兵沖鋒,然而戰爭氛圍真實可感,戰爭漩渦中惶惶不安的人民生活被大規模地呈現出來”,“1979年之后,作品的主題、語調發生了變化,作品中出現了帶有哲學潛臺詞的冷靜觀察”,“艾青詩作貫穿著一個信念:總有一天祖國大地上的水和人民的眼淚將失去自己的苦澀”,這樣的點評精當至極[9]。切氏對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新詩作了詳盡分析,既肯定了詩歌創作的不俗成就,也闡明其“公式化”傾向與藝術上的粗糙;另一方面,他也對詩人創作主體給予凝練恰切的總結。在《艾青:太陽的使者》中,切氏認為艾青是一位“平民化”詩人,是“太陽的歌者”與“光的代言人”,“是祖國文化、東西方優秀文化的繼承人”,“是與希克梅特、聶魯達并駕齊驅的世界級大詩人”[10]。切爾卡斯基在《徐志摩:在夢幻與現實中飛行》一書中稱贊徐志摩是“中國的雪萊”,他的詩不受約束,“滿腔熱情而又充滿智慧,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感”,“徐志摩是愛情與風景抒情詩的大師”,“他是較早傳遞蘇俄消息的人之一”,“徐志摩與聞一多全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最有天才的代表人物”,同時認為“他是一位理想的浪漫主義者,但他是圣潔的,尤其不是惡魔……有‘七情六欲’,也有缺點”[4]。
(五) 整合意識——宏微并進
切爾卡斯基不僅有譯著、合著,還有研究專著。譬如,切氏抓住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戰爭年代這兩個新詩發展的重要時期,凸顯了其研究架構的宏巨性和時代性。隨著對中國新詩研究不斷深化,他逐漸走向微觀研究,即對有代表性的詩人進行全面的系統的學理研究,他選擇了兩位詩人:一位是革命詩人艾青,一位是唯美派詩人徐志摩。切爾卡斯基說:“艾青作為藝術家出現時,我寫了評論他的著作。而現在,我將把評論徐志摩的歷史性的新著推到讀者面前加以評判。”“很多年以來,我都企望寫出一部評論20世紀中國的這兩位最杰出、最耀眼的詩人的著作。從我孤陋寡聞的‘信息’土丘,我想冒昧說出下面的話:艾青的生活之路是悲慘的,而命運是美好的;徐志摩的生活之路是美好的,而命運是悲慘的。”[4]20世紀80年代歐洲科學基金會編纂大型學術書《中國文學精選指南(1900—1949)》時,特約切爾卡斯基執筆該書的《現代詩歌卷》。由此,他把艾青、徐志摩等中國詩人推向了世界。
毋庸諱言,漢學家緣于自身認知的“原初格局”、心理圖式、價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干預,在對域外文學的體認與參悟中勢必存在某種天然的局限與障壁。譬如,《論曹植的詩》盡管是切氏“第一次向蘇聯讀者和學界介紹了這位偉大的詩人及建安文學”[2],但論者的學術水平尚難恭維。該著共設四章:建安文學、民歌與曹植、曹植的詩歌遺產、詩人生平[11]。總體來看,切氏認為曹植的作品飽含仁愛精神,抒情色彩濃郁,詩中充滿作者的思想矛盾、建功豪情、憤懣憂思、渴求失望等。這樣的說法并沒有任何新的學術生長點,仍為步塵之語,或者說只是切氏把中國學界的觀點進行了一下異域移植與符號轉換。切氏還有一篇論文,將奧維德與曹植加以橫向解說,二位確有相似點:出身名門,學富五車,穿梭于皇家詩人之間;奧維德遭遇流放,憂郁而死,年壽六十;曹植被逼徙封,英年早逝;奧維德寫下《哀歌》,曹植著有《七哀》;奧維德寫有《哀愁集》等懇求皇帝奧古斯都寬恕,曹植也寫下許多類于“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這樣的詩句向曹丕表露心跡。乍看這樣的視角似別出心裁,事實上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與曹植生年相距兩個世紀,他們生活的國家制度相去甚遠,秉承的文化“元氣”迥然有異,如此低層的比較論說,學術意義似乎不大。
再如,切爾卡斯基更多地看到了中國新詩現代轉型中與西方詩歌千絲萬縷的關聯,而沒有看到或顯豁或隱秘的中國古今詩學的“糾纏”。事實上,中國新詩發展是中國古典詩歌、西方詩歌傳統與現代詩人的個性追求合力作用的結果。另外,切氏認為中國戰爭年代的詩作存有“臉譜化”傾向,這一觀點并無新意。他在對中國詩歌進行整體特征的歸納,一方面會讓讀者抓住作品的類型,另一方面也會在某種程度上簡化歷史。那么能不能在文學生態中還原詩歌的精神真相,在新詩強調政治性,弘揚“大我”,推崇“炸彈”與“旗幟”的社會功能中,進一步闡發它的歷史合理性?如在《中國50—80年代詩歌選》中,蘇聯、“文革”題材占據比例較大,此種篩汰機制是作者以作品思想性為本位的思維慣性使然,旨在使文學作品的解讀成為窺視、搜集中國信息的渠道,此種翻譯意圖使得許多優秀作品不能入圍。詩歌乃作者以一種特別的語詞樣式呈現出來的言說,倘若逡巡于詩作外部而沒有真正進入詩本體,沒有在“詩之所以為詩”的意義上觸摸詩歌的質地與靈魂,是否弱化了詩歌真正的藝術精神、美學內蘊、中國味道?
誠然,指瑕并非苛責,更不意味著否定。切爾卡斯基的漢學著作在俄羅斯曾經一度洛陽紙貴。《中國20—30年代的新詩》《中國40詩人詩選》在當時印數創下峰值,各為1萬冊,《為了尋找一顆明星》印數2.5萬冊,《蜀道難》1萬冊,這些譯本炙手可熱,短時售罄,側面反映出切氏茹苦治學付出的巨大艱辛。切氏的《中國20—30年代的新詩》與《中國戰爭年代的詩》體大思精,兩部著作計50余萬字,中國社科院的李聃曾立志翻譯,但該著一直沒有與中國讀者見面。《馬雅可夫斯基在中國》是一部典型的有關學術交流的著述[12],譯成中文也似乎遙遙無期。這既是切氏自我的遺憾,亦是中國的損失。
切氏之所以如此投入地去翻譯研究中國文學,是因為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翻譯與弘揚中國文化,既是他的追求又是他的歸宿。平心而論,任何人都無法超越自身所處的歷史現場與文化語境,對“他者”的完全理解無異于一種美好的學術期待。故此,顧彬指出:“互相之間不能理解無論如何都不是個災難,我們習慣性地缺乏理解才是真正的災難。”[3]漢學文本的開放性也正是在闡釋者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統一中得以達成。正視漢學偏見存在的正當性,以包容的姿態去“指點”漢學家的“亮點”與“盲點”,去“看見”他們的“洞見”與“不見”,去“理解”他們的“曲解”乃至“誤解”,此種良性互動恰恰是推進學術前行的動力。漢學作為中國學者的外在視點,嘔心瀝血的漢學成果實在不應遭遇放逐與遺棄的命運。切爾卡斯基“希望自己的著作不只俄國讀者能讀到,更希望中國和世界讀者都能讀到,目的是將中國新文學推向世界先進文學之林,加強中俄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2]。漢學研究梯隊青藍相接,這既是漢學領域的學術期許,也是本文的立意起點。
[1] [俄]熱洛霍夫采夫.評李明濱的《中國文學在俄蘇》、《中國文化在俄羅斯》[J].中國比較文學,1996(11).
[2] [俄]李福清.車連義及其中國現代詩歌翻譯與研究[J].泰山學院學報,2007(1).
[3] 李雪濤.論漢學研究的闡釋學意義[J].國際漢學:26輯,2014.
[4] [俄]切爾卡斯基.徐志摩:在夢幻與現實中飛行[M].宋紹香,譯.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5.
[5] 錢中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叢書總序//錢中文文集:4卷[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8.
[6] 汪介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J].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2014(8).
[7] 然理.中國新詩在國外[J].詩探索,1982(7).
[8] [俄]費德林.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在蘇聯[J].岱宗學刊,2000(4).
[9] Черкасский Л.Ай Цин.Слово солнца[С].М.Радуга,1989.
[10]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Ай-Цин-поданный Солнца:Книга о поэте[С].Москва,1993.
[11]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Поэзия Цао Чжи[М].Москва,1963.
[12] Черкасский Л. Е.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Китае[М].Москва,1976.
〔責任編輯 劉小兵〕
H35
A
1006-5261(2016)03-0001-05
2015-07-29
吉林省2015年高教學會教育科學項目(JGJX2015c112)
侯海榮(1971—),女,吉林長春人,副教授,博士;宋紹香(1936—),男,山東泰安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