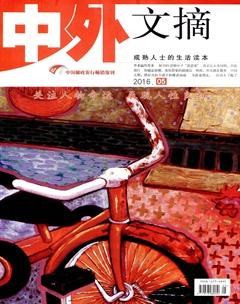操著趙本山口音的康熙
陳事美
康熙不說北京話
清軍入關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時康熙的周圍,也就是宮廷內都是說滿語的。這些人全部是從遼寧遷移過來的,雖然滿語不完全等同于東北話,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話在此時還沒有真正形成,或是還沒有真正產生影響力。可以想象,康熙的東北口音絕對比張學良還濃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遼寧省新賓縣,這個地方屬于撫順,距離趙本山的老家鐵嶺直線距離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與趙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會在一半以上。從康熙批閱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專治瘧疾……連吃兩服,可以出根”。這其中,“可以出根”實為“可以除根”,而東北話講“除”就是第二聲的“出”。還有,比如“解京又費一凡事,不如存庫……”,這其中“費一凡事”,實為“費一番事”,用東北話講“番”正是第二聲的“凡”。
后來,隨著滿漢語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漢臣的大幅增加,此時在民間形成的北京話才慢慢成為宮廷中的主要語言。但康熙年事已高,畢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學北京話了。
曾國藩讓人很郁悶
作為晚清重臣,曾國藩對大清國的貢獻可謂杠杠的。但老曾的湖南口音過于濃重,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
李鴻章是曾國藩非常賞識的弟子,有時二人也無話不談,或是一同說笑。談話間,老曾說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鴻章大驚,“卵昧”?這不是下流的語言嗎?老師怎么突然冒出這么一句。李鴻章不明白,大膽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來,“冒得卵味”是湘鄉話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是“沒意思”。
洪秀全起事后,曾國藩大膽上書咸豐皇帝,對年輕的咸豐帝不是批評就是抨擊。為了達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僅寫奏折,還要在上朝時說給咸豐聽。這是誠心不給皇帝面子嘛。
當著滿朝文武的面,曾國藩也不管皇帝愛聽不愛聽,對著咸豐就是一頓猛批。老曾太激動,語速有點快,平時聽慣北京話的咸豐很不習慣,要不斷叫停,因為根本聽不懂這個湖南蠻子在說什么。滿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國藩沒辦法,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給咸豐聽。結果,咸豐聽懂了,也怒了,大聲斥責曾國藩狂悖,非要軍機處給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攔著,老曾腦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業很吃虧
民間有句話,說“千不怕萬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清末有兩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與梁啟超,兩人在事業發展上也吃過普通話不好的虧。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都是珠三角地區,兩地直線距離只有七八十公里。兩人既是老鄉,又是師徒,還是政治同盟,平時兩人交流,用粵語酣暢淋漓。但二人走南闖北,傳播先進思想,只能自學普通話,他們的“廣味普通話”也是一大鮮明特色。
最麻煩的是見皇帝。光緒單獨接見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長時間,唯獨接見康有為,不到十分鐘就結束了。到底談了什么,別人無從知道,但光緒后來還接見了梁啟超,完全可以做個參照。
梁啟超見到光緒,也是推銷自己的變法,但無奈光緒聽著很費勁,只因梁啟超說話發音嚴重不準,如將“考”說成“好”,將“高”說成“古”。有時梁啟超講一句,光緒還要問一句,甚至梁啟超還要用手比畫,或者還要用翻譯。這情景,光緒的興致早沒了。但凡被皇帝接見后,按說都要賞個四品官,而梁啟超只得到個六品頂戴。
可見,變法也要學好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