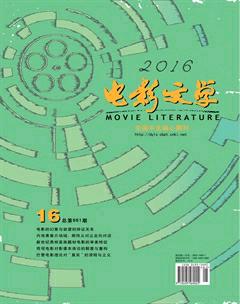《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倫理
池麗霞
[摘要]《消失的愛人》是美國著名導演大衛·芬奇的作品,影片在上映之后引發了人們關于婚姻等問題的持久熱議。“敘事倫理”則是西方文藝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批評學科,意在探究作品中的倫理效果是如何在敘事中實現的。《消失的愛人》關注著人的生存法則、道德行為與倫理訴求,其中存在著隱形的道德尺度,是應該置于敘事倫理的層面來進行討論的。文章即以此入手,從社會倫理、家庭倫理、兩性倫理三方面,分析《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倫理。
[關鍵詞]《消失的愛人》;大衛·芬奇;敘事倫理
《消失的愛人》(Gone Girl,2014)是美國著名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根據女作家吉莉安·弗琳的同名懸疑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電影以女作家艾米失蹤,艾米丈夫逐漸被各種證據指為殺人兇手開始,隨著真相層層揭開,兩人真實而殘酷的關系也展現在觀眾面前,令人感到不寒而栗。電影也在上映之后引發了人們關于婚姻等問題的持久熱議。芬奇利用各類視聽元素將小說中的暗黑、壓抑、驚悚氣質進行了強化,在影像設計上芬奇則延續了自己在《紙牌屋》(House of Cards)等作品中表現出來的一貫冷靜而簡潔的風格,以保證電影無論是從結構到細節,抑或是從場景到段落剪輯,都呈現出一種深入骨髓的寒意。而電影作為“有意味的形式”藝術的一種,上述元素皆是服務于敘事的。“敘事倫理”(narrative ethic)是西方文藝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批評學科,它最早由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即探究作品中的倫理效果是如何在敘事中實現的。《消失的愛人》關注著人的生存法則、道德行為與倫理訴求,其中存在著隱形的道德尺度,是應該置于敘事倫理的層面來進行討論的。
一、《消失的愛人》中的社會倫理
英國學者米切爾曾經指出:“社會一詞是社會學詞匯中最不明確和最普通的名詞之一。它可以從表示沒有文字的民族到表示現代工業民族國家,或者從一般的泛指人類到表示較小的有組織的民族群體。”可以說,社會一詞的外延是十分廣大的,任何人與他人在進行互動時,某種具有穩定關系的人的集合體都可以被認為是“社會”。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便是作為個體的“人”與群體中其他個體的關系,以及個體本身的自我認知、自我價值判斷,這些都可以被視為社會倫理問題。《消失的愛人》之所以引起熱議絕不僅僅是因其對婚戀問題進行了探討。單純就對婚姻的復雜性和絕望性的表現這一點來說,《消失的愛人》實際上并不比薩姆·門德斯的《美國麗人》(American Beauty,1999)和《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2008)更為優秀;《消失的愛人》也不應該僅僅被視作一部懸疑電影,就對懸疑的設置而言,芬奇早已在《十二宮》(Zodiac,2007)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消失的愛人》選擇在敘事進行不到一半時就拋出了“罪案”的“真相”,從而過早地結束了懸念。而電影基于暢銷小說改編這一點也注定了電影無法靠懸疑敘事取勝。事實上,《消失的愛人》與芬奇的另一部佳作《七宗罪》(Se7en,1995)更為接近,導演只是借用了罪案的外殼,來探索人性與社會的深層問題。
(一)艾米的身份迷失
身份迷失問題是當代人的困擾之一,同時也是《消失的愛人》中悲劇的根源之一。之所以筆者認為《消失的愛人》所探討的并非單純的婚姻問題,正是因為整個故事實際上都與女主人公艾米的心理問題有關。作為一個擁有名校心理學學位的女性,她深諳如何利用話語控制他人,為他人設下陷阱,給他人制造心理刻板印象,從而扮演各類能使自己獲益的角色,而艾米最擅長扮演的便是弱者。由于艾米的心靈早已扭曲,即使她沒有踏入婚姻的殿堂,電影中的驚悚故事同樣可以發生在艾米與他人身上。而事實上,艾米也確實在結婚前就通過扮演被強暴的女性而成功使自己的前男友背負了多年的性侵罪名。而艾米本人之所以熱衷于這種扮演行為,實際上還是在于自己身份的迷失。艾米及自己的父母都是知名人物,她是兒童讀物《了不起的艾米》的原型,必須在公眾面前展現自己知書達理、溫柔樂觀等優點,成為一個人見人愛的、大眾情人式的“美國甜心”。這其實沒有導致艾米在自我認同上出現偏差,她深知他人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艾米,自己也能在本性與扮演之間轉換自如。陷入“迷失”的實際上不是艾米本人,而是注視艾米的人們。如堅信艾米是忠貞賢妻,認為尼克是個負心混蛋的鄰居諾伊爾,便是蕓蕓庸眾的一個縮影。
(二)媒介與受眾的眾聲喧嘩
當代媒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大眾除了利用媒介獲取信息之外,更利用媒介獲取娛樂。而意味著話語權的媒介則往往由中產精英所掌握,大眾很容易為媒介所引導,進入一場又一場話語狂歡中,如尼克在“負心漢”形象被曝光之后迅速陷入媒介解析的泥淖,大批媒體日夜守候在其家門外,電視臺則為了迎合觀眾的獵奇心理提高收視率,不斷邀請專家分析尼克殺妻的可能性等,此時受眾所呼喚的其實早已不是真相。艾米正是深知媒介話語導向的作用才扮演成遭受家暴的懷孕妻子,而尼克在意識到這一點后也通過在電視訪談節目上扮演沉痛悔過的丈夫來挽回形象奮起反擊。受眾對于尼克的印象迅速被媒介固定又迅速為媒介扭轉,這無疑是電影最大的諷刺。而電影有意設置了一個與艾米一起看電視的女孩,出身底層的女孩一語戳破艾米在媒介上的偽裝,甚至通過打劫艾米的錢將算無遺策的艾米逼入絕境,生存的壓力使這一女孩無暇加入狂熱群眾的圍觀中,反而更能看清真相,可以說這一形象是整部電影中最為清醒的角色。
二、《消失的愛人》中的家庭倫理
家庭倫理也是影視作品中經常探討的內容。《消失的愛人》中的家庭倫理主要有兩類:一是親子倫理,二是手足倫理,這二者都是文學與戲劇藝術中進行家族敘事時屢屢涉及的倫理類型,對它們的處理也可以體現導演的價值取向與藝術匠心。
(一)親子倫理
電影中艾米與尼克都有各自的父母,然而他們在處理親子關系時幾乎都是失敗的。“理想之母”的角色在《消失的愛人》中是缺席的。尼克的母親在電影開始時就已經因病去世了,從后面尼克在律師的訓練下上電視節目的情節可以看出,母親已經成為尼克用來標榜自己“孝順”的一個符號。而實際上,尼克母親可以說是尼克夫婦關系失和的導火線之一。正是打著照顧生病母親的借口,尼克說服已經習慣了紐約大都會生活的艾米與自己搬到鄉下小鎮來開始艾米難以適應的生活。尼克的父親則因為年邁癡呆而出現在警察局,與自己的兒子只有一墻之隔,隨后尼克將父親送回養老院。在尼克為數不多的與父親接觸的畫面中,觀眾看到的是尼克的毫無耐心。而尼克一年僅僅探望父親一次也成為他后來遭到口誅筆伐的弱點之一。
而艾米的父母則在電影中出現多次,他們的形象承擔了塑造艾米陰暗家庭氛圍和性格的任務。艾米擁有遠勝于尼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擁有風靡全美的漫畫《了不起的艾米》的版權。對于艾米,艾米父母從來沒有給予過她無條件的愛,并且對艾米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如要艾米接受記者采訪等。艾米僅僅是“了不起的艾米”的原型,是在處處圓滿的“了不起的艾米”襯托之下的殘次品(如不會拉大提琴,不會打排球等)。艾米很清楚父母對自己的真實態度,也已經習慣了父母在媒體面前表演式的生活方式。這種親子倫理直接影響了艾米的兩性關系:一方面她迫切地期待丈夫能夠給予自己無條件的愛,愛自己的缺點與陰暗面,一旦發現自己得不到這樣的愛時,她便會懲罰對方;另一方面,從小形成的表演人格又使艾米有意無意地在與尼克初識時看透對方的心思而將自己扮演為對方想要的“Cool Girl”。這種表演實際上正是艾米父母長期將艾米打扮成“美國甜心”后的一種自然延續。
(二)手足倫理
電影中的手足倫理則是由尼克兄妹來體現的。尼克與雙胞胎妹妹瑪格之間的感情也是尼克在事發之后遭到攻訐的弱點之一,尼克甚至在機場聽到陌生人嘲笑他們為兄妹亂倫。在小說中,弗琳用大量文字介紹了“我”與瑪格的關系,“我”對瑪格的依戀之情。尼克與瑪格并沒有肉體上的亂倫關系,這也是尼克為何在機場會十分憤怒的原因,但是在精神上,兩人又對彼此確實有著畸形的依賴。在電影中,芬奇用不少細節將弗琳的文字具象化了。如電影一開始便是尼克與瑪格一起在酒吧無所顧忌地表達對艾米的不滿。瑪格的酒吧是在艾米出資幫助下開起的,瑪格卻對艾米沒有任何感恩之情,相反總是以自私、低俗的腔調詆毀艾米。又如,瑪格自己沒有戀人與朋友,在發現尼克確實出軌后的惱羞成怒,以及在電影結尾時兩人擁有一段曖昧不清的對白,尼克決定留在心如蛇蝎的艾米身邊,瑪格為此崩潰痛哭,尼克懇求瑪格陪著他,瑪格則流著淚說他們早在沒出世前便彼此陪伴了。對于早已在《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1999)中嘗試過精神分裂敘事的芬奇來說,瑪格除了是原著中的角色以外,實際上還承擔著尼克的另一重人格。電影中已經交代了兩人因為是孿生兄妹而有心靈感應,當尼克決定繼續自己窘迫的處境后,瑪格的崩潰實際上也是尼克內心隱憂的反映。
三、《消失的愛人》中的兩性倫理
兩性倫理則是整部電影中負載著戲劇張力的倫理類型,也是艾米的主要倫理訴求。電影中與艾米發生兩性關系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其丈夫尼克,另一個則是她的高中男友德西。
艾米與尼克的關系經歷了初見時彼此對形象的偽裝以及婚后真面目的暴露,直至彼此傷害,尼克出軌,艾米偽造家暴與他殺,最終兩人又選擇繼續在扮演中繼續生活,甚至還要生兒育女這一過程。婚姻在電影中呈現為一種壓抑的態勢,兩人都極為自私且自憐,在是施害者的同時又是受害者。艾米最終沒有因為殺人而被繩之以法,尼克也沒有揭露艾米,整個婚姻成為一個牢籠鎖住兩人,當兩人面帶微笑出現在眾人面前時,電影傳遞出來的婚姻的絕望感,實際上要遠比電影開頭時更為強烈。在影片開頭,兩人正在談論離婚,雖然記恨彼此,但此時這段婚姻仍然有結束的可能。然而在結尾時,離婚的可能已經不存在,尼克已經明明知道身邊人具有蛇蝎心腸卻無法離開,還需要在未來強顏歡笑,在恐懼與虛偽中度過余生。兩個人已經比電影開始時更憎恨彼此,卻又要扮演得更愛對方,婚姻成為“無期徒刑”。而電影在結尾時的漫長也給予了觀眾一個沉淀思緒的時間,讓觀眾感受到片中人的身心俱疲。
德西的存在并不僅僅是出于情節的需要,使艾米在被搶劫之后能有一個容身之所和替罪羊,最終順利回到尼克身邊。德西之所以被艾米殺死,除了他知道艾米還活著的真相以外,還與德西比艾米更為強烈的控制欲有關。電影中,芬奇多次表現了德西對艾米無處不在的控制,如不由分說地拿走艾米手中的平板電腦,在湖邊小屋的所有出口都裝上攝像頭,在性上采取主動、逼迫的姿態等,這些對于德西形象的完善都顯然比僅僅把德西塑造成一個癡情的、輕信的犧牲品角色更容易激發觀眾的思考,從而達到敘事的倫理效果。
大衛·芬奇的電影往往能夠在保證商業回報的同時,又不忘在電影中注入人文關懷精神。《消失的愛人》亦不例外。從對《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倫理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電影作為敘事藝術的一種,其敘事文本是可以用敘事倫理理論進行解讀的,而敘事倫理本身也對當今社會有著現實意義。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高等學校英語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基于語料庫的英語專業寫作名詞化研究”(項目編號:2015YYJG067);防災科技學院2015年院級教育研究與教學改革項目(項目編號:JY2015B14)。
[參考文獻]
[1]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J].外國文學研究,2010(01).
[2] 胡榮.社會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焦國成.論倫理——倫理概念與倫理學[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1).
[4] 李桂梅.中西家庭倫理比較論綱[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