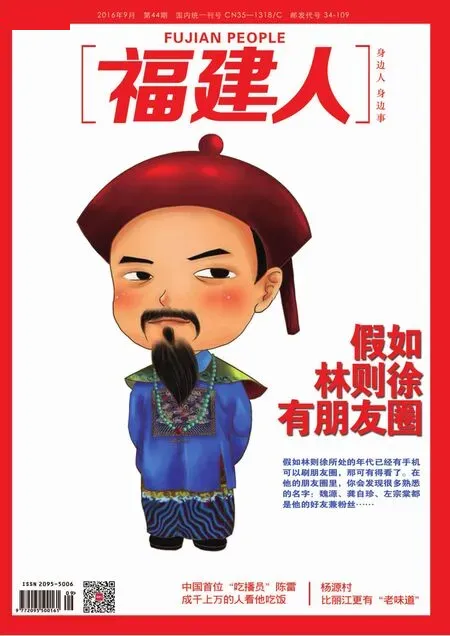陳衍這個詩人會做菜
陳衍這個詩人會做菜
你可以想象,當年陳衍和一幫文人雅士,泡一些茶,聽一會兒古曲,然后親自下廚,烹一桌美味。返璞歸真,淡淡的,卻能勾住你的嘴。
2016年6月13日,陳衍的玄孫女陳逸剛一下班,便直奔菜市場買豬腦。這天晚上,閩菜大師劉會健要按照她高祖寫的菜譜,復原一道100多年前的福州菜——“會豬腦”。
烹制的所有步驟,都按照陳衍的菜譜進行。劉會健本想加入高湯和幾種調料,他認為:“只用醬油調味的辦法在今天看來是難以想象,現代人吃慣了調料的味。”但陳逸的堅持讓他打消了這個念頭。陳逸說:“我們的復原,是原原本本地還原百年前的味道!”
20分鐘后豬腦出鍋,色相略差,卻極清香。“香!是豬腦的本味!”只幾分鐘,陳逸和幾個朋友便一掃而光。劉會健說,陳衍所寫的烹飪方法,吃的都是食材的本味,“這么做是對食材的尊重”。

陳衍(1856—1937),福州人,學者、詩人、詩論家,曾在南北各大學講授,編修《福建通志》,“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之一,撰寫了中國第一部烹飪教科書。
中國第一部烹飪教科書,全是福州味
在很多人看來,文人往往都是不沾人間煙火氣的,陳衍卻不然。他是一名學者,曾在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南北各大學府任教,他也是清末民初“同光體”詩派的締造者與推廣者。他平生素愛美食,常以“君子不必遠庖廚”自況,每與摯友詩酒唱和之時,便下廚執膳,以佳肴奉客。
常出現在他筵席上的摯友,有梁啟超、章炳麟、嚴復、林紓、陳寶琛、王國維、錢基博、鄭孝胥等。這些文人雅士,與陳衍一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卻無一不驚嘆于他的廚藝。
北洋大臣托忒克·端方任湖北巡撫時,就熟識當時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的陳衍,常要陳衍請客。倆人一面吃著,一面互評,某道菜比北京最有名的福全館還好,某道菜則不如。后來陳衍在福州成立詩社,每年人日(正月初七)在家中設宴招飲眾弟子,時任福建省主席陳儀還盛贊陳家菜較北京譚家菜有過之而無不及。
陳衍不僅會做菜,還會寫菜譜。
如果你是生在民國的女子,上著女子中學或者女子師范學校,那么你一定會學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烹飪教科書》。這是唯一一本經過民國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烹飪教學書,從1915年到1948年再版過4次,出了7個版本3萬余冊,后改名《烹飪法》,足見其影響之廣。
但很少人知道,這本風行全國的書,是完全脫胎于福州菜。而該書的作者“蕭閑叟”,便是陳衍。據陳逸介紹,陳衍妻子自號蕭閑堂主人,他用“蕭閑叟”署名,系懷念亡妻之舉。
陳衍號石遺,這本《烹飪教科書》原名就叫《石遺室食譜》,經教育部審定后才改了名字。書中內容分前后兩編:“前編”為總論,“后編”按葷、素、雜分類,共載70道菜式。
在“緒言”中,陳衍引經據典,列舉了古代婦女“居家之職”“主中饋”的典范,提出“烹飪之事,宜精而有法矣。精而有法,用錢省而可食,反是,用錢雖多無益”。
他還列舉了中國南北不同的飲食習俗,如“北方多面食,南方多食米飯,而一日兩餐則同。江蘇、浙江、福建各省,早晨必加一粥,所需腌菜一二味而已。廣東、湖南北各省,則只用兩餐”。
“后編”由“各論”組成,即70道菜譜。饒有意味的是,這些菜譜,均為家常飯菜,各菜譜字里行間也往往陳述南北飲食乃至食品銷售的差異。究其烹飪之法,帶有濃烈的福州菜特征。
在這本書中,也隨處可見福州方言。商務印書館老人蔣維喬曾回憶當時高夢旦與編輯的“釜鼎之爭”:編輯認為陳衍用“鼎”字太古,不普遍,不可用。而高夢旦堅持“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應留。二人爭得聲色俱厲。高夢旦是陳衍的福州同鄉,對他的表述自然心領神會。
《烹飪教科書》雖比袁枚的《隨園食單》晚,卻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部私家菜譜被教育部門審定的教育用書。這本書是在沒有可以借鑒參考的前提下編纂的,陳衍在編輯大意中寫道:“雖不敢自詡為空前杰構,而經營慘淡,煞費苦心,閱者鑒之。”
這本菜譜,陳逸家里一直藏著,小時候她并沒有把它當回事。一直到前兩年,翻看這本書,她突然有了續寫下去的沖動。但光看菜譜看不出幾分門道,這事就停滯下來了。她想找個懂行的廚師,幫助她來實現這個愿望。
后來,她找到了福建省烹飪協會理事劉會健,還開了個“尋味百年”的微信公眾號,嘗試著將100多年前老祖宗吃的美食重新復原。
閩菜大事劉會健按照陳衍菜譜復原的福州菜

炒面筋

炸排骨

拌芹菜

炒豬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