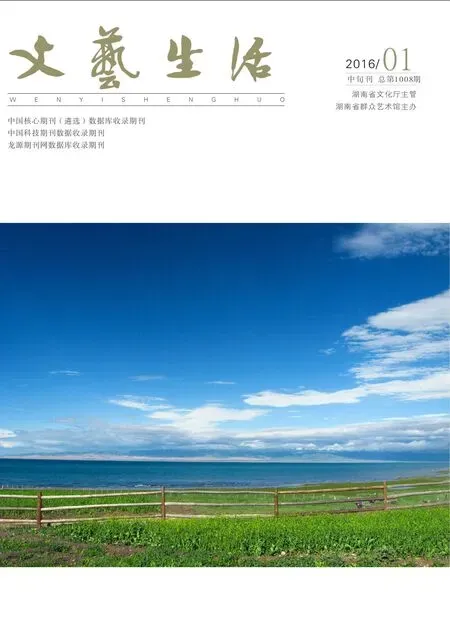淺析周思聰人物畫風格的轉變
馬甜甜
(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山東濟南250014)
淺析周思聰人物畫風格的轉變
馬甜甜
(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山東濟南250014)
20世紀初在中國畫壇中興起了一次較大的美術思潮,創新和變化成為中國畫發展的主要方向。自“五四運動”以后,以徐悲鴻、蔣兆和為代表的將西畫藝術中的造型透視方法和寫實主義引進中國。然而,“我們必須舍棄舊的理論體系和對藝術的僵化認識,重點強調繪畫觀念問題。”①
周思聰;人物畫;轉折;發展
一、師承徐悲鴻、蔣兆和的周思聰
周思聰先生是我國20世紀美術史上杰出的女畫家,一生留下了不少極具影響力的佳作。在她的藝術生涯中,師承徐悲鴻、蔣兆和二人。后又因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氛圍中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確立了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服務的根本方向的“二為”方針,使得在當時的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大多數是從人們具體的生活出發,這也使周思聰初期的作品《周總理和紡織女工》、《朵朵紅花送模范》都是歌頌領袖和勞動人民新生活的作品,她自己也對自己這樣評價:“1963年畢業至文革前,作品有生活氣息,但膚淺;思路、技法單一”。
二、周思聰早期繪畫風格的形成
周思聰早期的代表作之中,《人民和總理》是最富寫實人物畫典型的一幅作品。畫中災區人民將周總理緊緊圍繞,老少婦孺,動態各異。但災區人物都是面對總理而站,眼神中流露出的痛苦、信任和希望的復雜神情讓人凝思。在畫面近景中帳篷等景象以及遠處的枯樹、飛機,更是將災后的氣氛渲染的淋漓盡致。水墨寫實的手法,有極強的敘事說情之感,筆墨濃淡變化層次豐富但仍圍繞結構應運而生,線條簡潔直率。表達出對總理的無限懷念和對人民群眾艱苦命運的深切同情,而且又將自我對“文革”專制主義的不滿、批判表現得淋漓致盡,也把自身正直善良的本性回歸正點。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對于當時政治環境的變化,周思聰的作品表現的恰到好處,但卻沒有技法的突破,更加沒有思想上的革新,只是一味地傳統單一的寫實主義。
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隔離、批斗或者勞教等等各種現象在全國實屬普遍,畫家也必然免不了遭遇這樣或那樣諸如此類的活動,因此周思聰的繪畫活動也隨之基本中斷。到了1969年中國文聯、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撤銷更是讓全國上下所有的美術活動處于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1972年左右,國務院文化組主辦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會》的開展,全國的美術創作逐漸恢復。1976年10月,隨著“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思想也得到進一步解放,與此同時,藝術本位論也開始得到關注,繪畫形式語言更加注重藝術性。
三、求同存異,獨辟蹊徑:周思聰繪畫藝術的轉型
當中國打開大門迎春風之時,西方現代、后現代思潮的涌入,加之盧沉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先進水墨構成思想,周思聰的創作思想發生著巨大變化,《礦工圖》組畫便是周思聰實現“寫意精神”和個人思想的轉換,畫風受到德國表現主義柯勒惠支和赤松俊子的影響,對立體主義畢加索和日本丸木位里夫婦《原爆圖》的借鑒,大膽開始變形、夸張,用錯綜復雜的幻影描繪場景。《礦工圖》中運用的分割畫面、形象重疊的表現時間與空間的手法是對西方現代主義形式語言最好的借鑒,更是對中國沉重歷史悲劇主題的表達。
從1980到1983年,陸續完成了《礦工圖》之五《同胞、漢奸和狗》(與盧沉合作);之六《遺孤》;之二《王道樂土》;之三《人間地獄》。為表現壓抑,他們改變了傳統的構圖規則,在一個畫面拼接、組合了不同的時空;濃重的黑色調,扭曲的形體,悲苦呆滯的表情……細細品讀,感到由腳底到頭發所散發的那種陰冷,哀傷,擠壓與震撼。這個階段的作品,周思聰的作品內涵豐富了,形式感染力強了,現代氣息也更加濃郁了。
四、周思聰獨立的藝術風格
《礦工圖》是繼《流民圖》之后,用水墨表達中國歷史、人民災難的最偉大的作品。它表現了中國水墨畫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過渡轉折的時代,是一代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融民族傳統繪畫與西方現代繪畫語言于一爐的嘗試。②
1984年,是周思聰創作的高峰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藝術思想較為活躍的時期。她認為:“藝術是人道主義的,它是人性、人的感情結晶。”“藝術強調個性,藝術境界是審美觀的自我體現,自我完成,強烈的主觀色彩,個性的,不可能是一個模式。”③
郎紹君也在《現代中國畫論》中指出:“從強烈的社會性主題轉向了平凡的生活性主題,對莊嚴崇高的關注轉向對平樸淡雋的傾心,形式風格的樸茂渾厚也過渡到為細膩俊逸。精神方面,由直感人生深入到咀嚼人生。”在其繪畫風格的轉折中,這一時期的周思聰大膽突破原有的、嚴謹的寫實之風,吸收借鑒西方文化中變形夸張、分割、重疊、并置等多種現代化的表現手法和開放的藝術觀念,敢于打破時空的限制,輕線條、重變形、重整體,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變形風格。
隨著“八五新潮”,西方現代主義的各種風格流派更為純粹地在中國文化當中游蕩。周思聰的正直、善良隱匿深處,生活的沉重使得周思聰渴望一種精神上的解脫和自由,久之,她的畫面開始關注自然,格調也變得清幽和純凈。
到了后期,周思聰的身體也開始飽受病痛的折磨,作畫也愈發少了很多,但她堅持畫畫,彝女、山水小品和荷花都成為她的精神寄托。不得不說的是,1992年創作的彝女系列和荷花系列,是成為她的寫照,她的完滿,最美麗的夕陽。彝女系列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高原暮歸圖》,可以代表前期的風格:墨色沉重,背景多空曠、陰郁,人物面相勞苦,變形有限,寫實的成分較多。《秋林負薪圖》則代表后期的風格:背景淡化,近景的樹、人、草叢、落葉安排得疏朗有度;人物變形明顯,粗壯的脖頸,厚實的肩背,肥碩的臀胯,內盤的小腿和足尖相向的腳,一個個敦實厚重可愛;有種童稚趣味。每一處細節也都不曾敷衍或者草率。《秋林負薪圖》是整個彝女系列中最大,最成熟和最有代表性的,表現的是五個打柴、背柴的彝族婦女。比之前早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改沉重憂郁之風,更為蕭疏淡然,具有更濃的抒情色彩。朱乃正在《盧沉周思聰文集》中評價說:“他們的目光、他們踏上山路上的足跡都是詩,質樸物化的詩”。
隨著病情的加重,周思聰逐漸開始轉向了荷花的創作。愛蓮之心由來已久,更也許是蓮花的性格如她一般,沒有牡丹的雍容,沒有野花的活潑,恬靜淡然,順其自然。周思聰畫荷花也是生命和心境的需要,同時也享受著水痕和墨跡之間的變化。她的荷花設色淡雅,煙雨氤氳,一兩朵荷花、殘枝敗葉,若隱若現。
周思聰的繪畫風格演變,其中的大小轉折點不勝枚舉。融西中入的社會文化環境,工業化進程的迅猛發展,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等等都是影響其一生的重要因素。由早期作品的輕松、甜美、熱情到中期的凝重、苦澀、壓抑以致晚期的單純、淡泊和清雅。閱歷的逐漸豐富,體驗的逐漸深刻,促使了她的藝術語言不斷的錘煉,從稚嫩到成熟,從重描繪到重感受,從傳統的單一寫實到多樣的變現形式的交融,從隱沒個性到自由徜徉。就像她說過的,“畫畫的事,通常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相信自己感悟到的一切,所以時常是走一步退兩步,但是沒有停止過。”
周思聰的變革是從她自己開始的,她的悲劇美,她的人道主義,她的女性意識,都是最勇敢的革新,她身在其中,她是國畫界的中堅,她是中國水墨畫藝術走向現代的先行者,更是畫界的驕傲。
注釋:
①高明璐.中國前衛藝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468-469.
②邵大箴.回憶與懷念——對盧沉、周思聰創新探索的一些認識[J].美術研究,2010(02):44-46.
③馬文蔚.周思聰:藝術個性的覺醒[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04):47.
[1]水中天,郎紹君.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
[2]秋霖.論現代中國人物畫創作的多元發展格局[J].寧夏大學學報,2003(02).
[3]劉墨.中國美學與中國畫論[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4]馬文蔚.周思聰:藝術個性的覺悟[M].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
J212
A
1005-5312(2016)02-017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