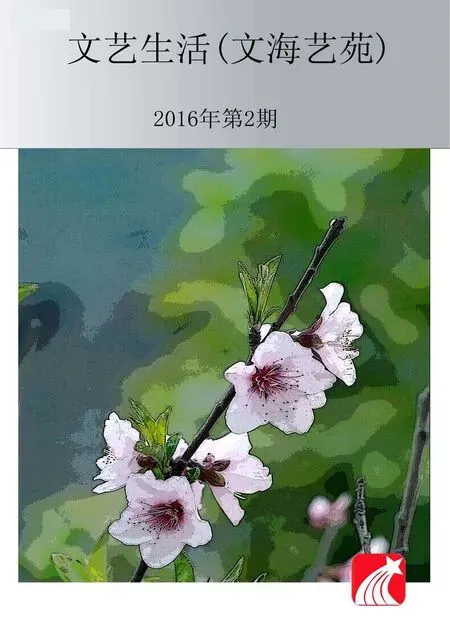《史記·張丞相列傳》、《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校讀札記
韓君瑋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史記·張丞相列傳》、《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校讀札記
韓君瑋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本文通過對《史記》、《漢書》中的兩篇列傳進行校讀,比對差異和錯訛,借鑒其他輔助材料,判定是非,以做這篇校讀札記。
史記;漢書;校勘
《史記》、《漢書》作為中國甚為有名的兩部正史,其間更是在體例、年代、敘事等多方面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而《漢書》一直被認為是沿襲、參考了《史記》大量內容所作,其中或摘抄,或創新,然年代久遠,世世相傳,其中必有一些訛誤和值得討論的地方。現就《史記·張丞相列傳》、《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兩相比對,加以討論,提出自己粗淺的觀點。其中原文皆引自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為1959年9月第一版第2版、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漢書》為1962年6月第1版、2002年11月北京第11次印刷。
一、為柱下御史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領主郡國上計者。(冊7頁/2094/行2)
《史記·張丞相列傳》: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領主郡國上計者。(冊8/頁2676/行4~5)
按:兩本所差僅在于“柱下史”“柱下御史”。《漢語大詞典》釋柱下史義項有三:(1)周 秦官名,即漢以后的御史。因其常侍立殿柱之下,故名。《史記·張丞相列傳》:“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司馬貞索隱:“周 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2)為御史的代稱。唐 李白《贈宣城趙太守悅》詩:“公爲柱下史,脫繡歸田園。”(3)指老子。參見“柱下”。(4)星名。《晉書·天文志上》:“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此之象也。”此處《漢書》言說“御史”,恐其受漢代官制稱名影響而將同一事物的兩種稱呼混同,“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張蒼自秦時,即應為秦時官名,至少秦時稱“柱下史”,此其一;義項2中稱“為御史之代稱”,兩者應為同義詞,豈有同時出現于一句之道理?縱使同時并舉,秦代是亦僅指“柱下史”這一官職,此其二。后文稱“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前邊的“上柱御史”與“御史大夫”迥然不同,不應相混同,此其三。故而,應從《史記》較為合理,《漢書》所言雖有解釋說明之意,亦有畫蛇添足之嫌。
二、黥布反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冊7/頁2094/行2~3)
《史記·張丞相列傳》: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冊8/頁2676/行5~6)
按:《漢書》與《史記》僅差“亡”一字,《<史記>箋注》:“黥布反亡,事在高祖十一年(前196)七月。《史記索隱》云: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史記·黥布列傳》后又言“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余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可知黥布造反敗亡之后,復立劉長為淮南王,若從《漢書》省去“亡”字似乎太過簡略,未能言明事實,亦有可能造成黥布一反即立劉長的誤解。
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冊7/頁2094/行13)
《史記·張丞相列傳》: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冊8/頁2676/行15)
按:《史記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梁玉繩曰:“當作‘三年’。《史記箋證》認為:梁說是,下述諸事應在漢三年(前204)秋,《秦楚之際月表》書于“四年三月”,同誤。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史記·留侯世家》:“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從很多文獻中可知,楚圍漢王于滎陽是于漢三年秋發生的,因《史記》其他自有篇章皆支持此說法,不可能自相矛盾,故《張丞相列傳》中大約是訛誤,《漢書》改之,從《漢書》說。
四、上以留侯策止;陛下欲廢太子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上以留侯策止······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冊7頁2095行7~8)
《史記·張丞相列傳》:上以留侯策即止······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冊8頁2677行9~10)
按:此兩例異曲同工。《漢書》省去2字,是在感情色彩程度上的偏好,《史記》較之《漢書》更易代入自身的喜惡,“上以留侯策即止”似過分夸大了留侯策的作用;“陛下雖欲廢太子”卻側面體現出周昌與劉邦關系之親厚,與前文相應和,僅一“雖”字,便將周昌剛直不阿、敢違圣諭的情態描摹出來,《漢書》客觀敘事雖可取,但如第二例,失去“雖”字則興味索然,不夠生動,更難幫助讀者詮釋周昌為人。
五、即罷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于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冊7頁2095行8)
《史記·張丞相列傳》: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于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冊8頁2677行10)
按:兩句僅所差一字,一句讀,意思卻千差萬別。《漢書》所表之意為劉邦聽了周昌的不滿后隨即將改立太子的事作罷,后呂后聞于東廂拜謝周昌,后邊用句號,正是此意;《史記》之意乃為劉邦聽了周昌的話,僅是客氣地欣然笑之而未表態。“既罷”,廢太子事因多種原因(如商山四皓)已作罷,但后用逗號,似又與后文連接很不緊密,文意恐有不同。
筆者更為支持《漢書》,其一,文中前極言劉邦與周昌關系之親厚,后又言呂后對周昌的感激之深,若不是周昌在諫止廢太子事中起了關鍵作用,呂后安能在誅殺如意受阻之時尤保全周昌?其二,此篇系為周昌作傳,豈會不著重突出其才能和功用,于文章主旨不和?其三,聯系后文呂后在東箱偷聽,一見周昌就拜謝,與勸阻高祖必是連貫發生的,若用“既罷”,不合邏輯。
六、東擊項羽
《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冊7頁2098行2)
《史記·張丞相列傳》: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冊8頁2689行5)
按:兩者之間差異在于項羽項籍。《史記》全書并無“東擊項羽”四字,但“東擊項籍”則是在六篇中都與“高祖立為漢王”“初為漢王”有篇章上的前后關聯。
而《漢書》中涉及此四字的除該篇外,僅有《樊酈滕灌傅靳周傳》“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而涉及“東擊項籍”的則有《韓彭英盧吳傳》、《荊燕吳傳》、《萬石衛直周張傳》三篇,而其中《韓彭英盧吳傳》:“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群臣莫敢望。”《荊燕吳傳》“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皆以不同方式提到是劉邦初立漢王時發生的事,故而根據其他篇章,似乎《史記》更為合理。
[1]漢司馬遷.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漢班固.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3.
[3]陳垣.校勘學釋例[M].北京:中華書局,2005.
[4]謝秉洪.漢書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5]曾小霞.近30年《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綜述[J].陜西教育學院學報,2009.
K206
A
1005-5312(2016)05-0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