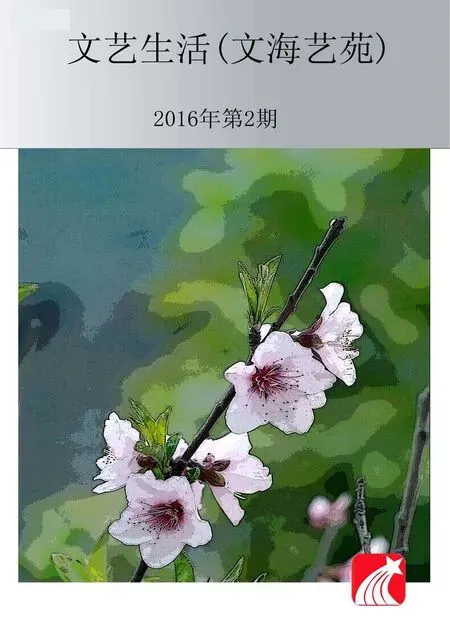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論看《春盡江南》
王凌霜
(青島大學文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論看《春盡江南》
王凌霜
(青島大學文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格非的《春盡江南》通過主人公們的精神衍變與歷史現實,展現了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本文試圖借助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人格理論,以小說中的人物群像為對象,分析探討主人公們的心路歷程和變化原因,并試圖探尋作者在創作背后,所進行的關于人的生存等問題的思考。
弗洛伊德;人格理論;《春盡江南》
一、人格分析理論的闡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認為,人的心理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意識、潛意識和無意識。當人的某些本能欲望與社會規范產生激烈的沖突,那些被壓抑與心靈深處的欲望和動機就構成了人類的潛意識,它是人類一切精神生活的根本動機。基于這些意識層次理論,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人格結構理論,這個結構模型將人格分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是在潛意識形態下的思想,是人最為原始的、滿足本能沖動的欲望,遵循享樂原則,追求個體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飽足與性欲的滿足。自我,介于本我與外部世界之間,是人格的心理面。此時,個體學會區分心靈中的思想與圍繞著個體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超我,是人格結構中的道德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組成,遵循“理想原則”。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間是處于一種協調的矛盾運動中的,人的一切心理活動都可以從它們之間的聯系中得到解釋。
對于格非來說,精神困境一直是他進行創作和思考的母題。格非自己說過“物質意義或者說物理意義上的社會變化不過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當然是精神史,或者說心靈的反應史。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變革,都會在人的內心深處留下陰翳。在改革開放的30年來,我一度悲哀地發現,似乎很難透過物質層面去觀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不管我們的反應是多么麻木而遲鈍,也不管這種反應是多么的微弱,我認為它是存在的。”①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心理活動也極為復雜,這源于格非總是嘗試從無意識層面進行挖掘,分析人物的心理,也讓人物分析自我和周圍世界。可以說格非筆下的這一群人物形象是一個整體,它代表著作者對整個歷史與現實的全方面思考,不同的人物及其性格形象也是整個精神史書寫與分析中的一環,代表了當下人們生存的某一種狀態。
二、人物群像分析
先來看《春盡江南》中的主人公譚端午,他可以說是整本小說的核心,由他牽連出以妻子龐家玉為代表的現實生存的妥協者;以哥哥王元慶為代表的隨性而為的理想者們。譚端午本身的性格也較為復雜,他存在于現實,既沒有完全按照“享樂原則”自我放逐,也沒有按照“理想原則”超脫現實,他只是以一種得過且過的姿態面對周遭的一切。一方面他進入現實的生活,在鶴浦地方志辦公室當一名小職員,拿著只夠自己抽煙的兩千多塊,在百無聊賴中自我過活。另一方面,他又有著自己的世界,愿意在海頓與莫扎特里“墮落”,靜默地觀察著周圍發生的一切,在一種烏托邦幻想中存在。如此,以譚端午為中心,將其看做一種“自我”的狀態,妻子龐家玉可以被看為“本我”狀態,哥哥王元慶則被看做是譚端午的“超我”狀態。
龐家玉,一個時代的追趕者。她原名秀蓉,作為一個仰慕詩人的少女與譚端午相遇,一夜雨露之后,兩人分離。一年之后的再次相遇“譚端午已經清楚意識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時,也改變了整整一個時代”。②過去的秀蓉已然死去,她改名換姓,自學律師,過上了時代所要求的體面生活。可以說,龐家玉遵循著享樂原則,追逐著想要的一切。但是她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本我”形象,時代的紛繁復雜與她個人的敏感憂郁格格不入,一方面她“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隊,一步也不要落下”,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有一件隱身衣,能夠生活在陌生人之中。她不斷努力,只求不被這個時代所淘汰,卻也不得不沉淪在這世俗的骯臟之中。她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與平靜,卻只能在肉欲的高潮中宣泄內心的渴望。家玉的存在就是一個矛盾體,她越想逃避痛苦,痛苦就越如影隨形。龐家玉都處于一個追求的極端,呈現出的是內心對安全感、滿足感和快樂的無意識的追求,這些都是本我的體現。“本我”是最原始的“自我”,龐家玉被現實所俘虜,她的所作所為,都是譚端午內心的一種對現實的追逐的一種放大體現,所以她對丈夫譚端午評價為“爛掉的人”但同時也為他那種憂郁與疏離的姿態所著迷,那個西藏之夢也一直在她心中。龐家玉身上已經表現出在一種“本我”的褪去以及“自我”的成長。而作為“自我”的譚端午對于“本我”的龐家玉更是有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感情,一方面,他壓抑著對于物欲的追求,對于功名浮華不甚在乎,另一方面,他又心安理得的享用著妻子掙來的一切物質生活。對于“本我”的欲望,譚端午控制和約束著,不愿被時代的洪流所裹挾,所以他身上的“本我”欲求,就通過徹底改變自我,妥協現實的龐家玉這一形象來體現。
譚端午的哥哥王元慶是一個“超我”狀態的存在。同母異父的哥哥王元慶曾滿懷希望建設一個充滿理想色彩的“花家舍公社”時,卻遇到合伙人的反對與打擊,那句“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對。沒關系。但請你記住,不要和整個時代作對”③直指時代的痛處。現實的種種束縛使得“超我”難以實現,王元慶對烏托邦的追逐只會與現實的銅墻鐵壁相撞,頭破血流不夠,他便為之瘋狂。當他的精神病治療中心落成之時,他本人就不失時機地發了病。他自詡為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正常人”,他更是時常寫下一些話語,成為箴言般關照整個文本。他以理想化的自我來要求自己,卻只能是走向死亡的“瘋狂”。他始終以“理想原則”來生存,相較于龐家玉的“本我”存在,王元慶是小說中的“超我”存在。
“超我”對“自我”有指導作用,體現在譚端午對與哥哥王元慶就潛意識的追隨上。年少時他就因為對哥哥的羨慕而走上詩人的道路,哥哥身上那種不顧一切,追逐理想,瀟灑隨性的做派,使他瘋狂著迷,雖然中年以后的譚端午成為社會邊緣人,日漸沉淪,逃避一切現實生活,但譚端午仍渴求在這個物質化的時代還能有種“詩意”存在,這種渴求就是哥哥的“理想”氣質的指導在某種意識上的體現,雖然他嘴上并不承認,但他潛意識下對已經瘋狂了的哥哥的羨慕,對仍然懷有烏托邦夢想的綠珠的親近,都是他對理想主義的一種向往。
三、自我身份的融合與重構
由此,可以看到譚端午身上具有雙重屬性,他在“本我”和“超我”的不斷沖突中掙扎,是選擇無法退回的古典時代的純粹“烏托邦”,還是徹底剝去傳統的外衣走進迷亂的時代,譚端午都不能辦到。
小說的開頭中,有一篇譚端午所作的《祭臺上的月亮》,表面上是對已經改頭換面的秀蓉的一篇告別,而實際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對于整個時代的祭文,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是那祭臺上的祭品。從改革開放至今,30多年過去,中國的社會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思想理念也顛覆了之前的傳統,太多的變化發生在潛移默化中,一切都呈現著變異與詭異,用文中的話來說“資本家在讀馬克思,黑社會老大感慨中國沒有法律,吉士呢,很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享樂。被酒色掏空的一個人,卻在呼吁重建社會道德……”④,多么諷刺,原本應當成為社會成員自我展現的平臺,卻成為欲望交織的骯臟交易場,一切都在改變,一切都被顛覆。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已是不易,跟何況“詩意的蹁躚”,時代的桎梏讓人們不得不緊跟現實的步伐。到底應該如何存在,“本我”和“超我”的二重屬性使得人物內心掙扎彷徨,放逐欲望,恐將畫地為牢;超脫前行,恐將陷于時代的孤島。
所以格非讓譚端午做一個旁觀者,用旁觀來抽離自身,避免自己的墮落和走向虛無。他沒有放棄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也沒有滑向物質的現實立場,而是游離于體制外,在邊緣處觀察著社會,成為一個社會的“中間人”。用一種獨特而冷靜的眼光來審視社會歷史的變遷,并觀察人們在此之中精神生活的演變過程,進而對自我的生存狀態進行反思。這是小說整體人物群像的“自我”狀態,是格非在進行歷史與現實、人的生存、烏托邦的意義等哲學層面上的思考后,特別是關于人的內心的一系列“如何存在”的問題的自我反思后,給出的答案。
注釋:
①格非,張清華.如何書寫文化與精神意義上的當代——關于春盡江南的對話[J].南方文壇,2012(02).
②③④格非.春盡江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29,77,236.
I207.42
A
1005-5312(2016)05-0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