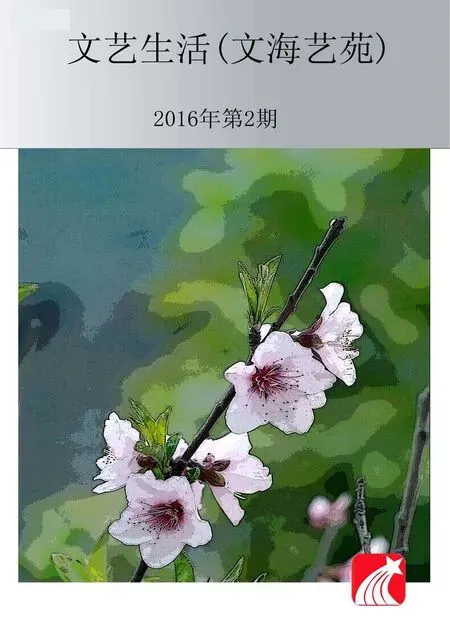日常物的轉化
蔡龍飛
(西安美術學院,陜西西安710065)
日常物的轉化
蔡龍飛
(西安美術學院,陜西西安710065)
盡管現成品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藝術品這一觀點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但日常物為什么能成為藝術品,作為藝術作品的評判標準是什么?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對于我們解讀當代藝術中的作品至關重要。
日常物;觀念;轉化
在20世紀之初,當杜尚第一次把現成品當作藝術品展示的時候,便引起了巨大的爭議:這怎么能是藝術?而到了21世紀的今天,杜尚已經成為后現代藝術的大師,他的那些現成品藝術作品也成為藝術史上的經典,現成品藝術也是藝術,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毫無疑問。但即便如此,今天的人們依然在想,這些擺在美術館里的現成品藝術與我們生活中的日常物品到底有什么區別?它們是怎么成為藝術的?
對于藝術品的定義問題,在《藝術問題》一書中蘇姍·朗格這樣寫道:“要確定一個作品是不是藝術,他要看這件作品的創造者是不是意在把它構成一種表現他認識到的情感概念或整套情感關系的形式。”。也就是說一件普通物品要成為藝術,需要藝術家通過對其進行語言或者觀念上的重新加工,使其具有新的價值意義。
傳統的藝術規范通過形式上的轉變,來實現從現實世界到藝術的轉化,通過模仿生活創造出一種虛擬的藝術形象。但是在現成品藝術中,變形轉化有其特殊性。因為在現成品形態中沒有了以質態不同的物化樣式模擬、再現現實世界的這一中介,而是直接把本來意欲模寫的現實本身作為表現媒介,現成品的物質形態并沒有發生變化。所以在現成物品轉化為藝術的時候,不再像傳統藝術一樣需要改變作品的物質的形態,藝術家只需要直接給現成品賦予他的觀念,使其從原來的使用功能中抽離出來,而成為具有了新的價值和意義的藝術品。
就像喬治·迪基對藝術概念的重新界定時需要回答的問題:現成品藝術把材料本身當成了藝術。當它聲稱一切皆可以為藝術時,當它把生活日常用品作為藝術展示時,自然就會有人質疑:這也是藝術嗎?在平常的生活中,實物又何以不是藝術?實物在什么時候才會成為藝術?藝術家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這些問題,在杜尚最早展示其“現成品藝術”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提了出來。杜尚在一本叫《盲人》的刊物上回應道:姆特(mutt)先生是不是親手制造了這個噴水裝置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選擇了一件日常的生活用品,并賦予它一個新的名稱和觀念,而把它從原來的實用意義中剝離出來,他給這個物品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它便不再是原來的普通物品而成為了藝術。
這一次杜尚再一次強調了在現成品藝術中思維和理念的重要性。1914年他所作的《酒瓶架》,用的就是一具購自小店用來放置空酒瓶的鐵架,并在該鐵架上簽上自己的名字,雖然這只是一個簽名的動作,但卻已經將此物品的“可使用價值”抽離,而轉變為“藝術品”的內涵。即把一件日常物品從他原來的使用功能之中抽離出來,給予它新的觀看視角,賦予它新的觀念。這種內涵和思想和藝術品同時存在,甚至有時比藝術品本身更為重要。
正如著名的當代藝術理論家家阿瑟·丹托在其著作《藝術的終結》一書中寫道的:“在普通物品“轉化”(transfiguration)為藝術品的過程中,藝術的闡釋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這里丹托所說的這種闡釋實際上就是一種視角問題,這種視角從根本上賦予了日常物不同的意義。就像評論家王春辰在《藝術的民主》中寫道的:“闡釋不是外在于作品之外的東西,作品與闡釋成為美學意識中的共同組合。在這個基礎上,“不可區別性”才會在理論闡釋下超出肉眼的局限,而轉化為藝術”。
其區別就在于日常物在轉化為藝術時,日常物原來的使用屬性和后來它所擁有的新的觀念之間的區別。就像安迪·沃霍爾的著名作品《布里洛盒子》一樣,1964年,安迪·沃霍爾制作了許多同超市售貨架上一模一樣的肥皂盒,并在紐約把它們作為藝術作品展出,沃霍爾的盒子跟超市貨架上盒子的區別就在于,沃霍爾通過這些流水線上工業制品的盒子表達了他對于工業社會、批量復制以及消費文化的思考,而在超市的那些盒子只是用來裝東西的日常物品。所以,盡管所使用的都是同樣的物品,但其所蘊含的觀念卻大不相同。
綜上所述,日常物與藝術之間的轉化,關鍵就在于是日常物是否被藝術家進行過觀念的加工,其自身的屬性是否已經不再是那個原來只有純粹實用性的物品,是否具有了藝術表達的功能。通過闡釋對日常物屬性、概念的重新加工,通過藝術家對其賦予新的觀念和意義,一件普通的日常物便獲得了成為一件藝術品所需要的表現特質,日常物便轉化為了藝術。這就是藝術中的日常物為什么能成為藝術的原因。
[1]阿瑟·丹托,陳岸瑛(譯).尋常物的嬗變:一種關于藝術的哲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2]阿瑟·丹托,歐陽英(譯).藝術的終結[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3]王春辰.藝術的民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J02
A
1005-5312(2016)05-02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