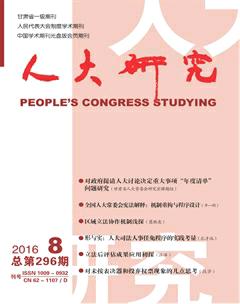第一書記“領導”下的村莊換屆選舉
陳國申 唐京華
村委選舉作為基層民主的起點,是實現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第一書記是上級機關選派的優秀黨員干部,他們參與村莊換屆選舉,有利于增強選舉的競爭性,維護選舉程序的公正,促進鄉鎮政府做好選舉的指導和監督。
一、引言
自村組法頒布實施以來,我國村民自治獲得了長足發展,村民自治也成為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重點研究領域之一。村兩委換屆選舉作為村民自治的起點,自然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學術界關于村兩委換屆選舉的研究主要沿著兩個維度展開,即個案研究與宏觀研究。從個案研究的維度,盧福營主要研究了民主選舉中的政府角色轉換、利益與選舉的關聯以及選舉的無序問題(吳萍、盧福營,2003;胡國強、盧福營,2002;李小平、盧福營,2000);郎友興、何包鋼則專注于選舉中具體問題的研究,包括村黨支部與村民選舉關系、選舉方法等問題研究(何包鋼、郎友興,2000;郎友興、郎友根,2005);賀雪峰與吳毅則以村莊換屆選舉為個案,研究了制度引入與利益主導、精英主導之間的關系(賀雪峰,1999;吳毅,1999)。而從宏觀維度,肖唐鏢、唐曉騰、戴慕珍等運用了統計學的方法,通過對眾多村莊換屆選舉的大樣本來分析選舉的相關問題(肖唐鏢、唐曉騰,2001;賀雪峰、吳毅、仝志輝,2001)。無論個案研究還是宏觀研究,都為我們全面理解村莊民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然而,近些年在村莊換屆選舉中出現的一個新現象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近年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全國各地廣泛派遣省直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干部深入農村擔任第一書記,加強基層黨建和扶貧工作。最早實行第一書記政策的安徽省自2001年至2012年已下派1萬余名黨員干部[1]。不止一屆第一書記經歷了村兩委換屆選舉的盛事,浙江省永康市甚至還專門向15個鎮街選派了31名干部擔任后進村第一書記,專門幫扶后進村的換屆選舉[2]。第一書記作為一種外來力量不經選舉而自動成為兩委成員,而且在下屆兩委換屆選舉中還要發揮重要作用。第一書記究竟在兩委換屆選舉中承擔何種角色?發揮什么作用?如何發揮作用?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們,學術界也未能展開有效研究。幸運的是,我們在一次國內重要的基層治理研討會上結識了在廣西壯族自治區H村擔任第一書記的L書記,讓我們有機會對這一問題展開深入細致研究,揭示第一書記在村莊換屆選舉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H村概況
H村地處偏僻,經濟發展水平落后。該村隸屬于廣西中北部的R縣X鄉,喀斯特地貌遍布全境,因而耕地面積狹小,全村920畝耕地人均分配后不足1畝。該村雖風景優美,但交通不太便利,山路坡陡彎急,崎嶇難行,進村道路只能容大型車輛單行。偏僻的地理位置及落后的交通狀況阻礙了該村經濟的發展,毛竹及水稻種植的收入甚微,不足以支撐家庭生活的支出,因此大多數青壯年選擇外出務工,務工所獲得的報酬是多數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多民族和諧混居,血緣、地緣關系影響深遠。H村共有常住人口1196人,苗、漢、壯、侗、瑤等多個民族混居,少數民族人口占90%以上。這里民風淳樸,各民族村民和諧共處。H村作為一個行政村共由8個自然村組成,山上、山下各四個自然村,劃分成了11個村民小組,其中山上四個自然村各為一個村民小組,山下四個自然村中有三個村分別劃分成了2個村民小組,因而山下共有7個村民小組。由于各個自然村尤其是山上四個村莊之間相距較遠,血緣及地緣關系在村莊生活中顯得尤為重要。
H村黨支部成員文化水平較低,老齡化嚴重,甚至與個別村民之間存在某些利益糾紛。該村共有黨員37名,其中10名黨員長期在外務工,絕大多數黨員的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年齡也大多在50歲以上,該村黨員這兩方面的特征決定他們雖大體了解村民自治制度的內容,但對具體的制度安排一知半解,往往忽視換屆選舉中的某些細節問題。
村兩委建構完整,但集體經濟收入匱乏。H村與“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相距不遠,其兩委工作制度經過前些年的發展雖不甚完善但也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架構,基礎制度基本具備。與全國多數村莊一樣,H村集體資產十分稀少,加之村莊自生能力較差,沒有支柱產業帶領村莊經濟發展,因而財政收入捉襟見肘,主要依靠上級財政補助也不足為怪。
H村對財政補貼的過度依賴導致了鄉村關系的行政化。據規定,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僅存業務指導關系,而不存在直接的領導和被領導關系。不過,在制度的具體實踐過程中,上述業務指導關系很多時候會異化為事實上的領導關系[3]。H村的鄉村關系也不例外:其一,村兩委認知出現偏差,將自己當成鄉鎮府的“腳”,唯上命是從;其二,鄉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兩委換屆選舉,尤其在黨支部選舉中鄉鎮掌握著決定權。鄉村關系在這兩方面異化的結果就是在村民自治實踐中,某些具體的村莊行為可能違背民主制度精神,造成對村民民主權力的損害。
三、第一書記“領導”下的兩委換屆選舉過程
L書記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的一名正科級干部,雖工作時間不長,但他綜合素質高,作為國內名校法學碩士的畢業生,對基層民主有著濃厚的興趣。2014年L書記所在單位的第一批第一書記任職期滿后,選拔第二批第一書記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該單位基于L書記工作突出、H村急需高素質人才的考量,決定派L書記前往H村開展幫扶工作。2014年是H村的選舉年,L書記作為黨支部的第一書記全程參加了H村換屆選舉,“領導”了整個民主選舉過程。
(一)選舉準備階段
2014年7月,X鄉政府為了保證下轄行政村兩委換屆選舉工作的順利開展,各部門根據職責內容做了一系列準備工作,主要通過文件下發的方式對選舉的方法及候選人的資格條件等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此外,鄉政府還成立了選舉領導小組和應急預案小組專門負責選舉有關工作的開展。
接著,第一書記“領導”H村兩委開始了換屆選舉的兩個準備工作。首先,決議村黨支部選舉方法及候選人產生方式。H村黨支部委員會發布公告宣布采用“公推直選”的方式選舉村黨支部委員會,同時,應鄉政府的要求對村黨支部委員會任職資格進行了規定,且在公告中指出黨支部委員會初步候選人先由黨員和群眾等額推薦,然后由鄉黨委收回匯總推薦票來研究決定。其次,第一書記與村兩委在鄉鎮有關人員監督指導下召開聯席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村委職數、選舉日期及選舉委員會成員等事項,此外還就村黨支部候選人進行了第一輪的投票,即黨員投票。其中選舉委員會主任由鄉領導提議的村黨支部書記擔任,副主任及委員則現場投票產生。
整個換屆選舉的準備階段,L書記作為鄉鎮與村莊進行溝通的橋梁,不僅將鄉鎮有關選舉的制度規定進行了傳達,而且參與了整個的落實過程,扮演了鄉鎮信息傳達者及村莊落實指導者的雙重角色。
(二)選舉實施階段
第一步,召開群眾代表大會。2014年7月末,H村8個自然村分別舉行了由戶代表參加的群眾代表大會,該會議主要包括兩個議程:一是推選產生第七屆村民代表及村民小組長;二是進行村委會候選人的第一輪投票以及黨支部候選人的第二輪投票,即群眾投票。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群眾代表大會參加人員不僅有原先的包片干部,每一個自然村還跟隨一名鄉鎮干部進行現場指導。當第一書記所在自然村選舉出現并列排名時,鄉鎮工作人員當即決定重選,整個選舉的過程都在鄉鎮干部現場監督下進行。
第二步,選舉村兩委初步候選人。群眾代表大會之后,H村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對群眾推選的村委會候選人進行投票,選出村委會初步候選人。然而,黨支部初步候選人的產生與此大有不同,無論是第一輪的黨員投票還是第二輪的群眾代表投票在黨支部選舉中并不具有絕對的話語權,而是僅作為鄉黨委的參考,最終由鄉黨委確定黨支部的初步候選人。選舉初步候選人的整個過程基本順利進行,只有在對村兩委初步候選人進行任職資格審查過程中,有村民舉報其中兩名初步候選人是夫妻關系,按《村民委員會選舉法(草案)》的精神,村民委員會成員正式候選人之間不得有近親屬關系[4]。第一書記知悉后立即進行了調查,結果確有其事。因此為保證選舉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地開展,第一書記向兩位初步候選人詳細講解了有關法律規定,之后兩人表示理解,并協商出其中的一人參與接下來的選舉。
第三步,正式選舉村兩委成員。首先進行的是黨支部的選舉,8月中旬,H村召開了黨員會議,第一書記及四名鄉鎮干部也參加了此次會議,與會黨員通過“公推直選”的方式順利選舉出了新一屆黨支部成員。
此次黨支部選舉有三點引起了筆者關注:其一,上屆黨支部書記獲得連任,而其將連任的重要原因歸功于第一書記及所在單位對H村開展的幫扶工作,包括援助100余萬修建村委大樓、幫助申請資金硬化村道、開展毛竹林低改、提供農業技術資助及協調465萬資金進行河道修繕等。其二,黨支部書記僅以一票優勢當選,黨員對書記人選的分歧較大。其三,黨支部候選人其實早由鄉黨委決定,前兩輪初步候選人投票并不當場公布,而是直接匯集到鄉里,黨支部“公推直選”的真實范圍其實僅是在已定候選人中進行黨內民主選舉。
9月初,H村開始了村委會的正式選舉,選舉共分兩個階段進行,即預選和正式選舉。預選會議是由村民代表組成,經過三輪的投票產生了2名村主任候選人,2名副主任候選人及3名委員候選人。預選會議中,由于村主任候選人有兩人得票相同且得票同居第二,因此在鄉鎮工作人員請示后對兩人進行了重新投票。此外,還有1名村委會委員初步候選人因未婚生育被舉報到鄉政府取消了參選資格,并且書寫了放棄聲明,這在H村兩委換屆選舉中是從來沒有過的。村委會正式候選人產生后,村民代表大會接著根據選舉情況對選舉委員會的人員進行了調整,將當選的候選人做了替換,以保證選舉的合法、公平、公正。
正式選舉階段。H村選舉采用了現場投票與流動票箱同時進行的方式,中心會場由鄉黨支部書記現場指導,每一流動票箱都有4名人員跟隨。此外,第一書記所在單位下屬的3名縣級工作人員作為縣選舉工作組人員也參與了H村村委會的選舉工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投票完成后,選票在中心會場進行了匯總,村委會主任、副主任皆以剛剛達到50%選票的微弱優勢當選,兩名委員則以絕對優勢當選。至此,H村兩委人員選舉工作順利完成。
四、對第一書記“領導”下H村兩委換屆選舉的理論分析
通過對H村兩委換屆選舉具體過程的細致分析,筆者發現第一書記“領導”的村莊換屆選舉與普通村莊之間存在某些差別,對此,我們將嘗試作出政治學理論的分析。
(一)第一書記“領導”的村莊換屆選舉組織程序更為規范,選舉結果更具公平性、公正性
程序進入鄉村社會的過程是民主進入鄉村社會的重要側面[5],程序規范對于民主的實現有著重要積極的作用。作為一次有序的選舉過程,應該具有的特征包括:選舉動員的廣泛性和深入性、選民登記的規范性、選舉辦法的明確性以及選舉現場的組織性和秩序性[6]等。縱觀L書記“領導”的H村換屆選舉的全過程,我們很容易發現,從選舉動員到正式選舉的實施組織,每一個環節都嚴格遵循了選舉的法律程序。此外,第一書記用法律知識規勸夫妻中一人退出候選人選舉更是將選舉法落實到了實處,保證了選舉的公平性。與H村之前幾屆換屆選舉相比較,此次選舉組織更規范、辦法更明確、實施更有序。
首先,第一書記的到來有助于改變“村莊無權”的地位,利用“旗手效應”獲得鄉鎮乃至縣級政府重視,強化對村莊選舉自上而下的監督,從而保證選舉程序的合法、公正。眾所周知,鄉鎮與村莊之間合法的關系模式應是指導與被指導。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政府還是習慣于將村委會作為自己的“一條腿”來對待,村委會被行政化的做法長期沒有得到改變,行政強于自治的格局基本未變[7]。事實上,不光政府,大部分村干部也將自己定位為“準行政機構”,鄉鎮政府重視的事便是工作的重點。第一書記是上級選派的優秀黨員干部,其政治地位高于一般鄉鎮干部。此外,第一書記是農村與更高級行政機關實現高位嫁接的橋梁,很容易成為群眾的“信訪代理員”,從而進行上下互動。因此,基于這兩方面的壓力,第一書記駐扎村莊必然成為鄉鎮工作的“重點村”,該村重大事項的開展也就自然而然獲得鄉鎮的全力支持。H村換屆選舉中,鄉鎮政府的全程參與以及所派遣人員的身份、數量即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有鄉鎮政府的重點支持與監督,村莊換屆選舉“走過場”“偷工減料”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選舉的程序運行也就更加合法、規范。
其次,第一書記擁有的知識、資源可以為村莊換屆選舉的合法、公正提供智力支持。據有關學者調查,2012年4月山東省省直機關單位共選派出582名第一書記,其平均年齡40.7歲,處級干部占30%以上;來自機關的240名,占41.2%;企事業單位的208名,占35.7%;高等院校的134名,占23%[8]。可見,第一書記是各單位選拔出的優秀黨員干部,一般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與第一書記的高素質相比,村兩委成員的文化知識則略顯單薄,在H村換屆選舉中,村干部們表示并不詳細知道資格審查中候選人之間不能具有哪幾種關系,甚至也并不了解合法、完整的選舉過程究竟是怎樣進行,第一書記擁有的知識、資源正好可以彌補村干部選舉知識的欠缺。同時,第一書記運用法律講解相關問題,例如選舉委員會成員回避問題、相關血親關系不得同時參選的問題等,有理有據,以理服人,可以減少選舉中不必要矛盾的產生,推動選舉合法、有序進行。
(二)第一書記“領導”的村莊換屆選舉競爭更為激烈,選舉更具實質性
選舉過程中的競爭激烈程度是衡量村民民主實現狀況的一個重要標準。有競爭,選民才擁有選擇的余地,選舉也才具有實質性的內容。競爭越是激烈,村民進行的比較分析就越全面,選出最優“領頭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H村此次選舉競爭的激烈狀況可謂是空前的:一是參選人數最多,單村委會4名成員的參選人數就達到了52人,當選比例1:13;二是當選者得票數量非常接近,皆以微弱優勢當選;三是參選者熱情高漲,積極為自己做宣傳動員。針對第一書記“領導”選舉競爭出現的激烈狀況,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第一書記“領導”的換屆選舉宣傳、組織工作較好,激發了村民從政的熱情。村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政治、法律知識匱乏是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村民自治的實踐雖在中國開展了30多年,但各村的選舉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制度引入過程,都是在強行政驅動下而展開的[9]。作為被動的接受者,大多數村民其實并不詳細了解具體的制度安排。此外,宣傳工作不重視是多數村莊選舉工作的一大缺陷,能否參選?怎樣參選?很多選民處于一知半解的境地,因而也就談不上去積極參選。第一書記“領導”的H村選舉全過程都非常重視宣傳及公示,將選舉的方法、候選人條件、選舉的程序等都以紙質形式進行了張貼,使得選民可以充分了解選舉的有關知識。加之第一書記所擁有的知識、地位帶來的個人權威增加了村民對選舉結果公正的信心,因而很多村民抱著試試的態度參與到了換屆選舉中。
第二,第一書記的幫扶改善了村莊經濟狀況,增加了村兩委職位的吸引力。何包鋼、郎友興通過實地調查研究發現經濟條件是影響村級競選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村的經濟狀況與村委會職位競選的激烈程度具有相關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經濟發展水平與競選激烈程度的相關性,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那么村委會換屆選舉過程中競選的激烈程度可能越高。第二,經濟發展類型與競選激烈程度的相關性,集體經濟越雄厚,集體資產積累越多,那么村委會職位競選激烈程度可能更高。”[10]L書記駐村一年期間除了開展低產農田改造、硬化進村道路等項目發展村莊經濟外,還協調了100余萬重建了村委大樓,利用原工作單位的資源為H村爭取了近500萬資金修繕河壩,發展旅游業。這不僅促進了全村經濟水平的提高,還增加了集體資產,并且為集體經濟發展開辟了新途徑。這兩方面因素的變化增加了村兩委對于資源支配、利用的能力以及兩委干部自身的預期收入水平,因而職位的吸引力大大提高,競選的激烈程度也隨之增加。
第三,第一書記帶來的資源增加了個人與集體的利益關聯度,從而改變了村民的政治冷漠態度。“村委會選舉能否成為競爭性選舉的關鍵是看選舉與村民和候選人利益的關聯性。能夠促進這種利益關聯性的因素可能有多種,但經濟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因素。”[11]村莊控制的資源越多,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的利益關聯度也就越高,代表不同利益的非正式組織就會基于各自的訴求展開對村委職務的激烈競爭。第一書記駐村工作可以為村莊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據有關報道,廣西2012~2013年一年間派遣的3000名第一書記為村莊引入的資金就有3.5億之多[12],L書記駐村期間也為H村帶來了低產農田改造、魚苗養殖、農作物種植基地等項目。而這些項目的具體運作都是由村兩委掌握,這就使得村民不得不積極參與選舉,并力求使掌握利益得失的權利落入“自家人”手中,選舉競爭也就變得尤為的激烈。
(三)第一書記“領導”的換屆選舉村干部穩定性更高
首先,第一書記的駐村幫扶工作增強了村干部的威信,為其繼續當選奠定了基礎。廈門大學教授胡榮在實地研究之后發現,候選人能力是影響選民選擇的重要因素。“村民希望有能力的人當選,具體說這種能力是能為村民實實在在辦幾件事的能力”,“在經濟落后的地方,村委會要辦公益事業主要靠上級政府撥款,有門路從上面爭取到撥款的村干部就被認為是有能力的。”[13]H村第七屆黨支部書記也將自己的繼續當選歸功于第一書記及其單位的幫扶,“我這次之所以能夠繼續擔任黨支部書記,要特別感謝L書記及其單位的幫助。”第一書記駐村幫扶,不僅可以為村莊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更重要的是其帶來了可觀的政策資金用于完善公共服務及增加村民收入。在第一書記駐村工作中,村干部作為其助手不僅進行了廣泛的參與,而且還極有可能是幫扶工作的實際操作者,因而村民會把村里實實在在的變化同時歸功于第一書記和村干部的“能力”。此外,由于第一書記政策的非制度化特征,哪個村入選幫扶對象都是不確定的,能夠使自己的村成為幫扶對象從而得到第一書記的駐村幫助,本身就為村干部贏得了不少村民的信任。這也就為其下一屆的當選奠定了基礎。
其次,第一書記為村民提供了表達訴求的新途徑,化解了干群矛盾。農村是一個各種利益關系交互錯雜的“熟人化”社會,村莊行政事務及自治事務也是紛繁復雜,村干部在實際工作過程中難免會因各種原因與村民產生矛盾,由于缺乏協調的途徑,這些問題就會長期留存繼而影響村干部的形象。第一書記駐村工作為這些矛盾的解決提供了協調的途徑,而且,作為更高級政府的一員,村民對第一書記的信任度遠遠高于基層政府,有第一書記“主持公道”,村民就會積極地表達不滿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第一書記與村莊沒有任何的利益瓜葛,可以作為中立的一方進行協調。這不僅有利于各種矛盾的及時化解,而且還可以緩和干群關系,維護村莊和諧。矛盾減少了,村莊和諧了,村民對于“領導班子”的信任度也就提高了,村干部繼續當選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大。
(四)第一書記“領導”換屆選舉推動了鄉鎮政府的角色轉換,有利于維護選舉的獨立性
基于稅收等利益因素及下派行政任務順利完成的考量,大部分縣鄉干部不支持村民自治選舉[14],尤其在村黨支書選舉中,鄉鎮政府的違規參與更為常見。H村黨支部選舉中候選人的產生則是鄉鎮政府的決議結果,但相比較之前的村兩委換屆選舉,H村此次換屆選舉中民主因素得到了增加,特別是村委會完全由村民選舉產生。而且,在其選舉過程中,鄉鎮政府真正扮演了監督及指導者的角色。
首先,第一書記參與選舉強化了行政系統自上而下的內部監督,督促鄉鎮政府規范自身行為。針對此次村委會選舉的真實性,L書記說“此次村委會組成人員確確實實是村民自己選出來的,不僅因為鄉鎮政府顧及到了我的存在,而且還因為H村的換屆選舉還得到了鄉、縣、市乃至省的關注”。第一書記自身具有的行政級別及在原單位的職務不僅本身能夠形成對地方政府的威懾,而且通過村黨支部第一書記這條線,可以把上級領導部門與農村、農民聯系到一起[15],成為上下溝通的橋梁,從而強化了來自行政系統內部的監督作用。其結果是地方政府違法參與或操縱選舉的風險度得到了大大提升,作為“理性”政府,停止或減少違規行為并做好指導者是其最優化選擇。
其次,第一書記參與選舉有助于克服黨支部對于選舉的控制,增強村民權力。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會議或者各村民小組推選產生。”同時,村組法還規定候選人不得在村民選舉委員會中任職。然而,實際過程中,大部分選舉委員會主席由原黨支部書記擔任,選舉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黨支部手中,其結果是鄉鎮等基層政府容易利用黨支部間接控制選舉,從而維護自身的利益訴求。H村村民委員會選舉頗具真實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遵循了法律對于選舉委員會的相關規定,對成為黨支部候選人的選舉委員會成員進行了及時調整,克服了黨支部對選舉的控制。第一書記作為村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懂法、知法,與鄉鎮黨委沒有必然的聯系,不僅可以通過規范選舉程序,依法選舉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來減弱黨支部對于選舉的控制。同時,其在日常工作中制定的規章制度規范了兩委關系,增強了村委會的權威,從而對黨支部的力量形成制約,增強了村莊內部權力博弈中的村民力量。
總而言之,第一書記作為一種外來力量參與到村莊換屆選舉中看似無關緊要,實際卻發揮著某些微妙的作用。從選舉的程序到選舉的實施過程,甚至到選舉的結果,第一書記的參與都有可能發揮某些作用。尤其是在與基層政府的互動中,第一書記的到來使得村莊內部權力關系、鄉村權力關系,乃至行政系統內部的相互關系發生了細微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出現會對村民選舉的實踐產生一系列的影響。其實不光換屆選舉,第一書記駐村所參與的大部分工作的實施過程、結果,都會因第一書記擁有的知識、地位、資源等發生某些細微變化。詳細分析第一書記幫扶村莊的作用,對于我們進入村莊、理解村莊并進而推動村莊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結語
基層群眾自治是我國政治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改善基層民主的實踐狀況,充分保證農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動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村委選舉作為基層民主的起點,是實現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就像俞可平所說的,“事實上,不管對民主怎么分類,如果從環節上看,兩個環節最重要,第一個環節是民主選舉。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可人民對國家的統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間接統治就離不開選舉。”[16]做好選舉工作,才能為村民自治的實踐奠定良好的組織基礎。第一書記是上級機關選派的優秀黨員干部,他們深入農村,積極參與到村莊換屆選舉的過程中,不僅可以利用幫扶工作促進村莊經濟發展,從而幫助村干部樹立威信,增強選舉的競爭性,還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識、資源維護選舉程序的公正,并督促鄉鎮政府進行角色轉換,做好選舉的指導者、監督者。民主選舉做好了,基層群眾自治就有了組織的保障,村民的民主權利才有了實現的基礎。
注釋:
[1]錢昊平:《黨委“第一書記”今昔》,載《南方周末》2012年7月12日。
[2]謝云挺:《永康選派“第一書記”幫扶后進村換屆選舉》,載《新華每日電訊》2010年12月29日。
[3]徐勇、朱國云:《農村社區治理主體及其權力關系分析》,載《理論月刊》2013年第1期。
[4]《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選舉法(草案)》第一百六十四條:村民委員會成員正式候選人之間不得有近親屬關系。當選的村民委員會正式候選人之間有近親屬關系的,只能留任1人,多出的候選人可自愿退出;自愿退出不能解決問題時,職務不同的,職務高者留任;職務相同的,預選得票多者留任;職務相同且預選得票相等的,由村民選舉委員會抽簽決定誰留任。
[5]仝志輝:《村民自治的研究格局》,載《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期。
[6]李小平、盧福營:《村委會民主選舉中的無序問題分析——以浙江省金華市吳村為個案》,載《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7]徐勇、王元成:《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銜接機制研究——從強化基層人大代表的功能著力》,載《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8]周群、薛祥偉:《人力資源開發理論視域下的“第一書記”扶貧政策分析》,載《延邊黨校學報》2013年第4期。
[9]肖唐鏢、唐曉騰:《基層政府在村委會選舉中的角色——對江西省40個村委會換屆選舉的綜合分析》,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6期。
[10]何包鋼、郎友興:《村民選舉中的競爭:對浙江個案的分析》,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11]胡榮:《經濟發展與競爭性的村委會選舉》,載《社會》2005年第3期。
[12]鐘春云、李欣穎:《“第一書記”真情為民》,載《當代廣西》2013年第16期。
[13]胡榮:《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影響村民對候選人選擇的因素》,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14]黨國英:《論村民自治與社區管理》,載《農業經濟問題(月刊)》2006年第2期。
[15]盧展工:《下派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很有意義》,載《村委主任》2011年第16期。
[16]俞可平:《民主與法治是硬幣的兩個面》,載《政府法制》2009年第12期。
(作者分別系山東農業大學地方政府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東北大學文法學院政治學理論碩士研究生。本文屬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招標項目“農村基層干部的代際更替與鄉村治理研究” 課題,編號[12JJD84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