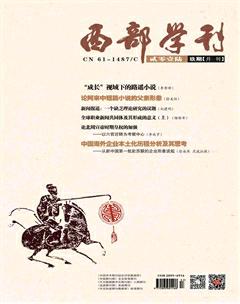從無懲罰到適度懲罰:義務教育的必然選擇
摘要:古代教育采用恐怖性懲罰維護教育秩序。隨著保護人權、保護未成年人權譽觀念的興起,我國第二部《義務教育法》及其他有關義務教育的法規明確拒絕封建學徒式的教育理念,廢除懲罰,進入了無懲罰的義務教育時代。但校園無懲罰,中小學生言行得不到規范,教學秩序無法得到保障,導致德智體教育質量無法保證。因此,義務教育不能完全拋棄懲罰,應當謹慎適用適度懲罰。
關鍵詞:義務教育;校園規則;恐怖性懲罰;適度懲罰
中圖分類號:DF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希望將黨的教育方針、教育理念上升到法律、制度的高度,以指導和調整教育。從1986年到2006年,在二十年時間內,我國就出臺了兩部《義務教育法》,反映了黨和國家關注義務教育,關注現代化建設下“四有”人才的培養。我們認為,雖然嚴厲的恐怖性懲罰下的教育確實弊端重重,但無懲罰的義務教育使少年兒童言行得不到規范,無法保障教學秩序,當然無法確保德智體的教學質量。有很多學者看到了懲罰在教育中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忍不住“重提懲罰教育”。[1]我們也認為義務教育需要懲罰。但是懲罰是一種責難學生的過錯,涉及到學生的權利與義務,更牽涉到學生是否應該承受懲罰,并且懲罰的強度或邊界在哪里?我們認為應從從法學的視角出發,理清學生權利與義務的度量,才能清晰界定義務教育中是否需要懲罰以及懲罰的強度與邊界。
一、《義務教育法》等法規驅逐懲罰,提倡無懲罰的義務教育
中國自孔子辦私家教育、漢武帝辦官方教育以來,對學生的教育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懲罰。美國著名的法社會學大師龐德在描述懲罰與教育的關系時說:“小說中的教師就是一個形象的例子,他宣稱‘男孩子必須心地純潔,不然我拿鞭子抽你。語言和行為的純潔性,在此是鞭刑所追求的最大目標。”[2]97教育與懲罰這對相生相克,如孿生子的互助互立,在我國2006年第二部《義務教育法》那里終絕了,這部法律將懲罰驅逐出了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法》第27條規定:“對違反學校管理制度的學生,學校應當批評教育,不得開除。”在第29條第二款進一步規定:“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岐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通過這二條法規,我們可以看到三層含義:
一是學校和教師不能開除學生。過去對于在學校打打鬧鬧的“學霸”,學校采取的辦法只能是開除,《義務教育法》第27條明確否定了學校這種自清門戶的手段。不僅不能開除,甚至連學生的輟學率在教育部《普及義務教育評估驗收暫行辦法》中都是有嚴格限制的。
二是對違反學校管理制度的學生不能體罰或變相體罰。這不比古代,像孔老夫子對不合意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家臣,為季氏搜刮了大量財富,孔子對此極為不滿,號召學生都去攻擊他,“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3]115事實上,在我國的刑法、民法上對教師體罰學生造成危害后果的追責應該說是很明確的,追究法律責任還是按照刑法、民法的規定或相應的司法解釋,《義務教育法》的類似規定,只能是再次重復,這恐怕也是一種臃腫立法或法條浪費。
三是有其他的侮辱學生的行為。所謂的侮辱,侵害了學生的名譽,“就是對他人表示輕蔑。”[4]660教師的言語、對學生的評價,很可能侵害了學生的名譽,刑法學與民法學將名譽分為內在的名譽與外在的名譽。內在的名譽是指人對自己的內在價值(如素質、能力、品行、信用等)所具有的感情。這種內在的名譽感情一般不可能受到侵害,就像屈原對自己受到非議根本不予認可,他的《離騷》可以看成他的牢騷,對自己的真善美的堅持,在他的詩中可點可滴。外在的名譽是指社會對特定人的評價,包括社會對特定人的品德、才能、思想、作風的評價,外在的名譽很可能受到傷害。所以我們認為,侮辱是一種對外在的名譽感的傷害。因此教師不能口無遮攔,隨意傷害學生。不能像開私學之先的孔老夫子通過言辭之激烈、動作之刻薄給學生深刻的刺激。孔老夫子看到能言善辯的弟子宰予白天睡懶覺,不禁大發其怒,對他進行了嚴厲嘲諷:“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于予何誅?”[3]45在教育法的孕潤下,當今的教師恐怕沒有孔老夫子那樣的膽量。
為了保證對違規或違反學校管理制度的學生受到不開除、不被體罰或變相體罰、不被侮辱的待遇,我國在《教師法》中進一步落實責任。《教師法》第三十七條中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一)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務給教育教學工作造成損失的;
(二)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
(三)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
在《教師法》中,竟然將體罰、侮辱學生作為獨立并行兩類行為,并且為了禁止教師體罰、侮辱學生,教育部2014年頒布的《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教師有體罰學生的和以侮辱、歧視等方式變相體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的,視情節輕重分別給予相應處分。
所以,這些教育法律和制度的確落實了對違規學生不得開除、不得體罰或變相體罰、不得侮辱,所以就進入了無懲罰的義務教育時代。
事實上,一群兒童少年聚集的學校,他們沒有自制能力,沒有令人畏懼的父權權威、宗教權威、教師權威,還喪失了規則權威,只有初生牛犢不畏虎的膽量,世界著名的犯罪學家謝利也說,少年犯罪的增長我們能夠理解,他們惡毒的程度我們難以想象。[5]121在我國保存得最早的法典《唐律疏議》,開始就講:“刑罰不可廢于國。笞捶不得廢于家。”[6]1古代的校園采取的是恐怖性懲罰,天地君親師的威嚴,教師的打罵,迫使學徒式的弟子中規中紀。但是,恐怖性懲罰與現代社會的教育理念日益不合,這是一個關注人權、關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時代,對于學生來說,應當緩解懲罰。對我國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社會主義教育學家如蘇聯的馬卡連柯也反對資本主義建立在學生痛苦基礎上的體罰制教學。[7]284我們認為,《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的立法者,滿懷社會主義教育理想,對封建學徒式教育的不滿,基本上全盤否定舊的教育理念、舊的教學方式,本來是想驅逐過度的、殘暴的恐怖性懲罰,采取的方法就是全然廢除任何懲罰,這樣懲罰被驅逐出了義務教育領域,開創了無懲罰的義務教育時代。
二、廢除適度懲罰對義務教育造成的危害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在制定《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的同時,教育部及其官員不忘素質教育,制定《小學生守則》、《中學生守則》、《小學生行為規范》、《中學生行為規范》,后來教育部干脆制定《中小學生守則》,還有《小學生行為規范》、《中學生行為規范》。用心也很良苦,反映了教育部及其官員希望學校就是一塊文明、規則的凈土,中小學生應該被訓練為“四有”新人。但教育部的這種善良企望,在中小學那里、在中小學教師那里存在一種深深的乏力感。因為沒有一種強力機制去培養、訓練適齡學生的文明、規則。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義務教育法》、《教師法》和其他有關未成年人的法規中明確廢除了懲罰制度,只保留了教師喋喋不休的嘮叨,而中小學生對他們父母的喋喋不休常常是冷漠或是反抗。所以有的學者說,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一種虛弱的教育、脆弱的教育、不負責任的教育。[8]
第一,沒有相應的懲罰制度而難于建立文明和規則。社會學大師涂爾干說,懲罰是規則的自衛手段,沒有懲罰,規則怎么立足。[9]51因為中小學都是文明和規則的凈土,一方面中小學生在這里學習知識,為了保證學習和掌握知識,良好的學習環境就顯得重要,所以中小學生還必須接受和遵守校園規則。伴隨規則的良好伴侶就是懲罰,因為規則教育、規則訓練,就不能不運用懲罰手段。法國思想家福柯將規則訓練視為“規訓”,他說,學校、工廠、軍隊都在實行一整套的微觀處罰制度,其中涉及時間(遲到、缺席、中斷)、活動(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熱情)、行為(失禮、不順從)、言語(聊天、傲慢)、肉體(“不正確的”姿勢、不規范的體態、不整潔)、性(不道德、不莊重)。有些失誤必然伴隨著懲罰,因為懲罰將過錯人置于難受之地,能夠使他們感到羞辱和窘迫,迫使過錯責任人認識到自己的過錯,改正過錯。[10]202并且學生的學習時間、學習內容、作業量以及學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規定的教育質量,也都是學生參加義務教育必須達到基本標準。如果學生遵守規則,達到標準,他就順利通過。如果他不遵守規則、達不到知識的最低標準,懲罰或補考也使過錯人置于難受的羞辱和窘迫境地。學校的校園規則在學生入學那天就應該明示,提倡學生在校園規則上簽字并表示遵行。美國教育法學家也主張:“為確保所有學生都了解學區紀律行為規章,我們建議學區管理者要求所有學生都簽署一項已知聲明,以表明他們都閱讀過學區的紀律行為規章。有了這份聲明,違紀學生就不能以不了解學區紀律行為規章為理由進行“未知”抗辯。[11]202
學生如果觸犯校園規則,就會出現班主任個別談話;風紀教師與家長、學生就違規事實座談,學生具結悔過;記過、移送工讀學校等。正是這樣的懲罰形式,才是校園規則得于建立的必然過程。因為這種懲罰也使違規學生難于接受,體驗到痛苦。著名的法社會學家埃利希說,正是因為懲罰使人不愉快,大家就會注意規則而不會隨意違反規則。[12]302懲罰使規則強硬、充滿活力。因為遵守規則的人享受激勵與便利,違反規則的人受到責難與羞辱,同學們自然挑選與規則一致的行為模式。
第二,堅持適度懲罰,也是學校維持正常教學的必要條件,沒有適度懲罰,必然會導致校園規則被侵犯、風紀淪喪,喪失應有的教學秩序。少兒好玩耍,接受義務教育,就必須忍住心中誘惑的魔,聽清并弄懂教師傳播的知識,必須內有毅力支撐外有規則監督。缺少懲罰的規則就像一面刻著規則的招牌,開始還很雷人。漸漸學生們發現規則是可以不遵守的,充滿悟性的他們便嘗試自己歡快的行為模式,取代學校希望的規則模式。老實說,在重點學校或重點班,同學們因為有學習經驗和優異的成績受寵得勢,大多會遵守校園規則。但在是在一般學校或一般班級同學們缺乏學習技巧、成績一般或較差,就不那么受寵,讀書也不是那么甜蜜快樂,遵守學校管理制度就比較差。取消了對違規學生的適度懲罰,學校和教師對違規學生也是無可奈何,事實上孫悟空手中沒有金箍棒,也沒法護法。
廣東珠海文園中學初一(6)班一個叫阿文的學生,被當地婦幼保健院診斷為“孤獨癥譜系障礙”。只不過,這個自閉癥學生并不是在安靜地“自閉”,他有暴力傾向、行為不可控,時而威脅學生、傳播黃色網站。他在女生前脫褲子自慰,對同學說“我要殺死你”、“殺你全家”等威脅言詞,同學很恐懼,家長很揪心,學校也沒辦法,自然沒法維持教學秩序。46人的班級已有42名家長聯名向信訪局、教育局投訴,要求把阿文和其他同學分開。[13]
不僅是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搗鬧,也令班級無法安心上課。南京市一所小學的三(1)班,有四個小男生非常調皮,讓老師、班上其他同學和他們的家長都頭疼。上課打打鬧鬧,他們坐在教室后面,桌椅板凳都掀翻了,砰砰啪啪地吵鬧。老師在上面講,他們在下面鬧,坐在后面的同學都聽不清楚老師講的是什么。后來矛盾升級,班上30多個孩子沒辦法學習,導致當天停課。小小的小學三年級的學生就鬧得學校上不了課,簡直是駭人聽聞。[14]
很多學校雖然沒有上述學生的“出格”,但學校和教師即使在教室里,沒有針對性的強有力的懲罰手段,不能、不敢糾正學生的歪風邪氣,這是編纂《義務教育法》等教育法規的立法者們不會看到的。
第三,在義務教育立法中,廢除懲罰的義務教育對抗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集體主義原則。廢除懲罰,照顧極少調皮的“熊少”的歡娛,將大多數同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共同利益拋到一旁,大眾的集體的利益何在呢?集體主義原則存在一個基本的解說:一是強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一致性,重視個人利益;二是強調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應當犧牲個人利益。但我們的教育立法剛好背離了集體主義原則。當一個或幾個兒童或青少年大鬧教室、校園,威脅教師或其他同學時,我們的集體主義原則、校園規則哪里去了?我們一個班、一個學校只能目睹個別人的邪惡,只能無能為力?這個時候,大多數同學的利益、學校的利益甚至有關民族振興的義務教育排在什么地方?這在講究個人利益、個人主義盛行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采取“零容忍”的態度,[11]229我們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的原則,在集體主義原則指導下教育法條,卻造就了只準個人邪惡,學校、教師和大多數同學不敢出面制止,從這種意義上講,廢除一切懲罰的義務教育的確是對抗了集體主義原則。
第四,在《義務教育法》廢除一切懲罰,尤其是禁止開除違規學生、禁止侮辱學生等,一是同現行法律相沖突;二是像“其他侮辱學生人格的行為”含義飄忽,作為法律規則必然導致不準確,難于遵守,同時也使教師的教育行為無法找到確定的行為模式。
首先,雖然《義務教育法》第27條規定:“對違反學校管理制度的學生,學校應當批評教育,不得開除。”但還是實際存在開除學生,也有變相存在的開除。先看實際存在的開除。一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對于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在人民法院判決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學籍。也就是說,在判決生效后,可以取消其學籍,也就是可以開除。二是當未成年人因犯罪被關押時,所在學校是否要派教師進監獄或收容機關為該疑犯上課并考試?事實上是監獄或收容機關在為未成年人履行義務教育的職責。這就是不是開除的“開除”。變相開除是指《義務教育法》第20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為嚴重不良行為的適齡少年設置專門學校實施義務教育,這種專門學校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那里就稱之為工讀學校。將這些嚴重不良行為的適齡少年移送到工讀學校,不是開除,也是變相開除。所以我們說,《義務教育法》等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取消開除措施,與同一法律的其他條文和其他有關未成年人的立法相沖突,真實的開除或變相的開除也還存在。所以我們認為,《義務教育法》禁止的開除學生,是在法定條件以外開除學生,但是法定的開除或變相開除除外。
其次,《教師法》第三十七條還把體罰學生和侮辱學生當作兩種不同的行為,立法者是否嚴格考察了侮辱的來龍去脈,這樣立法就更加模糊“侮辱”一詞的含義。《義務教育法》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辯出了正確的含義。禁止體罰、變相體罰與其他侮辱學生的行為,意思是說,體罰、變相體罰是侮辱學生的具體行為方式。人們清楚體罰與變相體罰的含義,但其他侮辱學生的行為是什么?就含混不清。因為學生有過錯,必然遭到教師的否定和指責,教師的這種否定和指責可以采用語言的或表情的方式,使學生的自身形象受到詆毀、尊嚴遭到挫傷,必然造成學生心理上的刺激,情感上難于接受,是否可以看成對學生的侮辱?如果是,這就使得教師不敢嚴肅指責學生的過錯,恐怕就走向教育的反面。
事實上,刑法學和民法學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它們將侮辱行為分為兩種情形:一是暴力,包括體罰、變相體罰;二是謾罵。所以《義務教育法》就應該吸取民法學刑法學相應研究成果,明確禁止教職員工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和謾罵。這樣就使得《義務教育法》的條文含義清晰,成為明明白白的行為規則。教師也能夠清楚理解在教學活動中不得對學生隨意實施體罰、變相體罰和謾罵,在這“三戒”之外,有權對學生的過錯進行批評和指責。
三、適度懲罰:實施義務教育的基本保證
我們認為,《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有關義務教育的立法規定在義務教育階段對違規學生廢除恐怖性懲罰,是正當的,但做得有些過火。體現在學校和教師對違規學生不得開除、不得體罰、不得侮辱,造成了無懲罰的義務教育。但一個班級、一所學校這樣的集體,必然有維護集體利益的規則,維護規則就必然存在相應的懲罰,這種懲罰當然不是殘暴的恐怖性懲罰,它是對應對違規學生的適度懲罰。
廢除義務教育領域對學生的任何懲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對從事義務教育的教師身份缺乏一個完整的認定。他們事實上是學生的知識傳播者,也是學生的兼職監護人。按照國家對教師資格的基本要求以及考核規定,也使教師成為具備一定的知識儲備與謹慎態度的家父家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在校期間,教師還接受家長的委托,成為傳授知識并接受家長委托的兼職監護人。在《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中,充分肯定了教師的教書育人的身份。但對學生家長將自己應予監護的子女送到學校、教師那里,則沒有明確規定學生在校期間,教師就必然分享監護人的權利與義務。但從其他法規中教師還是家長授權的監護人。因為中小學生在學校寄宿是常見現象,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九條則明文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為什么未成年人在中小學寄宿就可以脫離監護人,單獨居住?從法律的無言中,我們推斷是因為未成年人在校住宿,教師是他們的兼職監護人,當然學生就不算脫離監護單獨居住,這一點國外教育學家和教育法學家也是普遍認可的。
既然從事義務教育的教師是一個知識傳播者,也是兼職監護人,他們在從事義務教育時,必然具有傳播知識、管教學生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認為,義務教育的學校和教師在義務教育中,有管教學生,維護義務教育的基本權利:
一是學校和教師在一定的條件下對違規學生采取強制手段,是合法合理的。所謂一定的條件就是事件真實發生,并且急迫,無法等待家長、警察,不采取強制手段則無法保護同學們、教師們的安全,也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如教師和校警制止暴力打人的學生,或將搗亂課堂、影響教學秩序的學生強行帶至學校風紀教師辦公室。在刑法上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就是這種強制行為的堅實理由。因此,學校和教師為避免更大的傷害、維護教學秩序所采取的的強制手段,也是合法合理的。
對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家長承擔監護人角色,對被監護人還得采取懲罰手段。國外發達國家的教育立法中,沒有我們國家不準體罰的強力戒條,教師過度體罰學生,也是適用刑法、民法相應條款追究刑事或民事責任。事實上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六十條坦然承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分別依照行政法規追究行政責任;依照民法追究民事責任;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責任。在《義務教育法》、《教師法》中,禁止體罰、變相體罰的規定,如果這些規定有意義,也就是開出了對教師的罰單。其危害性在于,沒有對危害教學秩序的行為,開出懲罰性罰單。導致了學校和教師對于不良學生的霸道、搗亂無可奈何。尤其不良少年兒童暴力侵害其他同學、侵害教師人身安全或搗亂課堂秩序時,學校和教師該怎么辦?至關重要的情節,我們的法規沉默!像珠海市文園中學初一學生阿文在女生面前脫褲自慰,我們學校、教師聽之任之,不強力制止,才是悲哀呢!
二是學校和教師真實告知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學習、品行的真實情況,對學生的過錯加于批評和指責,這是作為教師、兼職監護人的權利,也是他們的法定義務。雖然學生知道真實情況會感受到羞愧、沒有面子。還有的學生離校離家,甚至有的自殺。但學生也要面對真實情況,也要接受失敗的教育,從而奮發努力。法學家們對于這一問題,也有爭論。有的法學家認為,教師告訴學生真實情況,不是制造情節,使學生感到受輕蔑。即使一般人只要講真實情況,就不存在承擔侮辱罪名。就像家長知道自己子女的缺陷,也會告知他們,希望他們盡力改正。所以孟子才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孟子的道理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所以社會輿論及學生家長應該對這一問題有明確的界定,對于教師教育學生、批評學生的過失,不可無端地指責學校和教師。
三是教育法規禁止義務教育階段開除學生,但在《義務教育法》及其他有關未成年人的法律中,存在一種將不良少年移送到其他機構接受義務教育。一是刑事判決生效后,未成年人到受刑地接受義務教育,學校也應當開除其學籍的人;二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舉辦的專門學校接受不良行為的少年,有的法律干脆稱之工讀學校。我們希望義務教育法規從原則性向規則性更進一步:移送誰?怎樣移送?否則,就會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我們認真閱讀義務教育法規,感受不到進取的力量。法國思想家埃爾說法國的教育立法是通篇毫無道理,又寫得缺乏優美文筆。[15]7我們反省我們的《義務交育法》及其他有關義務教育的法規,也是有些感觸。一是希望保留適度懲罰;二是希望這些原則性條款能向規則性條款轉換,成為有實效的、能操作的法律條文。
參考文獻:
[1]梁濤.重提懲罰教育[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7(6).
[2](美)羅科斯·龐德.法律與道德[M].陳林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日)木村龜二.刑法學詞典[M].顧肖榮,鄭樹周等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
[5](美)路易斯·謝利.犯罪與現代化[M].何秉松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6]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蘇)吳式穎等.馬卡連柯教育文集(上)[M].人民出版社,1985.
[8]孫云曉.懲罰不等于傷害,沒有懲罰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EB/OL].
http://edu.china.com/zh_cn/subject/parent/housemaster/10000293/20021028/
11353362.html.
[9]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10](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1999.
[11](美)內爾達·H·坎布朗-麥凱布,瑪莎·M·麥卡錫,斯蒂芬·B·托馬斯.教育法
學——教師與學生的權利(第五版)[M].江雪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12](奧)尤根·埃利希.法律社會學基本原理[M].葉名怡,袁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9.
[13]單士兵.誰把家長逼到了聯名投訴的地步[N].中國青年報,2014-12-16.
[14]4個“熊孩子”天天大鬧課堂,30多個同學“罷課”抗議[EB/OL].http://news.ifeng.
com/society/2/detail_2014_04_22/35934892_0.shtml.
[15](法)維克多·埃爾.文化概念[M].康新文,曉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簡介:李化祥,男,哲學碩士,嶺南師范學院法政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