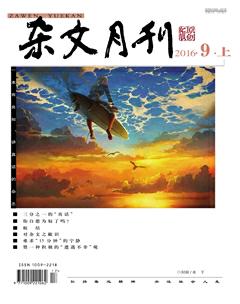難求“15分鐘”的寧靜
易見
薛涌先生任教美國高校多年,對美國的教育有著多側面的觀察和思考。據他講,他現在任教的薩福克大學,在美國名不見經傳,但對學生的吸引力卻非常大,常有姐妹兄弟甚至父子母女幾代人都在這同一所學校學習畢業,并以自己的母校為驕傲。原因在于,除了有幾個很好的品牌專業外,學校對待學生非常的人性化。譬如,許多孩子高中畢業后不適應大學學業,一年級輟學率非常高,可薩福克大學并沒有因為生源不愁就讓素質不好的學生自然淘汰,而是投入資本,開辦“新生討論班”。同時學校還設立一筆專門經費,帶學生旅游,請學生吃飯,保證學生“賓至如歸”。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們認為,輟學率太高,并不說明學校的競爭力,恰是說明學校不能幫助學生成功。不管到哪里,學生的失敗就是學校的失敗。一所普通大學能這樣設身處地為學生著想,有著這樣的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如此幾代人都在同一所學校求學的“回頭客”現象,還算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嗎?
而我們的一些大學,尤其是一些二三流的大學,對待學生的態度常常不脫騙、冷、推三部曲。所謂“騙”,是通過改校名和網絡上的虛假宣傳等手段,先把學生“騙”到手再說。等把學生“騙”進校后,堆滿笑容的面孔就迅速板結,充斥在校方的訓導語言里不是這“不準”就是那“不許”,管理生硬、冷漠、僵化,直把大學生當中小學生管。因為怕出事擔責,有時候節日里也不準學生出校尋親訪友。學校的各類組織機構更是對學生們缺乏應有的尊重,學生去辦事,可謂臉難看,門難進,還動輒被訓斥得像孫子一樣。此謂之為“冷”。當然,對待那些多少有些背景的學生則例外,甚至教務部門強令教師將其不及格的成績改成及格這樣的事兒都做得出。到了畢業季,學生基本沒有什么利用價值了,就開始“推”了。為達到什么就業率指標,千方百計動員學生趕快簽約就業或“替”學生就業,只求能把學生盡快推出校門就算萬事大吉。
像這樣對學生又騙又坑又推的高校,還奢談什么“回頭客”?常見這些高校的本科生,大一剛入校時,還充滿朝氣,對大學未來的生活充滿著青春詩意般的憧憬;大二時,逐漸失望,開始“看破紅塵”,頹態漸現;大三時,已毫無活力,暮氣滋生,部分學生還學會了見風使舵和“告密”;大四時,則心思早已不在課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忙著為畢業后找出路、找門路了。
把高校辦成這個樣子,不要說學生,就是教師,都有了另謀出路“走”的心思。只是我們的人才流動并不那么自由方便,難以遂愿而已。如今的某些大學,行政力量非常強勢,今天一個評估,明天一個認證,一年一小考(核),三年一大考(核),各種表格填寫沒完沒了,各種會議、學習隔三差五。為了什么政績,各類限令教師做這寫那的部門文件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誰都可以給教師吆喝著分派這個任務那個差事。說過去的年月是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沖擊了教學科研,如今又是什么東東,使得偌大校園,幾乎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中國科技大學教授陳曉非對母校最深切的認識,就是一個“靜”字。他說,“我喜歡中國科大的安靜”。這個安靜,既指校園環境的安靜,更是指內心的安靜。美國學者漢普頓,曾將印第安部落一位長老送給他的一塊小紅石,安放在美國奧林匹克國家公園霍河雨林中的一根圓木上,并將那里命名為“一平方英寸的寂靜”,希望這個偏遠荒地的自然聲境能被很好地保持和管理。他定期到那里,監測、記錄著可能入侵的各種噪音,還嘗試確認其來源。他的記錄告訴我們,在美國要找到連續15分鐘以上的寂靜,極度困難(《報刊文摘》2016年6月29日)。
我們的教育部門的行政官僚們,某些大學的主事者們,你們能讓大學教師的內心連續保持“15分鐘”以上的寧靜,讓他們純粹再純粹點,回歸于本職工作,心無旁騖地專注于教學科研嗎?倘連這一點都做不到,要爭創世界一流大學,豈不扯淡!
【王成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