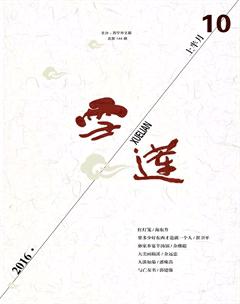與亡友書
一
事故摔碎了時間。
血液把公路燙出了一個大坑。淚珠在車前歡快地奔跑,你看紅線斷開,一百零八顆佛珠崩濺,倒也散發(fā)孩童般的歡快和自由。
然而,這樣的崩濺持續(xù)了二十年。沒有誰能夠忍受二十年的斷裂、脫落和崩濺。
在雨雪交加的夜晚,你聽到大風(fēng)的呼喊,由嘹亮轉(zhuǎn)而混濁,由混濁突然明亮。
偶然,改變了命運。或許,還有性格。
死亡,每天在打量你;有時,露出亡友明燦的微笑——太亮了。
二
現(xiàn)在,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以你的離去,作為最強烈的愛的宣言;但是——
這宣言更是一種刻骨的復(fù)仇。
你把自己刻在我的骨頭上。
每時每刻,我都感受你的存在,你的變化,你的小心眼。——還有你的冷酷:絕不和我面對面。
尤其是,當(dāng)雨珠在玻璃窗上唱著寒涼的歌曲,在光滑的鏡面即死即生,即隱即沒——
你知道,這時我只想偏執(zhí)地把臉從屋內(nèi)伸入玻璃薄窄的空間,然后終于貼向夜晚,貼向你,貼向雨滴的溫度——
當(dāng)然是無情的!
誰也不能穿過玻璃,從這一面到另一面,類似從生到死:你在嘲笑,你在微笑。
你的笑容和雨滴一樣凄冷。
三
我對你的遠行,毫無準(zhǔn)備;如同,我對你信任,毫無準(zhǔn)備。
而你也僅僅在我的夢中造訪過一次。
在夢里,我已經(jīng)在你未至之時,感覺到你推動微風(fēng)輕塵的氣息;當(dāng)你面對我,隔著一段不可能兩手相握的距離,我已盡知你的心意,你的來意,你的凄惶,和你眼中劇烈的憐憫——是涌向生者的憐憫。
后來,你恰恰屬于百天的那張臉,你最后的那張臉,在我的大腦中變成了一只揮別的手,緩慢而堅定,就像一只就要隱藏起來的鐘擺。
你的臉,像一只鐘擺在黑與白的交叉地帶向我揮別;有時又像是永生的呼喚。
四
永遠17歲的女孩,我沒想到在烈日下,接觸你的衣飾、書本和玩物的方式——竟然是焚燒。
讓火焰給你帶去這些熟悉的物件,也許它們到達你手中時,還保留著人間氣息。
火焰輕快地舔舐著白色的裙子,火焰怒氣沖沖地翻烤厚重的冬衣。
我是說,在另一個界面烈日正翻烤著我,箭雨般的日光怒氣沖沖沖刺我的頭頂和脊背。
五
我看見自己的汗粒飽滿地滲出皮膚,像膽怯的孩子坐在窗臺,猶豫著跳還是不跳。
當(dāng)然是要跳的。
再細小,再純粹,再柔美,也還要跳的。不跳,也會被推下去。你看,春風(fēng)撕落了多少花苞?何況,接踵而至的還有急驟的夏雨,刀鋒閃動的秋霜。
汗粒從額頭、眉間、鼻梁、下巴、脖子、腹背、胯間,雙腿,還有腳指縫中艱難地冒出來,失重般、入魔一樣滴下去。
我就是一個汗粒。
在時光的碾軋和世事的切割中,盡管獨生無依,充滿了血一樣黏稠的痛苦,鹽一樣濃重的記憶;卻也是愛意飽滿,有種自我開花的溫軟感覺。
跳,還是不跳,這是一個問題。
跳,還是不跳,這不是一個問題。
六
沒有誰不在呼吸,不在飲水,不在啃噬;蠕動的咬肌,開合的牙齒……換一個角度,這是一個貪婪的世界,不是在吃,就是在被吃。
巴列霍說:我不在這里喝咖啡,會有另外一個人……我占據(jù)著誰的生存位置,滿口滿腹嚼咽的是誰的血肉?
我愛上了陽光,就是愛上了罪孽。
我愛上了罪孽,因此分外珍惜陽光。
七
如果,我沒有主動認識你,那將如何?
如果,我們的心不是天然地相像,那將如何?
如果,死亡不曾打斷,你現(xiàn)在如何?
如果,死亡不曾打斷,我現(xiàn)在如何?
如果,我不曾產(chǎn)生這持續(xù)終生的負罪感,那將如何?
如果,我像失控的浮士德拋卻所有,一頭扎進幽深密林,在恐怖和無恥中肆意妄為,那將如何?
可是,我在輕飲你,一小口,一小口,讓爬上腹腔的茶垢退去,讓喉嗓發(fā)出清正的聲息。
八
你以奇怪的方式,和我同在。
你隨時翻閱我的靈魂,就像微風(fēng)或者狂風(fēng)檢視著葉簇。
你嘩嘩亂響,你汩汩而歌;你有時像竊聽者,窺視者;我在你面前沒有秘密。
我已經(jīng)把自己視為一卷書冊,有些紙葉落上了字粒畫符;還有一些仍然等待你的手指。
書卷嘩嘩亂響,書卷汩汩而歌;就像葉簇,就像清泉:就像你和我的從前。
九
旅行。流浪。放逐。
醉生夢死。湖邊獨坐。用青海話在夜晚的空寂的西寧大聲朗讀,驚醒了街巷的燈火。
算不算自我表演,自我催眠,自我麻痹?
管他呢!我的人生已經(jīng)拋卻舞臺劇。
我活著,我行走;我忽夢忽醒——我相信會在某一刻遇到你;當(dāng)然也會再次失去——就像日月的交替,就像血液的喧囂之后骨頭的寂靜。
大概這也算是靈魂的一種滋養(yǎng),也算是帶有酸苦味道的獨自的信仰……
【作者簡介】郭建強,有詩歌、小說、隨筆數(shù)百篇(首)見于《人民文學(xué)》《詩刊》《詩江南》《上海文學(xué)》《花城》《青年文學(xué)》《世界文學(xué)》等。著有詩集《穿過》《植物園之詩》《昆侖書》等。有作品入選三十余種國內(nèi)詩歌和散文選本。獲青海省第六屆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獎,第二屆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第二屆海子詩歌獎提名獎,2015中國桃花潭國際詩歌藝術(shù)節(jié)新銳詩人獎,第二屆《人民文學(xué)》詩歌獎。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青海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現(xiàn)為西海都市報副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