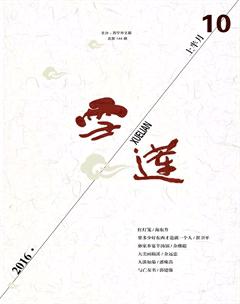人淡如菊
潘姝苗
秋季在我心里,像舊時的月色,被打撈起來,盛入藍底釉白的青花瓷盞里,伴茶飲進,沁人心脾。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用“淡”形容菊,是一種意境自不必說,用以喻人,更是一道風骨。秋色連波,寒煙翠籠,每當西風漸緊,漫山遍野飄蕩的都是疼痛的痕跡。該開的花兒都已綻放,該送的祝福無論是否成真,也一一風荷舉,圓的圓殘的殘。生命的歡顏次第呈上,窮盡三十余年,氣力也堪足,心性也盛過,最終不過是一場繁華落地,惟留素淡在心。
小的時候,連伙伴也很稀有,只揪著你多我少、你新我舊的衣食計較,同姐妹們鬧不和,與父母唱對臺戲。走入社會,收斂了倔強,卻藏不住外強中干,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差事。記得我初到單位,先扛鍬再拿帚,最后執(zhí)筆,那幾十米長的水泥樓道,被我天天拖得水滑光溜。嫁為人妻,與執(zhí)子之手的那個人較著勁,先有兩年的相看不厭,待身為人母,脾氣見長、欲念也長,就像稻田里一壟壟的野草,越不被待見越發(fā)兇猛地冒出來。直到對著家里踹破的門,摔爛的椅子,冷戰(zhàn)如雨無人哄勸,才自知過了分,慢慢有所收斂。而今臨睡,枕邊那人欲再攬我入懷,我只將背朝向他,給一個“困”字。耳后傳來他悻悻然的自語,誰當年不枕著別人的胳膊就不睡來著?生命難道是供奉的香案,只看菊花殘,滿地霜,彼此的笑容已泛黃。
碧云天,黃葉地。喜歡秋,最初是源于它的豐盛,火紅的柿子,烏紫的葡萄,澄黃的鴨梨,還有麻房子里的花生果,長著犄兒的水菱角。對于平日貧瘠的廚臺,這些吃食像老天爺應(yīng)景的贈禮,不消費力就得來了。現(xiàn)今居家赴宴,飲食只揀清淡,應(yīng)酬只求簡約,翻書但看閑散,再不像年少時分,急吼吼端著碗里看鍋里,貪多嚼不爛。
秋意孤獨,世道亦然,當談古論今演變?yōu)檎劰烧摻穑l懂心素如箋。拿出當年手抄的一本本詩集,一頁頁翻開,不似我在看字,倒像一個隱居世外的故人,帶著異樣的眼神在打量我。昔日,我曾經(jīng)像山野里的雛菊,不聞香,不逐色,但有空穴里一股來風,便掙掙地探出腦袋,拼命地開。如今,我急急趕路,身邊同行者或有三秋之隔的晉進,或有萬夫莫開的威力,變化都是疏忽之間的事,哪有閑情吟詩作賦北窗里。迷失,是在路上最多的感傷,剪一段往日的筆墨,但將心事付西風,權(quán)當他鄉(xiāng)是故鄉(xiāng)。
夜太漫長,凝結(jié)成霜;夢在遠方,歲月滄桑。透過迷蒙的夜色,踏不進時光的那條流。成長的腳步漸去漸遠,秋的豐饒像一縷風、像一抹紅,輕輕一吹就散了,我明白屬于自己的蛻變已為數(shù)不多,就像許多去不了的地方,遇不見的人,我需要把握的,只是攥在手心里的溫暖,以及積攢在心頭的淡定平和。
秋色已濃,人淡如菊。我將打起背包,離開市井,攬一懷平湖秋水,坐一澗鳥鳴魚翔。田崗繞炊煙,阡陌閃雛菊,心事淡淡一如初妝,帶我一腳跌入含苞待放的夢鄉(xiāng),不醉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