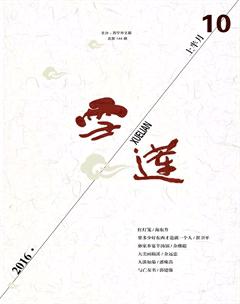夢想和現(xiàn)實(shí)
張靜
生不做萬戶侯 ,但愿一識韓荊州。
——李 白
一
那一年,我搞專題攝影搞得轟轟烈烈,幾家報紙報道了我的事跡,后來,一家電視臺來采訪我,記者問,“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民間行為,是什么動力促使你吃這么多苦,走幾個省搞專題攝影?”聽了這句話,我久久地沉默,如果讓我回答的話,我想用艾青的一句話來回答“為什么我的眼里總是飽含了熱淚,因?yàn)槲覍@土地愛的深沉。”
攝影機(jī)唰唰地轉(zhuǎn)著,記者的眼里滿是期待,他們哪里知道,在我的心里,有一個難言的結(jié),有一個深深的痛,有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疤……
我是一個教師的兒子,爸爸媽媽大學(xué)畢業(yè)后分到離省城幾十公里的兩個小山村,在那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將他們的青春奉獻(xiàn)給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十五歲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鐵路中專,畢業(yè)后,到鐵路上班。平時常常寫些“我在地球的邊上放著風(fēng)箏”之類的詩,生活平淡并且安逸。六年后,發(fā)生了兩件事,一是哥哥辭職去了深圳,兩年后出國;另一件事是一個同事去了省電臺當(dāng)了一名主持人。這兩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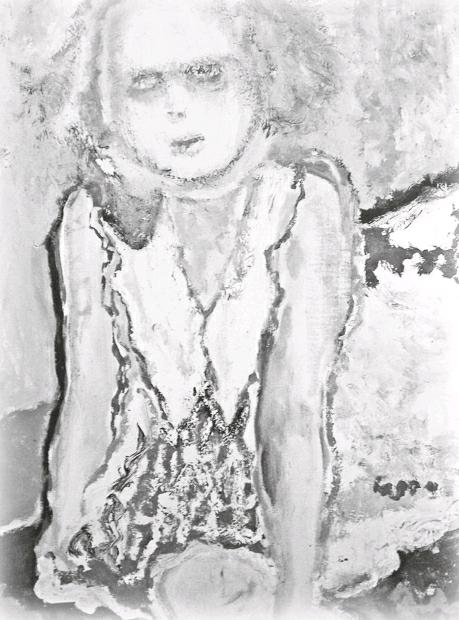
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個夢,盡管我常常在夢中驚醒。記得有人說過,如果問一個人少年,青年中年時期的理想,會是三個不同的答案。而我,現(xiàn)在和今后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想當(dāng)一名像范長江、邵飄萍一樣的記者。
多少次,我看電視,看那些主持人伶牙俐齒侃侃而談,讀報紙上來自在炮火中的阿富汗塔利班的消息,看安頓的《絕對隱私》,常常想,如果我是記者,我會用什么樣的角度來報道?
那一年,我所在的這所城市很不平常,各級電臺,電視臺,報社,都招主持人招記者,我常常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碰運(yùn)氣,從單位請假,參加這樣那樣的考試,應(yīng)該說我的條件還是不錯的,所以我屢屢沖進(jìn)決賽圈。那幾年努力的結(jié)果,就是后來我進(jìn)了一家電臺,兼職當(dāng)了一名業(yè)余主持人。在電臺里,有許多象我一樣來尋夢的青年男女。
歲月白駒過隙,一下就是三年,鐵路實(shí)行了下崗制度,我的兼職路也走到了盡頭,我從電臺辭了職。
二
我不想再兼職了,我不想身心疲憊地穿梭在兩個單位之間,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記者。
我在給省報以“新聞是什么?”命題作文之中寫道:我心目中的記者是在炮火紛飛的科索沃廢墟里,在被轟炸的阿富汗導(dǎo)彈彈坑中,在悍匪張君搶劫珍寶店的現(xiàn)場,在南方水災(zāi)現(xiàn)場一個浪頭撲過來時,一個穿著條臟兮兮的牛仔褲瘦得像蛇一樣的家伙從彈坑里爬出來,拍拍身上的土,大叫一聲:“我是記者,我來了!”
我心目中的記者絕不會為了一個紅包去吹捧一兩個庸醫(yī),美化一兩個明星的私生活,包裝一兩個暴發(fā)戶。我心目中的記者該是象羅伯特·卡帕一樣,在踩響地雷的那一瞬間按下了快門。
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差距,工作之余,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于學(xué)習(xí),在讀完了兩個大專學(xué)歷后,晚上還到師大去聽寫作課。那段時間里,我常常把自己泡在圖書館里,一呆就是一天。我讀完了十幾年的《小說月報》,當(dāng)我讀了十七歲的韓寒的《三重門》,二十歲就獲百花獎的福州女孩林瀟瀟的中篇小說《高四學(xué)生》,猶如一匹懈怠的馬兒,被人猛抽一鞭!
張愛玲說:“成名要趁早。”我何嘗不知,可是成功又談何容易!
我攢錢買來電腦,打印機(jī),攝影器材,為了一個新聞線索,我兩次跑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縣城去拍被破壞的古城墻,跑幾十里路去搶一個新聞。那段時間,是我稿件的多發(fā)期。多少次,坐在呼嘯的火車上追著時間采風(fēng)。或在夜神人靜時,獨(dú)自敲擊鍵盤到深夜;我常常想,自己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在人們的眼里,只注意成功者是最璀璨最耀眼的那顆星,又有誰會留心未到終點(diǎn)那長長的過程中又有多少追求者所付出的汗水和艱辛?
我曾經(jīng)背著我的小說稿,走在S市市莊路2號那家省城大刊物外的馬路邊,走在京都沙灘那家享有赫赫聲望的國家級大編輯部,痛苦著并且快樂著,寒酸著并且富有著,體味著路遙先生的 “孤獨(dú)可以使人崇高,困難可以使人深刻”那句話。投稿之路對于每一個文學(xué)青年來說,經(jīng)歷是令人(即使以后名垂青史的名家)難忘的,雖然我屢屢碰壁,但是我深信,不放棄終會成功。
在北京農(nóng)展館南里十號樓,我走出了中國作協(xié),我請人給我照了一張照片,背后就是誕生我們民族魂的這座建筑物。
我獨(dú)自走在長安大街上,粗曠的北風(fēng)吹著我的臉,我的懷里揣著那部帶著體溫的中篇小說,一個人久久的徘徊,只記得那年,北京的天氣很干冷……
在北京西客站,我站在西站2樓的候車廳里,向下望去,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車流動成一個燈的世界,在那么多高大的建筑物下,一個人是顯得那么的渺小……北京的夜晚,滿天繁星,北京的夜晚,燈火通明。
當(dāng)我的打印機(jī)再也擠不出一滴墨汁,當(dāng)我為郵掛號和平信在郵局里躊躇,我將小說投出去,我已經(jīng)沒有了底稿,幾天后,我收到了西北高原來自老去的那份《老區(qū)文學(xué)》的發(fā)稿通知單,信上說,他們將以最快的速度編發(fā)這篇小說。這是我發(fā)表的第二部中篇。一份普通的發(fā)稿通知單,像當(dāng)年照亮許多青年人的北斗星一樣,又燃起了我的記者夢……
三
在我的心中,有一個永久的痛……
那年冬天,省會一家大型報紙招記者編輯,我看了要求,除了全日制的大學(xué)本科學(xué)歷我沒有外,別的條件都很符合。一路考過去,最后只剩下幾個人了,最后一次是答辯,是一個一個進(jìn)去考,我是最后一個。出來的人一個個都很興奮,想必是已經(jīng)得到了什么承諾。等輪到我時,屋里只有一個人,我認(rèn)出來了,是考試時監(jiān)場的那個老師,姓何,何老師見了我,他說:“你的作品我們看了,文筆色彩飛揚(yáng),涉獵的東西也極深刻新鮮。可是,我們政審時發(fā)現(xiàn),你的學(xué)歷是兩個大專,而且還是電大和函授。”我心里一沉,心想:“壞了。”他說:“不知道你怎么領(lǐng)到了準(zhǔn)考證,交了報名費(fèi)。”我心里的希望一點(diǎn)點(diǎn)地降落。“解海龍沒有文憑照樣能進(jìn)《中國青年報》,一個姓王的女孩子小學(xué)畢業(yè)進(jìn)了武漢的《知音》雜志當(dāng)記者,你們有這氣魄嗎?”“假如我是主抓宣傳市長的兒子你們要不要?”我的一連串發(fā)問猶如機(jī)關(guān)槍似地掃射出來。
我等著他回答,如果他有一句話被我抓住把柄,我就把這里攪他個地覆天翻。
他平靜地望著我,平心靜氣地等我說完,客氣地說:“我此時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是一個很優(yōu)秀的青年,你的作品我都看了,你是這次報名者中最有爭議的一個,可是,我們也是有機(jī)制的,沒有錄取你,我本人也很遺憾。”說著,他將一個牛皮紙信封塞到我懷里,說:“我們完全可以打電話來通知你,可是我想把你的材料退還給你,也許你以后會用得著。”說著,他又從兜里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說:“我是XX部主任,以后歡迎你多投稿。”我心頭的熊熊烈火如同抽薪一般逐漸涼了下來,我接過名片,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轉(zhuǎn)身就跑下樓,我不敢抬頭,此時的我一定是淚流滿面,我不敢坐電梯,我怕我變形的臉把那些白領(lǐng)麗人嚇著。我一口氣跑下了十三層樓,人們用奇怪的表情看著我。
我一口氣跑到了民心河,扒著民心河的欄桿,我將牛皮信封里的個人簡歷,一寸照片,代表作品,作家協(xié)會會員證,電大,夜大畢業(yè)證復(fù)印件掏出來,一點(diǎn)點(diǎn)地撕碎,把他們?nèi)舆M(jìn)民心河里,十年來筆耕不輟,足跡遍布幾個省搞專題攝影,幾十篇被行內(nèi)看好的郵市評論,二十幾歲就發(fā)表包括兩部中篇的三十萬字的作品,所有這些,都抵不過這一紙“全日制以上的大專文憑”。
那是我求職路上最刻骨銘心的一次,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向那家報紙投過一篇小稿,這也許是我一切虛榮,所有面子都摒棄以后,唯一放不下的一點(diǎn)點(diǎn)傲骨。而那個XX部主任的名片,我直到現(xiàn)在還珍藏著,他的名字叫何振兵。
世紀(jì)初羊年年底,某報將我們這些“筆桿子槍桿子”召集到一起,要我們各拍一個反映新世紀(jì)的圖片,我拍攝的題材是新世紀(jì)的第一縷陽光,我獨(dú)上高樓,支好三腳架,凍了一個多小時,等來了紅彤彤的太陽,當(dāng)新世紀(jì)的第一縷陽光灑到我臉上時,我禁不住已是淚流滿面,“太陽啊,太陽總是新的!”我默默地吟嘆著古希臘哲學(xué)家赫拉克利特的這句名言,心里是那樣的激動,太陽啊,這個圓圓的魔術(shù)師,你是多么公平,多么慷慨,人們對太陽的膜拜如同朝圣般,用身體去丈量自己的行程。當(dāng)我們終于明白,那些風(fēng)花雪月的故事遠(yuǎn)不如柴米油鹽更實(shí)際;天上美麗的風(fēng)箏一旦脫離了地上這根線就會飛得無影無蹤,還有一年,我就要到而立之年了,我心中的那個夢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jīng)越來越遠(yuǎn)了,當(dāng)我照鏡子時,發(fā)現(xiàn)鏡子中那張臉是那么的憔悴,逝去的不僅僅是歲月,還有詩一樣的青春和火一般的激情。不知道,我心中的那個夢,今生今世,能否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