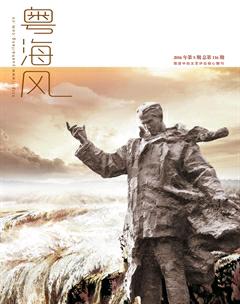“受眾”,還是“讀者”
李伯勇
一
作家陳應松在《文學興盛的可能向度》(《上海文學》09年第11期)說:文學的興盛取決于每個讀者閱讀水平的上升——對藝術更加挑剔,口味更加“刁鉆”,對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對時代保持更加清醒、冷靜和警惕。有什么樣的讀者,就有什么樣的文學。文學不僅在紙面上,更在讀者心里……閱讀就像寫作一樣,是一種創造行為。
這是側重讀者角度的。在我看來,“有什么樣的讀者,就有什么樣的文學”與“每個讀者閱讀水平的上升”之間不總是呈現正面的促進關系,而存在前者與后者在文學接受上的不同步,不是前者有效地提升后者,倒是前者拖扯并消解后者(所謂劣幣驅逐良幣),這正是國人的精神素質難以提升的一個原因,此種現象在中國存在已久矣。也就是說積極的閱讀(少數)往往被被動的讀者(多數)所腐蝕——積極閱讀淹沒于被動閱讀的汪洋大海,而不能有效地擴展,化為具有一定覆蓋的社會精神氣象。這“多數”恰恰是市場化(更是今天的市場化)所倚重的。整個社會忽視了真正的創作(文學)對讀者閱讀水平上的重要提升作用,那種真正閱讀的“創造行為”就不會出現,也就沒有國民精神素質整體性的提升,當然不能有力地推動真正的創作,真正的創作經常性地陷入落寞的境地。因而在中國語境中,有必要對“讀者”進行分析。
我以為,“每個讀者閱讀水平的上升”屬于真正閱讀意義上的“讀者”,而“有什么樣的讀者,就有什么樣的文學”的讀者只是“受眾”,前者呈一種動態,一種主動——能動的姿態,而后者更呈一種靜態,一種受制于單方面宣示——被動的狀態。中國的文學接受也就分為“讀者”和“受眾”這樣兩個層面。所謂“讀者”就細化為讀者和受眾,受眾就是只接受來自一個方向的訓誡熏陶,自身并不質疑,屬于單方面接受的人,而讀者則是能與閱讀對象雙向交流的人,但讀者不是鐵板一塊,讀者來自受眾,但不等同于受眾,而受眾是非積極意義上的讀者。這或許是中國文化情境的一個特色。由于習慣和官方準許,自然有為“受眾”即市場化的創作。
所幸陳文后來似乎意識到應該有所補充:“本文中所指的文學正是純文學和精英文學,造成其深遠魅力和影響力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它堅持的價值觀,它與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系等,是通俗小說、武俠小說、網絡小說和青春文學望塵莫及的。它的思考,它的責任感、道義感,以及對現實生活的追問力量和藝術的隱喻力量是鶴立雞群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語言的神奇性,精煉,創造力。”陳文力圖呼喚真正的閱讀——培養“讀者群”——的況味非常明顯,可也不自覺揭示了依傍通俗小說、武俠小說、網絡小說和青春文學的“受眾”的廣泛存在。我更加意識到陳文中包含文學的讀者和受眾——兩個必須區別但沒有區別的概念。
于是陳文權當引發我思索的引子,把中國語境中的“讀者”和“受眾”再做一番甄別。
二
這里我把能夠進行文字閱讀的人(受眾)視為“讀者”,把看戲聽故事聽傳聞流言視為“受眾”,人一出生就是個受眾,受眾是“汪洋大海”。比如“中國人此類(黃)段子的流傳,其受眾之多”中的受眾一詞就用得恰當。顯然有些“受眾”會轉為“讀者”——他們直接閱讀相關作品,又擴展為閱讀其他文學作品,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因此涵養而成。沒有文字閱讀,精神難以扎根。我們也就明白,中國是充斥“受眾”卻缺乏“讀者”的國度。一是能識字的人很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二是長期的專制統治,閉關鎖國,國人可以看(讀)什么不可以看什么有嚴格的規定,于是有什么讀什么——讀也是為了受教育——成為不成文的傳統,“受眾”的隊伍非常龐大;三是“受眾”易接受并滿足于低層次感官刺激——過一把癮;四是“讀者”中不少人從現實利益出發,名義上是閱讀,皓首窮經,其實是想做帝王師,闡述帝王術,他們自身的精神素質局限于一個低水平,經由他們傳經授道的人大多數是“受眾”。
只有在開放的情境中,才能激活“讀者”,“讀者”的隊伍(圈子或“部落”)才能壯大,才能激活個人和民族的精神,才能涵養并體現一個時代的思想精神水平。從文字閱讀層面,這種“開放”是隨時存在的。以古代的閱讀為例,格非說:“在中國古典小說自寫作至被閱讀的過程中,評點者既是讀者,也是批評者,同時就……具備了作者的功能——這不僅僅是由于評點者提供了次文本或準文本,同時也會對作者的文字、回目進行編刪和修改,以體現自己的意圖。對于一個讀者而言,他所面對的文本不是單純的作者正文,既有評點者的次文本,也有許多無名作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這就構成了全新的對話關系。……讀者在與作者對話的過程中,實際上也在與不同時代的讀者同時進行對話,這也使得閱讀變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共時性行為……”(《作者與準文本》,載《花城》2009年第6期)可見,真正意義上的讀者是不多的,而大多數人只能是受眾。
從這個角度,“讀者”既是個傳統也是個現代的概念。自紙質媒體(書報)的普及,大量“讀者”應運而生。大量的“讀者”是推進全球化——人類文明的決定性力量。
不錯,讀者閱讀水平在上升,它建立在讀者的社會感受——社會現象思考的基礎上,閱讀能強化并提升社會感受和思考,是社會重要的精神生活。有各式各樣的書籍雜志(包括思想和生活雜志)供讀者閱讀,許多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之前已經具備了開放的精神結構。為什么還要讀現時的文學作品?這是由于文學本身所承擔的對時代社會思想精神揚棄的獨特功能,它是人類文明延續并發展的一個基本“器官”(之一),人類的情感、精神和當代性思考能在個人化表達的文學上得到最為客觀全面而準確的、富有歷史感的表達,當然它還是鮮活的民族情感與精神的象征。當年諾貝爾設文學獎是有道理的,而且百年來世界文學的發展給諾獎不斷注入生機,它才可能確立公信力,具有全世界的廣泛影響。人類需要創新——不斷認識自己發掘自己以適應新時代新環境的創新,這樣的精神方式(情感和審美及思考)通過具有獨創性的作家來顯現,就是說作家承擔了這一職責。作家把人類的、民族的心聲化為藝術形象,通過自己獨特的感受和表達——創作奉獻給社會,同時也是作家自己跟社會的思考方式和對話方式。這種獨特性也包括前沿性——正是人類豐富想象力的體現。這樣的創作(作家)既適應了讀者,也超越了讀者,也就是提升了讀者的閱讀水平——精神境界。這里,具有獨創性的作品必定能培養自己的讀者,不是作品適應讀者,而是作品提升讀者。
讀者與作品有機地互動,是文明社會有著很高價值的精神活動。
當年魯迅的讀者以居住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他們與全中國民眾相比只是極小的一部分,但他們感受并選擇了魯迅的價值觀審美觀,成了有力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精英,他們是“讀者”。可是,在中國鄉村的汪洋大海中——就是在中國城市里,更多的人在陳舊的忠奸戲因果戲武打戲通俗小說里“樂不思蜀”,并沒有產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的詰問,精神繼續麻木。當然,他們享受了娛樂和精神的放松。從精神含量高的文學接受角度,從改變原有生活創造嶄新生活角度,他們只是“受眾”。“受眾”就是你給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只要能娛樂就行,跟你給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只要能填飽肚子一個意思。就說京戲的票友,他們對京戲人物和場景的“技術性”批評很到位,但他們提不出超出原著的思想認識,所以他們依然是受眾。聯系傳統中國說教文化的興盛和官方的有意引導這一“國情”,我們也就應該承認“受眾”大于“讀者”這一習焉不察的社會現實和精神現實。
這等于說,雖有“受眾”但缺“讀者”,在許多年代只見“受眾”而鮮有“讀者”。受眾不等于讀者,由一般受眾到成為真正讀者必須歷經一個精神過程,而且要有相應的社會條件(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生態)。受眾可能永遠是受眾,但由受眾而進入讀者行列的人很難再返回受眾之中,他可以對作品失望和不滿,卻不會退回再欣賞那些說教的通俗作品中。當然也有屈從于自身利益考量的作家,乖巧地違心創作符合某政治集團利益的作品,其實他們內心是知道什么是真正好作品的,但在客觀上,這樣作家心目中的讀者仍是受眾。
在商品化市場化欲望化成為主流生活的當今中國,讀者為什么會更挑剔?實際上自20世紀初年中國進入現代,外國現代文學傳入(同時傳入還有革命思想,“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中國開始融入世界,就產生了挑剔的讀者——讀者也就更挑剔了。換言之,富有思想精神氣息的西方文學(包括日本文學)激發或創造了中國的現代讀者。有了這樣富有精神新質的文學參照,加上陳舊窒息的傳統生活的反向刺激,以及有活力的文學本質在于創新,“更挑剔”的讀者出現了。跟“受眾”有“受眾”的文化傳統一樣,現代意味的“讀者”也會形成“讀者”的精神傳統而薪火相傳。這種薪火相傳經歷了閉關鎖國時段而步入了今天的擁抱世界的新階段,同樣受社會狀態和國外(包括非洲拉丁美洲)現代文學的雙重激發,他們不滿意現有的讀物——當然包括許多作家寫的一般化的東西,他們是基于精神需要發出種種挑剔之聲。
其實,上面所說的“讀者”,當包括作家自己,指思想精神層次較高的那一部分閱讀者,而不僅僅指全部的閱讀人。要知道,現在對皇權官場戀戀不舍津津樂道的讀者不在少數,于是適應如此讀者的創作也就應運而生。也就是我們必須正視“受眾”依然大量存在的社會現實。在表面上,這類讀者也是挑剔的,此類作品淺層次地逗人一樂一笑,或高雅地逗人一樂一笑,那是“受眾”的挑剔,跟前面所說的挑剔不能相提并論。
所以,真正的創作,作家心中當然有讀者,他也面對讀者,但他心目中的讀者絕不是那些與他的精神層次相差甚遠的寬泛意義上的讀者,即受眾,他在寫作的時候,第一個讀者就是他自己,他想象的讀者是跟自己精神同步的讀者。當然他希望讀他作品的讀者越多越好,可是他寫作絕不是建立在有可觀的讀者數量的基礎上的,他心目中的讀者與他自己的精神同構,他可以設想有很多,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可能是極少數。由“極少數”到“相當數量”,說明在眾多受眾里有一批或快或慢地轉變為讀者的可能。
于是我們進入了文學受眾與文學讀者關系的更深層次。
三
在現代條件下,比如一個從小生活在鄉村環境后來來到城市的讀書人,他早就是文學受眾,后來因接觸現代文學而向現代讀者轉化。這樣的轉化者其實很少,但存在著由小圈子讀者擴展為大圈子讀者的可能。即使是一個小圈子,卻顯示了民族的精神方向。
可是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延安文學模式”(延安體)楔入(干擾)了這一民族性的精神歷程。
李潔非、楊劼在《延安的藝術變革·舊形式的利用和改造》說:秧歌劇、秦腔、評劇、章回小說等,在我們的手里正在發展為不論在語言和表現手法上,都有創造的民族新形式(陳涌語),這就是“延安體”最清晰的描繪,它“在未來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支配著中國文藝的面貌”,“作為一種即將取得文化領導權的政黨意識形態,‘延安體不動聲色地大量置換了民間形式的話語,充分利用語言能指的模糊性,將其語義指向政黨意識形態,同時,馬克思主義文藝體系獨特的‘組織化架構也適時地發揮其整合作用,使民間形式與民間文化的固有傳統相剝離,轉而成為特定政治集團的精神的代言體。”“原先民謠中許多用于神靈崇拜的意象和表達方式,被轉化為歌頌革命、黨及其領袖的話語;許多源于男歡女愛的情詞,也悄悄指向階級之愛、同志之愛以及革命理想的歡愉。秧歌形式所內含的民間野性與放縱,經過一番能指的調整,被解釋為對革命勝利及解放的憧憬和感恩。章回小說的神魔好漢故事模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奇化講述形式,則被橫移到革命史和革命英雄主義的敘事上。《白毛女》就是極好的例子。”(《小說評論》2009年第三期)
沿著《白毛女》路子走來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艷陽天》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紅色文學,自然也創造出一代讀者。從精神建構的意義來衡量,它強化的階級斗爭思想——人的階級性斗爭性高于人性和人情,恰恰與現代民主自由精神相背離,它自己也窮途末路,成了極“左”政治的單純演繹(如《金光大道》),它教導人用怎樣的手段實現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理想”。那時作為學生的讀者,我們只能在政治意識形態語境(包括各種報刊和學校的政治教育)中——非原生態生活,即偽裝的現實中去感受,讓自己的心靈與小說中的正面人物相呼應,因而我們這些“讀者”其實也是受眾。
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人”的解放號角再次響起,有更強勁人文——人類精神的現代作品做參照,其“讀者”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向真正的現代讀者轉化,不可能如陳應松所說,出現“對藝術更加挑剔,口味更加刁鉆,對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對時代保持更加清醒、冷靜和警惕”的讀者,而大多數與這類作品無緣的農民(國民),依然是受眾,甚至比傳統中國的受眾更加低俗而封閉。
應該看到,此類創作排斥市場經濟,強化了一般民眾與市場思維不相吻合的思維(如無商不奸,經商等同于剝削),縱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也蔑視資本主義(資本家),把后者視為要解放要占領要改造的對象。此類創作不如說是政治宣傳,培養了新的大量的“受眾”。
不過幾年工夫,連主流媒體都攆著干部民眾撲進市場的大海了,“群眾需要”“市場需要”堂而皇之地成了我們的主流意識。
文學之于讀者,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沒有讀者就沒有文學,沒有文學也就沒有讀者,這好像是個平白易懂的常識。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加速市場化以來,主流媒體把“市場”成敗定為衡量一項工作(事業)的重要標準,文藝(文學和影視等)把“讀者”多寡納入自己取得效益(成功)的重要考慮因素。也就是文學去掉自己身上神圣的光環(如啟蒙),在商品世界中文學也只是一件可用錢衡量用錢交換的“物品”,猶如宮廷貴婦下嫁給市井的俗人,雖存尷尬,但無可奈何,只有適應市井生活。拿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就是到人民群眾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實現社會和經濟雙效益。諸多作家也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碼字匠”——社會百行中的普通一行,“做鞋(作協)”“作為老百姓一員寫作”,以不乏自我貶損的姿態來適應精英文學的失落——文學的市場化轉換。
轉眼到了新千年第一個十年的末尾,政體依然,文學面向市場的態勢依然,文藝向著符合人民“意愿”的方向,也有輝煌的成果,比如張藝謀的“英雄”“黃金甲”,據說創造了可觀的市場效益,民眾滿意,張藝謀們口袋要賺破了。這就是文藝適應市場、適應讀者的典范!
從接受美學角度,在現代轉型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受眾并沒有轉為“讀者”,而是轉為另一種被急切進行政治意識形態宣教的“受眾”,連傳統戲劇中的人情趣味也蕩然無存。“受眾”因物質生活極度貧乏而具有的對物質和富饒生活的追求壓在心靈深處。如果說,傳統戲劇的因果報應和大團圓尚能給予傳統的受眾以廉價的心靈撫慰,那么,“三突出”作品中只有革命情操的正面人物只能讓受眾滋長權勢思想——唬人的豪言壯語,只會加倍破壞與腐蝕人性和人情。不管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如當時的學生我)在讀書筆記或作文中如何情感激蕩,仍是受眾的角色,或者說撐著“讀者”面孔的受眾。如此天生不足的受眾構成今天的精神環境,使現代讀者成為中國蔚為大觀的精神氣象而顯得中氣不足。
民眾求財求富之心一旦釋放,財富——市場力量催生出一種讓文學受眾做新時代受眾的魔力。
我們會明白,中國社會老是有一股強大的、難以抵御的不是將文學受眾向現代讀者轉化,而是將文學受眾定位于“受眾”的習慣性力量。
四
仔細琢磨,官方確有讓市場來接手每每招來麻煩和拖累的文藝(文學)的考慮,不過它更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被市場消解(拋棄)的擔憂,于是成功地改造了張藝謀——張藝謀不再是拍《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那個張藝謀(張正是憑此獲得了國際名聲),而是獲得了市場極大成功的張藝謀,張藝謀成了中國文藝走向市場的成功典范。其實,誰都明白,張藝謀的所謂成功是,在國際先是以“中國叛逆者”出現,在國內很快洗心革面,憑借官方提供的排他性的優越條件和環境,狠狠地大撈了一把,張藝謀在貌似市場經濟的“市場”,鼓吹的仍是皇權政治或皇權文化。皇權文化就是可操控文化。只要在主流政治的統制之下,文學(文藝)也好,房地產也好,別的什么經營也好,你即使用潛規則賺個盆滿缽滿決不會出事。這是中國市場化的一個特征或一個秘密。文學市場化同樣如此。
從文學(文藝)市場化的實際情形來看,是跛腳的,顯而易見的偏向是,一是消遣性娛樂性怪異性(包括形式上的先鋒)的作品大量涌現。這在中國,固然有市場(讀者)的因素——市場解放了人性但同時也滋長了人性耽于享樂的惰力,恐怕也是皇權政治高壓下的一種必然,社會的精神之流被攆趕或被誘導匯入這個方向,其不與主流政治產生沖突則是肯定的,也就可以判定,此類作品除了包裹善惡因果報應、官場權謀、姑嫂斗技的“思想”,欠缺向著未來敞開的,富有健康精神質素的思想精神品位。與作者相比,普通民眾只能看這樣的作品(戲劇)。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其精神需求也不可能高,即使有那么一點精神需求想在閱讀中得到提升,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國式受眾的思想精神基質也就形成或強化了。
二是貫徹主流意識形態也即叫讀者受教育的作品大量涌現。這當然是官方的提倡和扶持,作者心里“識數”做出程度不等的妥協與順應。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是;對許多作家來說更有著來自內心的積極性,為什么?因為創作屬于“立功立言立德”的神圣之事,著書人在民間有很高的聲譽,況且有相當的難度,需要天才和豐富的學識,不是哪一個人說寫就能寫成功的,作家心里自然有這樣的情結。更何況,人一生只有在年輕或盛年方能爆發創作靈感和激情,寫作是自我實現的最好方式。因此,對相當多作家來說,與其沉默不寫空耗光陰,不如在察言觀色中進行創作,獲取名利——向名利急劇傾斜。現實中不是有許多得這獎那獎的作家做了相當級別的行政官員么?自然,這樣的創作因在某種程度具備人文氣息也能夠創造出相應的讀者,就是說,這樣的作家仍有一定的人文精神涵養。不過,實際上這類作品的讀者并不多,外在的宣傳熱烈而真正的讀者寥寥,也可以說,連“受眾”也是潛在的,因為此受眾非彼受眾也,受眾同樣需要變換口味呢。
上述兩點其實包含著文學“受眾”與文學“讀者”的聯系和區別。加上前面說的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受眾”傳統根深蒂固——在讀書人極少的古代,有幾人是能夠讀“書”的人?大多數是在茶樓酒肆戲臺上聽聽而已,在敬佩與仰慕、惋惜與嘆息中接受了正統文化的思想和趣味,如果說有質疑和爭論,那只是“火燒赤壁到底燒了曹操四十萬還是八十萬”的意氣之爭,決不會上升為“天道”與“人道”(世道)之爭,說他們是受眾倒是恰如其分。
在社會發展或慢或快的年代,“受眾”前后會有不同(比如清朝的受眾就不同于唐朝的受眾,21世紀的受眾不同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受眾),但總的來說受眾隊伍是穩定的,就是說社會上大量存在“給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的人群,所以“受眾”也就大于“讀者”,講究忠奸善惡的《說唐演義》《七俠五義》《平山冷燕》一類典籍在民間長盛不衰。“受眾”就是與最寬泛的文化形態(包括說書、戲劇、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習俗、意識形態宣教)呼吸與共的民眾(當然包括各種官員),而“讀者”就是自覺不自覺接受某類讀物的人(自然也含各種官員)。“讀者”一定先是“受眾”,“受眾”卻不一定是“讀者”,只可以說是潛在的讀者。也可以說,“受眾”是在某個歷史時段,在傳統文化的土壤加上政治意識形態及文藝趣味的牽引,所形成的接受者群體,或者說普泛性審美接受心理的顯現。
當今時代應該是“讀者”大量涌現和成長——大量的“受眾”轉變為“讀者的年代,而我們的情形恰恰相反,“受眾”不斷壯大,“讀者”卻成不了“氣候”,顯然不利于民族和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型。
五
富有思想精神力量的文學雖是曲高和寡,即使生產(寫作)和出版都非常艱難,但它的品性和品位均為作家們所認可,即使在其他如通俗小說、武俠小說、網絡小說和青春文學中,也都程度不等地流淌著現代精神的汁液(如金庸的武俠小說),“受眾”有向“讀者”轉身的可能。這樣的轉身經常發生,由此見證前者與后者的互動。不過這樣的“轉身”并非易事,完成如此轉身猶如“杯水車薪”——靠一部幾部的好作品來提升大面積的受眾顯然不現實,遠不如直接做純文學和精英文學的讀者收獲的多,得到的精神滋養大。所以,“有什么樣的讀者,就有什么樣的文學”就包含著“受眾——讀者”與“受眾——受眾”的雙重命題。
所幸,我們時代已經涌現了不少有思想精神追求的作家,用陳應松的話就是,“對當下文學狀況盲目的悲觀和樂觀都沒有用,唯一要緊的是創作出具有品質追求,符合歷史召喚,與整個時代保持親和力,也保持一點緊張關系的作品。”如前所述,作家創作的第一讀者即靠得住忠實的讀者就是作家本人,加上互聯網時代信息的通暢,由“這一點”會形成或大或小的讀者圈,再向“受眾”漫漶,這就是社會的回報。這是有著較高品質的作品向社會流散的一般情形。
要是從社會生態角度,我們容易發現,海外(外國)對于一部有著真正品質的作品,很快會被獨立知識分子組成的評介網絡(比如有獎金或零獎金的什么獎)推波助瀾,在短時間內許多“受眾”轉為了“讀者”。即使互聯網時代,一部好作品一部好電影都能得到不菲的市場回報,發行十幾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冊的事屢見不鮮,從如此熱情的“讀者”(并不是公款買單),就可以得知這個國度建立在健全個人心智基礎上的精神活力。而我們國內,就缺少這樣的機制,除個別的媒介向這方向拓展,大多媒介要不先瞪官方的眼色,要不計算著可能的“推銷”效益(包括收買有影響力的學者),一部純文學作品能有上萬的銷售就不錯了。聯系我們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發行量與其說是作家的悲哀,還不如說是精神的憋悶——社會的悲哀。換言之,包括媒介,是甘心把自己置于“受眾”的狀態啊。
所以,不但作家需要“讀者”,我們整個社會同樣需要“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