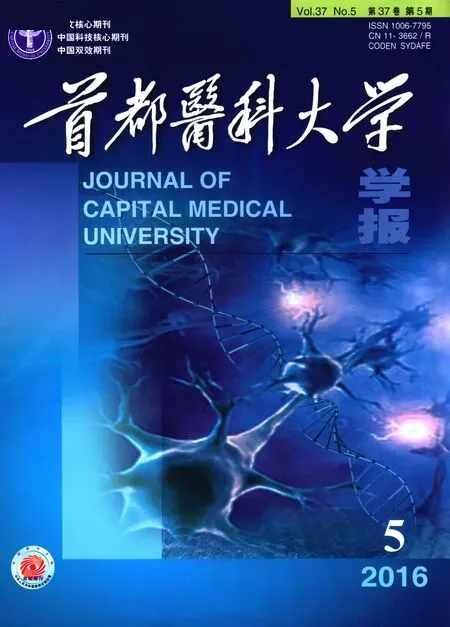2016年拉斯克獎
李禹正 張 婷 王曉民,3*
(1.首都醫(yī)科大學基礎醫(yī)學院長學制臨床醫(yī)學專業(yè), 北京 100069;2.首都醫(yī)科大學基礎醫(y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 北京 100069;3.北京腦重大疾病研究院, 北京 100069)
?
· 拉斯克獎 ·
2016年拉斯克獎
李禹正1張婷2王曉民2,3*
(1.首都醫(yī)科大學基礎醫(yī)學院長學制臨床醫(yī)學專業(yè), 北京 100069;2.首都醫(yī)科大學基礎醫(y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 北京 100069;3.北京腦重大疾病研究院, 北京 100069)
北京時間2016年9月13日,拉斯克獎獲獎者名單公布。基礎醫(yī)學獎頒發(fā)給William G. Kaelin, Jr.、 Peter J. Ratcliffe以及Gregg L. Semenza,以表彰他們發(fā)現了人體和大多數動物細胞感知和適應氧氣變化機制。臨床醫(yī)學研究獎頒發(fā)給Ralf F. W. Bartenschlager、 Charles M. Rice以及Michael J. Sofia,以表彰他們對丙型肝炎的“復制子”系統的研究及藥物的研發(fā)。特殊貢獻獎頒發(fā)給Bruce M. Alberts,以表彰他在DNA復制和蛋白質生化研究方面的發(fā)現,在國家和國際科研機構中為改善人類生活而展現出的富有遠見的領導力,以及在改進科學和教育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拉斯克獎;HIF-1;丙型肝炎病毒;DNA復制
拉斯克獎(Lasker Awards)是美國最具聲望的生物醫(yī)學獎項,現由基礎醫(yī)學研究獎、臨床醫(yī)學研究獎、以及特殊貢獻獎3個獎項組成。1945年,Albert Lasker和Mary Woodard Lasker夫婦共同捐資在紐約創(chuàng)設拉斯克基金會(Lasker Foundation,全稱 Albert and Mary Lasker Foundation),其目標是通過醫(yī)學研究建立起一個健康的世界。拉斯克獎旨在表彰醫(yī)學研究、公共服務和教育領域的杰出成就,以加快醫(yī)學研究進步,增進人類健康水平。因拉斯克獎得主獲獎后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比例很高,因此有“諾貝爾獎的風向標”之稱。1946年至2015年,拉斯克獎共頒發(fā)過67屆,共有372人次獲獎,其中諾貝爾獎得主共89人次,占23.67%[1]。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因發(fā)現青蒿素于2011年摘取“拉斯克臨床醫(yī)學研究獎”桂冠,2015年成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1 基礎醫(yī)學獎[2]
2016年拉斯克基礎醫(yī)學研究獎獲得者為哈佛醫(yī)學院達納-法伯癌癥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William G. Kaelin, Jr.(圖1),牛津大學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University of Oxford/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Peter J. Ratcliffe(圖2)以及約翰霍普金斯醫(yī)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Gregg L. Semenza(圖3),他們發(fā)現了對人類及大多數動物存活至關重要的一個過程——細胞感知并適應氧氣變化的分子機制。人類及動物依靠氧氣來維持生命,但體內過多的氧氣也會產生危害,為了應對周圍環(huán)境中氧氣含量的不斷變化,生物體內進化出一套完善的機制來優(yōu)化機體的氧氣供給。長期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依賴氧氣生存的生物存活的 “秘訣”,但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William G. Kaelin, Jr., Peter J. Ratcliffe以及 Gregg L. Semenza 通過描述核心的分子事件,解釋了幾乎所有多細胞生物應對氧氣含量變化的調節(jié)方法,揭示了其獨特的信號機制。

圖1 William G. Kaelin, Jr. [2]

圖2 Peter J. Ratcliffe[2]

圖3 Gregg L. Semenza[2]
1.1初期探索:HIF-1的發(fā)現與分離
20世紀90年代早期,Semenza 和 Ratcliffe嘗試解釋低氧誘導紅細胞生成素基因表達的機制。他們發(fā)現基因組中的一段DNA序列對感知低氧至關重要。Semenza發(fā)現,在低氧條件下,一種核內蛋白質會出核與這一段DNA序列相結合,進而將這一蛋白質命名為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 (HIF-1)。當HIF-1無法結合到DNA上時,低氧誘導的基因表達也會消失。Semenza推測,低氧時HIF-1會結合到DNA序列上,進而啟動鄰近基因表達。1995年,Semenza和他的博士后Wang在實驗室中純化了HIF-1蛋白,并發(fā)現它包含HIF-1α和HIF-1β兩個亞基。其中,HIF-1α是從人源細胞中分離出來。當Semenza把細胞從低氧環(huán)境快速轉移到高氧環(huán)境時,HIF-1α很快消失[3]。
1.2顛覆舊識:各種細胞內均存在HIF-1結合的靶基因
成人的紅細胞生成素主要是由腎臟細胞產生,因此,長期以來,科學家們一直認為這種應對氧氣含量的調節(jié)機制只單純存在于腎臟細胞中。隨著HIF-1及其所結合DNA序列的發(fā)現,Ratcliffe 和Semenza顛覆了這一觀點。Semenza 和Ratcliffe逐步發(fā)現低氧會促使大多數哺乳動物細胞(包括一些不能產生紅細胞生成素的細胞)利用HIF-1激活特定基因的表達[4-6]。例如,1996年,Semenza證明HIF-1激活了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的表達,其在血管的形成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1.3揭示機制:高氧條件下,VHL與HIF-1α結合導致其泛素化降解
一種家族遺傳性腫瘤——VHL病(von Hippel-Lindau disease)的病因是特定蛋白的變異。William Kaelin初期的研究內容是該特定蛋白——VHL蛋白在疾病中發(fā)生了怎樣的改變。經典的VHL病表現為異常的血管生成、VEGF過表達以及紅細胞生成素過剩。于是Kaelin推測VHL蛋白影響了低氧誘導表達的基因[7]。1996年,Kaelin和同事在實驗室中培養(yǎng)正常或VHL缺失細胞,檢測了與低氧有關的包括VEGF在內的多種mRNA的含量,發(fā)現即使在高氧環(huán)境下,缺乏VHL的細胞仍大量表達低氧相關mRNA,而再次加入VHL后這一現象消失[8]。Kaelin隨后發(fā)現,高氧條件下,VHL可以通過與特定蛋白(包括泛素)結合,泛素會將蛋白質引向相應的蛋白酶體進而導致其降解,最終使上述mRNA含量降低。在高氧條件下,HIF-1α正是通過泛素-蛋白酶體系統降解。1999年,Ratcliffe及其同事再次證明了這一發(fā)現。Kaelin隨后發(fā)現,VHL與HIF-1α的直接結合需要利用HIF-1α的一個特殊結構域,該結構域是高氧誘導其降解時所需要的。Ratcliffe等隨即證明該結構域可以與泛素結合。綜上所述,高氧條件下,VHL會引起HIF-1α的泛素化降解。
1.4挖掘本質:脯氨酸在氧氣存在時可以使HIF-1α羥基化從而被VHL識別
此后,Ratcliffe和Kaelin都把研究重點放在了HIF-1α與VHL結合的機制。2個研究小組通過沉默掉該結構域的一個氨基酸——脯氨酸,發(fā)現VHL喪失了與泛素結合的功能,從而保護了HIF-1不被降解。脯氨酸在氫鍵旁攝取一個氧原子使HIF-1α獲得一個羥基化修飾。進一步的研究揭示了兩者的結合原理,一種脯氨酸羥化酶為HIF-1α的一個特定脯氨酸加入一個羥基,使HIF-1α能夠被VHL識別并最終導致HIF-1α失活。這項研究于2001年發(fā)表。因為脯氨酸羥化酶需要氧分子才能發(fā)揮作用,因此該研究解釋了HIF-1α在低氧條件下不被降解的原因,以及酶是如何將氧氣含量轉化為HIF-1α的穩(wěn)定性[9](圖4)。通過與Christopher Schofield(牛津大學)的合作,Ratcliffe提出這種脯氨酸羥化酶屬于一個較大的分子家族。Ratcliffe和Steven McKnight(德州西南醫(yī)學中心)分別獨立地鑒定出3種哺乳動物體內控制細胞應對氧氣含量變化的脯氨酸羥化酶。Ratcliffe隨后發(fā)現HIF-1α中其他脯氨酸的羥基化也會促進其氧氣依賴的VHL介導的降解。不久后,科學家們發(fā)現,其他氨基酸的羥基化也會抑制HIF-1α,但機制不同。
1.5臨床應用
基于科學家們數十年的研究成果,目前HIF通路正被逐步應用于臨床。例如,脯氨酸羥化酶抑制劑可以使HIF-1免于降解,從而促進紅細胞生成素的表達,低氧條件下(左圖),HIF-1(包括HIF-1α和HIF-1β)完整進入細胞核,激活紅細胞生成素、VEGF及其他蛋白的表達,促進機體適應低氧環(huán)境。高氧條件下(右圖),脯氨酸羥化酶利用氧氣使HIF-1α羥基化,進而使其被VHL標記并最終導致HIF-1α泛素化,被相應的蛋白酶體降解。當HIF-1敲除后,低氧誘導基因無法表達。

圖4 氧氣調節(jié)HIF-1穩(wěn)定性的機制[2]
以此來治療貧血癥。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均已證實這一理論的可行性,一些公司也已經開始以此為依據研發(fā)藥品;鑒于HIF-1α脯氨酸的羥基化也可以促進血管生長,這一原理同樣可以用來治療一些心血管疾病;大多數腫瘤是通過血管的增生來獲取營養(yǎng)的,基于這一點,科學家們可以利用HIF來治療一些惡性腫瘤。目前一種HIF-1α的類似物正用于治療腎癌的初期臨床試驗中。
2 臨床醫(yī)學研究獎[2]
2016年拉斯克臨床醫(yī)學研究獎獲得者為海德堡大學的Ralf F. W. Bartenschlager(圖5),洛克菲勒大學的Charles M. Rice(圖6)以及Arbutus生物制藥公司的Michael J. Sofia(曾就職于Pharmasset公司)(圖7),他們發(fā)現了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的復制機制,并對治療這種致命性慢性疾病的方法進行革新。在全球范圍內,每年約1.3~1.7億人感染HCV,35萬人死亡。目前為止,沒有針對HCV的疫苗,感染后如果無法得到有效的治療,15%~30%的患者病情惡化,最終導致肝衰竭或肝癌。傳統的治療方法需要持續(xù)注射24~72周干擾素,其不良反應巨大,并且通常以失敗告終,很多患者因無法耐受而中斷了治療。Bartenschlager、Rice以及Sofia的發(fā)現,有效克服了這一問題。

圖5 Ralf F. W. Bartenschlager[2]

圖6 Charles M. Rice [2]

圖7 Michael J. Sofia[2]
2.1出師不利:HCV從發(fā)現到體外復制
研制針對某種病毒性疾病的藥物的先決條件是在人源宿主細胞中繁殖這種病毒。1989年,Houghton等分離出HCV病毒,他因此獲得了2000年拉斯克臨床醫(yī)學獎[10]。隨后,科學家們試圖利用DNA重組技術制備HCV的RNA。導入宿主細胞后,科學家們希望能產生感染性HCV。然而,這種常規(guī)方法并沒有幫助科學家們實現HCV的復制。就在科學家們不斷嘗試用各種方法促進HCV在細胞內復制時,一些科學家終于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他們可能并沒有得到HCV完整的RNA序列。1996年,Rice和他的博士后Kolykhalov用特殊技術提取到完整的RNA,在其3′末端非翻譯區(qū)發(fā)現了一段特殊片段,之前從未有人報道過[11]。與此同時,科學家Shimotohno也報道了這一發(fā)現[12]。在隨后的試驗中證實,前期的實驗之所以不能復制產生完整的RNA序列是因為這些病毒本身已經缺失了這一重要片段。Rice認為自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當他把一系列含有該片段的HCV注入黑猩猩體內時,這些黑猩猩并沒有像他預計的一樣表現出丙型肝炎(以下簡稱丙肝)的癥狀。Rice在隨后更深入的研究中發(fā)現了原因——在HCV感染人體并進行繁殖時,它的RNA需要發(fā)生序列改變。這些改變削弱了HCV的復制能力。于是,Rice制備出一種“一致性”基因組。1997年,Rice等[13]和Bukh等[14](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 分別發(fā)表文章報道了這種人工制造的RNA使黑猩猩感染了丙肝。至此,科學家們終于可以成功在實驗室中繁殖HCV病毒,由此為HCV病毒的研究與防治打開了新的篇章。
2.2邁向成功:HCV的檢測
與此同時,Bartenschlager(當時在美因茨大學)制備出另一種不同的HCV一致性序列。他將其導入各種宿主肝細胞,但無法檢測病毒的復制。應用Rice的RNA也是這樣。考慮到HCV在缺失一段編碼病毒包裝蛋白的基因組序列后,仍然能夠在宿主細胞內復制,Bartenschlager將這一段序列用一段遺傳標記代替,這樣被病毒感染的細胞就可以被檢測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Bartenschlager及其博士后Volker Lohmann在HCV的一致性RNA序列中插入一段新霉素基因,并用G418進行篩選,感染這種HCV的宿主細胞在復制病毒RNA的同時,編碼新霉素的基因也會復制并表達,使該細胞能夠對抗G418的作用。應用這種方法,科學家在實驗室就可以檢測到病毒的復制[15]。但不幸的是,大部分細胞都死了,只有百萬分之一的細胞能夠存活。通過進一步研究,Rice等[16]和Bartenschlager[17]同時發(fā)現,存活的復制子在細胞內會產生一段獲得性序列變化。當科學家把這一序列構建到原始RNA上時,感染細胞的產量增加了500~ 10 000倍。這是科學家首次在實驗室成功產生有效的HCV復制。由于這些復制子并不產生感染性病毒顆粒,該系統可以安全使用。
2.3蒙面王者:HCV的治療
隨著科學家們成功在活細胞中復制HCV,HCV新療法的研制成了當務之急。 Pharmasset公司(Raymond Schinazi創(chuàng)立)的科學家們開始關注HCV的RNA復制酶。這種酶的活性結構域在各種HCV中相對保守,而人體內卻沒有類似物。因此,針對該復制酶的抑制物可以阻礙HCV的復制而不干擾人體的正常生理功能。研究者關注到一些核苷類似物,他們可以在RNA復制過程中連接到新的RNA鏈上,阻礙RNA復制酶添加新的核苷。這種核苷類似物的干擾使RNA的復制過程中斷。2005年,Pharmasset團隊成員Clark等[18]以此為依據,鑒定出了一種抑制HCV RNA復制的核苷類似物。初期的臨床試驗得到了很好的安全性評價,然而科學家們很快發(fā)現,這種類似物進入人體后很快就失去了活性,不再參與RNA的復制過程。Pharmasset公司隨即在Sofia的帶領下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改良后的核苷類似物通過與另一類RNA復制酶抑制劑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HCV的增生,美中不足的是這一方法需要大劑量、頻繁使用核苷類似物。
為了改變僵局,Sofia想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方法[19]。早期研究[18]已經發(fā)現傳統的類似物并不會全部失活,通過一系列的反應,體內的酶可以把他們中的一部分轉化為一種特殊的化合物。這一物質能夠長期穩(wěn)定地存在于肝臟中阻止HCV的增生且不會變性失活。為了提高這部分穩(wěn)定高效的化合物的比例,Sofia需要一種特殊的與傳統核苷類似物相似但轉化效率更高的復合物。但這種復合物表面帶有磷酸鹽基團,其負電荷使它很難通過膜磷脂進入細胞。Sofia通過修飾其表面的磷酸鹽使其不能被識別從而使該物質順利通過膜磷脂。進入細胞后,肝細胞酶會分解這種修飾物,從而暴露出其內部的復合物。此時,細胞內另一種轉化酶與其結合激活其功能,抑制HCV的增生。由于只有肝細胞才能攝取并利用這一復合物,因此其避免了對人體其他器官的傷害。Sofia將其命名為Sofosbuvir(索非布韋,商品名Sovaldi),早期臨床試驗顯示出極大的有效性。與Ribavirin (利巴韋林) 共同使用,可長期清除HCV。經過12周連續(xù)治療后,患者體內將持續(xù)24周檢測不到病毒。這種無干擾素治療開創(chuàng)了HCV治療的新時代。2013年12月,美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批準Sofosbuvir用于HCV治療。其在各種丙肝人群中證實有效。
同樣應用該復制子檢測方法,Gao帶領的Bristol-Myers Squibb小組鑒定出一種復合物,能夠靶向HCV上一個未知功能的蛋白[20]。在此基礎上,Gilead快速研發(fā)出該復合物的衍生物,命名為ledipasvir。ledipasvir與Sofosbuvir聯合應用能夠快速清除病毒(圖8)。應用該處方8~12周,療效增加至94%~99%,甚至對于難治性患者也能達到此療效。ledipasvir與Sofosbuvir的聯合使用,被命名為Harvoni,經FDA批準用于多種類型HCV感染的治療,這是第一個避開干擾素和利巴韋林的治療方式,之后又有4種藥物獲批,其中2種是以Sofosbuvir為骨架。

圖8 Harvoni的快速治療效率[2]
Harvoni治療一周后,血液HCV的量下降10 000倍。數據來自感染HCV后未接收其他治療的患者。8周治療后,HCV低于檢測閾值。HCV:丙型肝炎病毒。
3 特別貢獻獎[2]
2016年拉斯克特別貢獻獎頒發(fā)給了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學家,一位有遠見的領導者——Bruce M. Alberts(圖9)。在科研領域,Alberts設計了強大的實驗工具,用于理解DNA復制的機制;在社會活動領域,Alberts一直秉持著仁愛、開放的態(tài)度推進全世界的科學教育事業(yè)與科學交流的發(fā)展。他編寫的細胞生物學教材,現已出版至第6版,鼓勵了無數科研工作者從研究、發(fā)現及思考中獲得樂趣。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S)主席,Alberts一直堅持致力于提高全民科學教育水平。他通過謙遜、誠實、有效的工作,贏得了全球科學家和政治家的尊敬和信任。

圖9 Bruce M. Alberts[2]
3.1始于失敗:誰的青春不迷茫
Alberts畢業(yè)于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之后于哈佛大學進行研究生學習。1965年,完成博士學業(yè)后,這位科學界的泰斗很不幸沒有通過自己的第一次博士答辯。Alberts笑稱自己之前一直以為博士答辯只是一種形式,會讓每一名學生通過,然而他卻成為同學中唯一沒有獲得博士學位的人。Alberts很快從失敗中走出來,并且完成了第2次答辯拿到了自己的博士學位。這次失敗的經歷使他在之后的科研生涯中一直秉持著這種觀點——實驗結果能夠證明自己的推論固然是好事,但陰性結果也可以證明其理論的缺陷從而使自己獲得改正提高的機會。不管實驗成功與否,他都認真分析自己的每一次實驗結果。自此之后,Alberts一直秉持著嚴謹認真、求實創(chuàng)新的研究態(tài)度,他在事業(yè)上的巨大成功與這些密不可分。
3.2牛刀初試:解析DNA復制過程
Alberts對待實驗的態(tài)度促使他發(fā)明了一種非常實用的技術,該技術能夠捕捉并分析所有特異結合DNA的蛋白質。1970年,他報道了一種DNA結合蛋白能夠結合在DNA雙螺旋的其中一條鏈上,并使其解螺旋,從而使DNA復制酶更容易向DNA鏈上添加核苷酸[21]。這一單鏈DNA結合蛋白的發(fā)現非常偶然,科學家們逐漸發(fā)現類似的蛋白在幾乎所有細胞內發(fā)揮著促使DNA復制的作用。為了確定DNA究竟是如何合成的,他提純了一種簡單的在細菌病毒復制中發(fā)揮作用的蛋白質。1975年,他利用6個蛋白合成DNA,高度還原了DNA在細胞內的產生過程[22]。傳統觀點認為,各個蛋白在與DNA模板發(fā)生隨機碰撞后依次發(fā)揮作用。Alberts卻發(fā)現所有蛋白相互影響共同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分子機器。每個蛋白都會依次發(fā)揮作用,ATP供能后使蛋白形狀改變,驅使DNA開始復制。Alberts很快意識到,這種分子系統的反應形式存在于多種生理過程中,他的這一發(fā)現開創(chuàng)了生物化學研究的新紀元。
3.3致力教育:從細胞生物學到科學
20世紀70年代末期,Alberts開始有了把細胞生物學與當時新興的分子生物學合編為一本教科書的想法。1983年,他和他的同事們編寫的《細胞分子生物學》正式出版(圖10)。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Alberts的團隊用一種全新的敘述手法介紹最新的觀點和事物。他們希望這本書不僅僅是總結知識,更是科學的升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每個科學家分別撰寫了與自己專業(yè)領域有關的章節(jié)后,與其他專業(yè)領域的科學家交換閱讀,以此確保即使是初學者也能夠明白本書內容所表達的意思。他們的工作使這本書的內容史無前例的清晰明了。為了突出可讀性,這本書沒有使用大量的術語使那些還沒有建立清晰的學科框架、熟悉專業(yè)術語的學生感到困惑和厭煩。僅僅需要數秒鐘的閱讀時間就可以理解一條學科相關信息。

圖10 《細胞分子生物學》教材[2]
Alberts對于學生學習知識的關心遠超出細胞生物學領域。他一直主張,科學的學習應該教會學生解決問題而不是盲目地教授理論知識,真正成功的教育應該能夠使國民真正參與社會有關的問題的解決并且在解決問題時能夠客觀理性地思考。1993年,Alberts執(zhí)掌了國家科學院并試圖轉變美國的科學教育。在位12年,他完成了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并推動國家科學院發(fā)表了大量關于如何在各種層面教授科學的報告。
3.4傳播科學:每一個國家都需要科學工作者
作為國家科學院主席,Alberts一直致力于幫助發(fā)展中國家的科學家對政府做出影響,目的在于鼓勵健康、農業(yè)、環(huán)境、教育以及能源領域進行循證評價。Alberts堅信每個國家都需要自己的科學工作者來掌握當地的文化和需求,即使貧窮的小國家也必須要有自己的科學工作者及科研院所。擁有收集客觀公正的科學意見的途徑,公民及政客才能做出理性的決定,促進國家經濟持續(xù)發(fā)展。1993年,Alberts創(chuàng)建了國際組織——國際科學院(Inter Academy Panel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IAP),旨在引導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將科學研究與國家的建設相結合,促進各國政府對科學事業(yè)的支持,如今世界各國已有一百多個科學學會加入該組織。2000至2009年,Alberts一直兼任該組織主席。
Alberts于1993至2005年連任兩屆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離任后,Alberts作為美國總統Barack Obama的首席科學顧問之一繼續(xù)從事他的科學事業(yè)。2011年,科學家們被任命處理伊斯蘭國家的科技問題。Alberts的工作重點是世界第4人口大國——印度尼西亞。他很快發(fā)現印度尼西亞沒有穩(wěn)定的機構可以支持科學研究。因此,有天賦的年輕科學家們因為得不到資助而沒有機會去驗證他們的觀點并進一步成為科研工作者。于是,2016年,Alberts與世界銀行及印度尼西亞的科學院共同建立了基金會——印度尼西亞科學基金(the Indonesian Science Fund)。旨在通過為青年科學家們提供資助而推動印度尼西亞科學事業(yè)的進步。為了增強印美兩國科學家間的互信合作,Alberts每年會組織約80名印美兩國的科學家齊聚印度尼西亞共同探討共同關心的科學問題,深入交換看法。他一直堅信著,對于科學事業(yè),國家間的合作比競爭更重要。
2008至2013年,Alberts連任Science雜志主編。并且,Alberts長期在非營利科學組織擔任顧問。2012年,美國總統授予他美國國家科學獎。如今已78歲的Alberts仍以實際行動孜孜不倦地推動著全球科學教育的進步與發(fā)展。
[1]朱安遠,郭華珍. 諾貝爾獎的風向標——美國拉斯克獎概覽[J]. 中國市場,2016(5):183-194.
[2]Evelyn Strauss. THE 2016 LASKER AWARDS. (2016-09-13)[2016-09-27].http://www.laskerfoundation.org/.
[3]Semenza G L, Rue E A, Iyer N V, et al. Assignment of the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alpha gene to a region of conserved synteny on mouse chromosome 12 and human chromosome 14q[J]. Genomics, 1996, 34(3): 437-439.
[4]Tan C C, Eckardt K U, Firth J D, et al. Feedback modulation of renal and hepatic erythropoietin mRNA in response to graded anemia and hypoxia[J]. Am J Physiol, 1992, 263(3 Pt 2): F474-F481.
[5]Tan C C, Eckardt K U, Ratcliffe P J. Organ distribution of erythropoietin messenger RNA in normal and uremic rats[J]. Kidney Int, 1991, 40(1): 69-76.
[6]Ratcliffe P J, Jones R W, Phillips R E, et. al. Oxygen-dependent modulation of erythropoietin mRNA levels in isolated rat kidneys studied by RNase protection[J]. J Exp Med, 1990, 172(2): 657-660.
[7]Minamishima Y A, Kaelin W J. Reactivation of hepatic EPO synthesis in mice after PHD loss[J]. Science, 2010, 329(5990): 407.
[8]Sellers W R, Novitch B G, Miyake S, et al. Stable binding to E2F is not required for the retinoblastoma protein to activate transcription, promote differentiation, and suppress tumor cell growth[J]. Genes Dev, 1998, 12(1): 95-106.
[9]Epstein A C, Gleadle J M, McNeill L A, et al. C. elegans EGL-9 and mammalian homologs define a family of dioxygenases that regulate HIF by prolyl hydroxylation[J]. Cell, 2001, 107(1): 43-54.
[10]Takeuchi K, Boonmar S, Kubo Y, et al. Hepatitis C viral cDNA clones isolated from a healthy carrier donor implicated in post-transfusion non-A, non-B hepatitis[J]. Gene, 1990, 91(2): 287-291.
[11]Kolykhalov A A, Feinstone S M, Rice C M. Identification of a highly conserved sequence element at the 3' terminus of hepatitis C virus genome RNA[J]. J Virol, 1996, 70(6): 3363-3371.
[12]Tsuchihara K, Hijikata M, Fukuda K, et. al. Hepatitis C virus core protein regulates cell growth and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transmitting growth stimuli[J]. Virology, 1999, 258(1): 100-107.
[13]Kolykhalov A A, Agapov E V, Blight K J, et al. Transmission of hepatitis C by intrahepatic inoculation with transcribed RNA[J]. Science, 1997, 277(5325): 570-574.
[14]Yanagi M, Purcell R H, Emerson S U, et al. Transcripts from a single full-length cDNA clone of hepatitis C virus are infectious when directly transfected into the liver of a chimpanze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94(16): 8738-8743.
[15]Bartenschlager R, Lohmann V. Replication of hepatitis C virus[J]. J Gen Virol, 2000, 81(Pt 7): 1631-1648.
[16]Evans M J, Rice C M, Goff S P. Gene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hepatitis C virus replicons[J]. Journal of Virology, 2004, 78(21): 12085-12089.
[17]Bartenschlager R. Hepatitis C virus replicons: potential role for drug development[J].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002, 1(11): 911-916.
[18]Clark J L, Mason J C, Hollecker L, et. al. Synthesis and antiviral activity of 2′-deoxy-2′-fluoro-2′- C -methyl purine nucleosides as inhibitors of hepatitis C virus RNA replication[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06, 16(6): 1712-1715.
[19]Sofia M J, Furman P A, Symonds W T. Chapter 11:2′-F-2′-C-Methyl Nucleosides and Nucleotid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epatitis C Virus: from Discovery to the Clinic[J]. 2010.
[20]Lu L, Shen T, Gao J, et al. Effectiveness of HCV core antigen and RNA quantification in HCV-infected and HCV/HIV-1-coinfected patients[J].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2013, 14(1): 1-8.
[21]Huberman J A, Kornberg A, Alberts B M. Stimulation of T4 bacteriophage DNA polymerase by the protein product of T4 gene 32.[J].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1971, 62(1): 39-52.
[22]Weintraub H, Worcel A, Alberts B. A model for chromatin based upon two symmetrically paired half-nucleosomes[J]. Cell, 1976, 9(3): 409-417.
編輯陳瑞芳
, E-mail:xmwang@ccmu.edu.cn
The 2016 Lasker Awards
Li Yuzheng1, Zhang Ting2, Wang Xiaomin2,3*
(1.ClinicalMedicalSciences,SchoolofBasicMedicalSciences,CapitalMedicalUniversity,Beijing100069,China;2.DepartmentofNeurobiology,SchoolofBasicMedicalSciences,CapitalMedicalUniversity,Beijing100069,China;3.BeijingInstituteforBrainDisorders,Beijing100069,China)
In September 13, 2016, the list of winners of the year’s Lasker Awards were released. The 2016 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ward honors William G. Kaelin, Jr., Peter J. Ratcliffe and Gregg L. Semenza, for their discovery of the pathway by which cells from human and most animals sense and adapt to changes in oxygen availability, a process that is essential for survival. The 2016 Albert Lasker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honors Ralf F. W. Bartenschlager, Charles M. Rice and Michael J. Sofiafor, who developed a system to study the replication of the virus that causes hepatitis C and used this system to revolutionize the treatment of this chronic, often lethal disease. The 2016 Lasker Award for Special Achievement in Medical Science honors Bruce M. Alberts for fundamental discoveries in DNA replication and protein biochemistry; for visionary leadership in direct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to better people’s lives; and for passionate dedication to improving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Lasker Awards;HIF-1; hepatitis C virus (HCV); DNA replication
時間:2016-10-1610∶5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1.3662.R.20161016.1058.028.html
10.3969/j.issn.1006-7795.2016.05.028]
2016-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