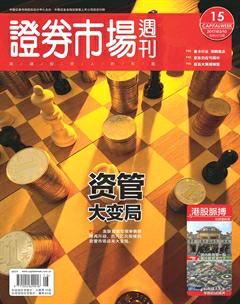息差收窄對于銀行是禍是福?
劉濤
對于銀行而言,息差收窄反而是一個有力的助推器。它將激勵銀行加快發展零售銀行、私人銀行、投資銀行、交易銀行、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等創新業務,積極向國際領先同業看齊。
近年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陡然提速。先是2013年7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率先放開;接著是2015年10月,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上限也最終取消。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利率市場化帶來最大、最直接的沖擊莫過于息差收窄。
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利率市場化開始前的1960-1976年,日本銀行業平均利差為2.29%;而在利率市場化完成后的1995-2010年,日本銀行業平均利差已降至1.72%。韓國也存在類似情形,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之初的1982年,韓國銀行業平均利差曾高達3.79%;而在利率市場化完成后的1998-2010年,平均利差僅為1.67%。
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數據,2012年一季度,我國商業銀行凈息差為2.76%;而到了2016年一季度,這一指標降至2.35%,降幅達41個基點。但上述情況只反映全國的整體水平,并不代表各地銀行實際的凈息差水平皆是如此。總體上看,中西部、東北地區凈息差水平略高,東部沿海地區偏低;地方銀行較高,全國性大型銀行較低。
最近,許多媒體都注意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剛剛獲準上市的西部某城商行2015年ROE(凈資產收益率)高達26%,該行也被譽為14家擬上市銀行中盈利性最出色的銀行。究其原因,除資產規模快速擴張外,主要還是地處金融生態相對不發達的西部省份,加之客戶定位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銀行擁有較高的貸款定價權,2015年凈息差雖比2014年的4.05%下滑43個基點至3.62%,但仍遠高于東部地方銀行和大型銀行。
類似的“區域性利差紅利”在我國東北、中部不少地方銀行都不同程度存在。從東部地區來看,2015年江蘇省法人銀行金融機構的凈息差僅能維持在2.8%左右,最新上市的江蘇銀行凈息差更低至1.94%,這反映出當地金融生態較發達,銀行業競爭極為激烈,同時企業議價能力也更強。
此外,就大銀行來看,2015年,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的凈息差分別為2.3%、2.49%、2.12%、2.46%、2.22%,同樣明顯低于中西部、東北的地方銀行。其中,農行的凈息差之所以能在五大行里居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其業務渠道相對于其他大行下沉得更深,特別是在中西部農村網點布局廣泛,面對的客戶相對弱勢。
然而,凡事皆有兩面性。一方面,利差持續下降將導致銀行凈利息收入隨之減少。經合組織(OECD)《銀行利潤報告》顯示,上世紀70年代初德國銀行業凈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超過90%,而1981-1998年這一比重平均僅為78.1%,1999-2003年更進一步降至67.7%。另一方面,凈利息收入萎縮的壓力也將倒逼銀行努力創新,擴大非利息收入來源。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日本銀行業表外業務量以每年40%的速度遞增,從80年代初的20.14%升至90年代的35.19%。這也說明利率市場化以后,相關國家商業銀行積極從單純的“融資中介”向“融資中介和服務中介并重”轉型,大力拓展中間業務收入來彌補不足。
短期來看,息差收窄確實給我國銀行帶來了較大壓力和挑戰。2012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凈利潤增速普遍從兩位數暴跌至個位數,甚至出現零增長、負增長,除經濟下行情況下日益增長的不良資產吃掉了較大一塊利潤外,息差收窄無疑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在這一背景下,部分地方銀行如能繼續享有相對較高的凈息差,無疑是令其他同業羨慕不已的事。
但需要警惕的是,較高的凈息差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部分地方銀行加快中間業務發展、創新利潤增長點的動力。2015年,前述的西部某城商行利息凈收入占比高達88.6%,手續費和傭金凈收入僅占8.75%,表明該行在中間業務和創新業務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掘。
相比之下,2015年,中國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達30.65%,雖與國際先進銀行,如富國銀行的47%仍有不小差距,但已遠遠超過國內多數地方銀行的水平。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在美國,大中小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也存在一定差異。
長遠來看,對于已經下決心推進轉型發展戰略、積極適應新常態的銀行而言,晚動不如早動,息差收窄反而是一個有力的助推器。它將激勵銀行加快發展零售銀行、私人銀行、投資銀行、交易銀行、金融市場、互聯網金融等創新業務,積極向國際領先同業看齊,實現向現代銀行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