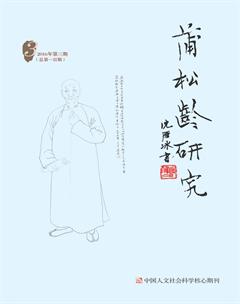論蒲松齡的民生思想
付一冰 陳文新
摘要:本文以《聊齋文集》為主要文本依據(jù),具體分析了蒲松齡民生思想的內(nèi)涵:在與官員的交往中,仗義執(zhí)言,為民請(qǐng)命;對(duì)害民之政,致力于防微杜漸;悲天憫人,哀民生之多艱;全方位關(guān)心百姓日常生活。其儒生情懷與唐代的杜甫比較相似。
關(guān)鍵詞:蒲松齡;聊齋文集;民生思想;聊齋志異
中圖分類號(hào):I207.41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了路大荒編輯整理的《蒲松齡集》,其中《聊齋文集》收錄了絕大部分蒲氏散文,內(nèi)容涉及交友、游歷、生活、農(nóng)事、氣候、時(shí)政等各個(gè)方面。縱觀整部《聊齋文集》,題材多反映農(nóng)村生活、描繪民間疾苦,并積極為淄川一帶百姓的生產(chǎn)生活問題奔走疾呼,充分體現(xiàn)了蒲松齡的民生思想。本文以《聊齋文集》為主要文本依據(jù),致力于對(duì)蒲松齡民生思想內(nèi)涵的闡述。
蒲松齡常年生活在山東省淄川縣蒲家莊,親眼目睹了社會(huì)底層民眾艱辛不易的生活,對(duì)他們抱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之心,這份同情之心被他付諸筆端,成為了政論里的建言獻(xiàn)策、書信里的吶喊疾呼、災(zāi)記里的痛心疾首。用蒲松齡自己的話來說,他對(duì)民生問題的關(guān)心是“眾瘡痍啼饑號(hào)凍,每恨拯救無(wú)術(shù),只此一腔熱血,可對(duì)青天” [1] 211 ;而具體來說,蒲松齡的民生思想在《聊齋文集》中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gè)方面。
一、在與官員的交往中仗義執(zhí)言,為民請(qǐng)命
蒲松齡雖然終生困于場(chǎng)屋,但憑借著過人的才華,在當(dāng)時(shí)也已頗有聲望,因而得到了一些官員的欣賞和尊重——小至淄川縣的歷任縣令,如汪如龍、張嵋等,大到朝廷重臣、文壇領(lǐng)袖,如王士禛等,都與他有所往來。關(guān)于他和這些官員的交往情況,我們可以從《聊齋文集》所收錄的書信、序跋等文中管窺一二。
張嵋,字石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淄川知縣,“神姿卓邁,歷事精明,下車數(shù)月,邑賴之百?gòu)U俱興” [1] 15 ,為了紀(jì)念他的功德,淄川百姓還為他修建了“沈張二公祠”。蒲松齡與他交往較為密切——張嵋到任淄川時(shí),曾親自登門拜訪過蒲松齡,蒲松齡《與邑侯張石年嵋》、《頌張邑侯德政序》等文,都表達(dá)了對(duì)張嵋德政的感激與贊賞之情。對(duì)于張嵋在治縣時(shí)沒有體察到的一些事情,蒲松齡也敢說、敢議,在《上邑侯張石年嵋書》一文中,蒲松齡先是針對(duì)淄川存在的刁訟之風(fēng)提出了“重懲而亦仁”的建議;后又提醒張嵋“古今有忠奴仆,無(wú)忠衙役” [2] 132 ,希望張嵋嚴(yán)厲管理衙役。蒲松齡的直言不諱,既是關(guān)心朋友,更是站在百姓的角度對(duì)縣官提出建議和要求。
在淄川漕弊一案中,蠹役康利貞因?yàn)槠阉升g和淄川百姓的努力抗?fàn)幎桓锫殻赐犊啃滩可袝跏慷G和山東巡撫譚再生,企圖官?gòu)?fù)原職。聽到這個(gè)消息,蒲松齡立馬寫了《與王司寇》、《與張益公同上譚無(wú)競(jìng)再生進(jìn)士》兩封書信給王士禛和譚再生,痛斥康利貞的種種惡行,請(qǐng)求二人不要支持康利貞重回淄川擔(dān)任漕糧經(jīng)承,他在文中聲淚俱下地控訴道:“(康利貞)欺官害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平民,皮骨皆空。” [2] 139 “小民有盡之血力,縱可取盈,蠹役無(wú)底之貪囊,何時(shí)填滿?” [2] 140 ——由于蠹役的貪婪,漕糧被抬高到淄川百姓無(wú)力承擔(dān)的高價(jià),面對(duì)這樣的暴政,蒲松齡憤怒地用“皮骨皆空、血力皆盡”來形容被壓干榨盡的百姓。由于蒲松齡的干涉,康利貞沒能得償所愿,但蒲松齡也為此得罪了譚再生。
對(duì)于那些平日里沒有多少往來的官員,只要事關(guān)淄川百姓的生產(chǎn)生活,只要確有進(jìn)言的必要,蒲松齡也會(huì)以各種方式間接上書,《與孫爻文轉(zhuǎn)示吳縣公》、《又與李希梅》等都是這類文章的代表。其實(shí),以蒲松齡的名氣和他與這些官員的交情,他大可以自薦功名或者請(qǐng)求幫助,但蒲松齡沒有這樣做,他在信中也幾乎不提自己困頓的處境(即使偶爾提及也多是自嘲)。總而言之,在與各級(jí)官員的書信往來中,蒲松齡常常是就一方百姓之安樂向這些身居高堂的人積極進(jìn)言,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擔(dān)起兼濟(jì)天下的責(zé)任,字里行間流露出那份樸實(shí)而又深情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
二、致力于杜絕“害民之政”
“天下害民之政,多起于仁人也。何以故?當(dāng)年廉者創(chuàng)之以除民害,故為仁政;后世貪者借之以罔民財(cái),故成流弊也。” [2] 307 “事有似為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實(shí),乃毫無(wú)益而大有害者,則歷來各省州縣禁糴之令也。” [2] 316 在《淄邑流弊》、《禁糴說》等多篇談?wù)摃r(shí)政的文章里,蒲松齡都發(fā)表了自己對(duì)害民之政的看法。蒲松齡認(rèn)為,這些政策在制定時(shí)的出發(fā)點(diǎn)往往是好的,但最后卻給人民造成了負(fù)擔(dān)和困擾,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diǎn):一是后世的貪官污吏趁機(jī)鉆營(yíng),使仁政變成了“人禍”;二是政策本身的制定沒有從實(shí)際出發(fā),因而在施行過程中產(chǎn)生了偏差或者相反的后果,也就變成了“人禍”。而生活在淄川農(nóng)村的蒲松齡與底層人民共處一域,使他能夠接觸真實(shí)的情形,并就此做出深刻分析。
就拿禁糴一事來說,主事者最初的想法是通過禁止人民私下買賣糧食來防止米價(jià)起伏傷民,“本處豐收,四方來糴,則本處之糧大貴;或且糴者多而糧必盡,貧民必至于餓死,則是禁糴者,體上天好生之仁,恤一方無(wú)告之眾,豈非善政哉?” [2] 316 但是身居高位的主事者卻沒有想到,在糧食市場(chǎng)上,不是先有買方的需要,而是先有賣方的需要,“夫糴者,非強(qiáng)人而糴之也,有糶者而后有糴者。” [2] 316 恰恰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需要靠販賣糧食來?yè)Q取其他必需的生活物資,禁糴不可能真地杜絕買賣糧食的現(xiàn)象,只能使糧價(jià)日賤,貧民要賣更多的糧食來?yè)Q取所需,“向來可以少糶而有余者,今反使之多糶而不足,其所有利于貧人者何如也?” [2] 316 。于是,“仁政”就變成了“人禍”,蒲松齡的指陳,可謂犀利。
蒲松齡不僅能發(fā)現(xiàn)問題本質(zhì)、體察實(shí)際民情,還就如何解決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議。在《循良政要》一文中,他站在淄川知縣的角度,針對(duì)如何治縣提出了多達(dá)十七條的建議,涉及治安、訴訟、民風(fēng)、吏治、征稅等各個(gè)方面;這些建議都是蒲松齡經(jīng)過對(duì)底層百姓生存狀況的細(xì)致觀察和深入思考后提出來的,每一條都針對(duì)一個(gè)實(shí)際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具有較強(qiáng)的實(shí)用性。如“速聽斷”一條,建議縣官在處理田土錢債這些平常糾紛的時(shí)候,不必拘泥于規(guī)定的判決日期,而是在當(dāng)天就審理判決,因?yàn)椤耙蜓染茫瑒t刁民之變?cè)p日生,而良民之脂膏日盡,往往未蒙質(zhì)審,而皮骨已空” [2] 286 ,訴訟的時(shí)間一長(zhǎng),對(duì)良民就會(huì)不利,這是上級(jí)官員難以體察到的。又如“禁衙役下鄉(xiāng)”一條,乍聽之下有些可笑,但卻揭露了蠹役害民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衙役一到,勢(shì)如虎狼,羅織鄉(xiāng)村,肆行貪虐,因之挨戶攢錢,迄無(wú)寧晷。” [2] 286
總而言之,蒲松齡對(duì)“人禍”的思考和建議,可以說是敦本務(wù)實(shí)、思慮入微,這些思考保留在《淄邑流弊》、《淄邑漕弊》、《禁糴說》、《錢糧比較說》、《循良政要》等十?dāng)?shù)篇政論文章中,是我們研究蒲松齡民生思想的寶貴材料。
三、悲天憫人,哀民生之多艱
長(zhǎng)期生活在淄川農(nóng)村的蒲松齡,深知?dú)夂颉⑾x害等自然災(zāi)害對(duì)農(nóng)民生產(chǎn)生活的毀滅性影響,他不僅在平日里關(guān)注天文氣象、注重預(yù)測(cè)和防范,還在災(zāi)害發(fā)生的時(shí)候,用深沉悲切的筆觸記錄和抒發(fā)了自己的悲痛心情。如《蝗賦》、《祭蜚蟲文并序》等控訴蟲害的文章,前者發(fā)揮賦體的特點(diǎn),以激昂、悲憤的氣勢(shì)逐條痛述蝗災(zāi)來臨時(shí)的情狀:“爾其掩映萬(wàn)村,橫亙百市,遮朝陽(yáng)而晦光,帶寒星而鵲起”、“迎旭抖擻,貫甲自喜,銜枚無(wú)聲,赤地千里”、“倉(cāng)卒毀裳,急遽揚(yáng)旌,丁男長(zhǎng)號(hào),父老哀鳴”,一幅蝗蟲蔽日、赤地千里的畫面如在眼前,怵目驚心;后者則以對(duì)話體的形式,直接向蜚蟲發(fā)出嚴(yán)厲的責(zé)問,“人已剝皮而見骨,爾猶嘬乎胔骼之余芳。嗚呼!麥奄奄以垂盡,爾蠕蠕而未已,延及秋禾,害無(wú)止休。天既生人,何復(fù)生爾?” [2] 35作者對(duì)蜚蟲的厭惡憎恨之情躍然紙上,讀這些作品,我們仿佛看見了那個(gè)奮筆疾書、悲憤不已的蒲松齡。
據(jù)統(tǒng)計(jì),“清代山東地區(qū)幾乎無(wú)年不災(zāi)、無(wú)災(zāi)不烈,水災(zāi)、旱災(zāi)、蟲災(zāi)是最主要的三大災(zāi)害現(xiàn)象”。[3] 81 這些自然災(zāi)害中對(duì)民生影響最大的、也讓蒲松齡最憂慮痛心的一次,是發(fā)生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到四十三年(1704)之間的一次水災(zāi)、旱災(zāi)、蟲災(zāi)接連發(fā)生的千年災(zāi)荒。也正是在這次災(zāi)害期間,蒲松齡寫下了《康熙四十三年記災(zāi)前篇》、《秋災(zāi)記略后篇》、《救荒急策上布政司》等文,記錄了災(zāi)情的發(fā)展過程和人民抗災(zāi)的努力,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上書山東布政司趙宏燮,力陳救荒政策,顯示了他的莫大勇氣和系蒼生、憂天下的民生情懷。其中,《康熙四十三年記災(zāi)前篇》一文繼承杜甫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精神,以寫實(shí)的筆觸描繪了臭蟲漫天、餓殍遍野、流民失所、滿目瘡痍的淄川受災(zāi)景象,可以看作是蒲松齡災(zāi)荒文的代表之作。
《康熙四十三年記災(zāi)前篇》以時(shí)間為軸,先敘述災(zāi)情之反復(fù),從四、五月間“二麥無(wú)收”、“風(fēng)雨竟日”的水災(zāi),到六月十九以后“田深半尺無(wú)潤(rùn)土”的旱災(zāi)(在此期間還發(fā)生了嚴(yán)重的蜚蟲災(zāi)害),一直到來年下了幾場(chǎng)雪,才“麥未出者盡出,出者盡長(zhǎng)”,卻又“由此雨復(fù)絕,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zhuǎn)灣種者高田亢死之”,總之,災(zāi)害持續(xù)時(shí)間之久,災(zāi)情之反復(fù)無(wú)常,實(shí)為少見。緊接著,蒲松齡用寫實(shí)的手法,描述了災(zāi)荒年代人民生活的慘象,先是糧食不足造成的物價(jià)飛漲,“攜千錢并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為了生存,農(nóng)村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專門買賣婦女兒童的市場(chǎng),“鬻兒賣婦者,邑?zé)o賴居為肆求售,取牙利焉”;后來,天災(zāi)發(fā)展為人禍,“(盜)縱火燒村舍,殺人行淫,罔不至”;到了最后,整個(gè)淄川差不多村村皆空,“耗者死二而逃者三,存者人三而賊二”;這時(shí)怵目驚心的景象發(fā)生了:“掘眢井,深數(shù)尺,納尸焉;既滿復(fù)掘,蓋十余井,猶未已也”;“貨人肉者,凌晨驅(qū)驢,載送諸市肆,價(jià)十分羊之一”;“得入眢井,猶大葬也”。 [2] 47-49 ——堆積成山的尸體挖十口井也埋不完,人肉的價(jià)格比羊肉還低,死后尸體能被埋入深井而不是被賣掉就是“體面風(fēng)光的大葬”了!
寫《康熙四十三年記災(zāi)前篇》的時(shí)候蒲松齡已經(jīng)六十高齡了,但他沒有絲毫的世故和冷漠,而是悲天憫人、一腔熱血。隔著數(shù)百年的時(shí)間,我們?nèi)匀荒軓淖掷镄虚g讀出那份縈繞在他心頭“哀民生之多艱”的痛心。
四、對(duì)百姓日常生活全方位的關(guān)心
蒲松齡的民生思想,還體現(xiàn)在他對(duì)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關(guān)心上,大到前文提到過的天災(zāi)人禍,小到村里的建橋修路、農(nóng)田水利,甚至淄縣村民的婚喪嫁娶,他都事事勞心、親力親為。從《〈藥祟書〉序》、《〈農(nóng)桑經(jīng)〉序》、《王村募修路序》、《連三溝募修橋序》、《栗里建橋疏》等文章里,我們看到了一個(gè)全方位關(guān)心百姓民生的蒲松齡。
《〈藥祟書〉序》一文收錄在《聊齋文集》卷三,交代了蒲松齡編寫《藥祟書》一書的初衷,“山村之中,不惟無(wú)處可以問醫(yī),并無(wú)錢可以市藥”。因?yàn)樯酱謇飳めt(yī)問藥不方便,所以蒲松齡把一些常見藥方收集起來,“以備鄉(xiāng)鄰之急”;考慮到村民的實(shí)際經(jīng)濟(jì)能力,所以《藥祟書》只收錄價(jià)格低廉、容易獲取的藥方,“不取長(zhǎng)方,不錄貴藥,檢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攜取” [2] 61 。這種處處體察與體貼人民生活艱辛的風(fēng)范,令人感到溫暖。
蒲松齡很早就注意到了農(nóng)村基礎(chǔ)建設(shè)的重要性,《王村募修路序》、《連三溝募修橋序》、《栗里建橋疏》等數(shù)篇文章記錄了他參與的一些工程。而對(duì)于為什么要修路建橋,蒲松齡有不同的考量。王村地處郡邑通衢,交通位置重要,然而道路需要整修的原因,是“雨則魚游于道,旱則馬陷于淖”、“畝中車馬襁屬,未種者驅(qū)為道,已禾者踐為道” [2] 68 ,年久失修的道路不僅給行人帶來了不便,而且也使道路兩旁的莊稼遭受踐踏,農(nóng)民蒙受了經(jīng)濟(jì)損失。而在連三溝修橋,更多是出于安全上的考慮,“即晴燥時(shí)亦滑滑有蹄痕,小雨過,則如鲇魚上竹竿,不可復(fù)行”,“余曾冒雨經(jīng)由,驢蹷人墮……竊意一道行人,往來甚伙,其必有覆載傾跌如仆者可知也” [2] 71 ,因?yàn)樽约涸?jīng)在連三溝失足跌落,所以推己及人,擔(dān)心他人也會(huì)發(fā)生同樣的遭遇,于是想到要建造橋梁解決問題。
《〈農(nóng)桑經(jīng)〉序》交代了蒲松齡根據(jù)淄川地方實(shí)際增刪《農(nóng)訓(xùn)》的情由,《積貯社序》號(hào)召農(nóng)民在豐年儲(chǔ)存谷物以備饑荒,這樣的文章還有很多,這里不再一一贅述。總而言之,從這些文章里我們可以知道,蒲松齡對(duì)民生的關(guān)注是全方位的、無(wú)微不至的。
蒲松齡關(guān)注民間疾苦,其儒生情懷與唐代詩(shī)人杜甫有幾分相似。他們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懷有兼濟(jì)天下的遠(yuǎn)大理想,因而在情感上多有共鳴。在蒲松齡的詩(shī)中,他常以杜甫自比。杜甫的詩(shī)被稱為“詩(shī)史”,是中唐時(shí)期壯闊的歷史變遷的生動(dòng)寫照,蒲松齡的古文雖然在體裁上有別于詩(shī)歌,但《康熙四十三年記災(zāi)前篇》、《秋災(zāi)記略后篇》等諸篇對(duì)清初人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寫照,同樣反映了底層人民真實(shí)而悲催的生存狀況,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懷。
參考文獻(xiàn):
[1]蒲松齡.聊齋文集選注[M].劉階平,選注.臺(tái)灣:中華書局,1975.
[2]蒲松齡.蒲松齡集[M].路大荒,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62.
[3]王建平.論蒲松齡的災(zāi)難詩(shī)[J].蒲松齡研究,2012,(1).
(責(zé)任編輯:譚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