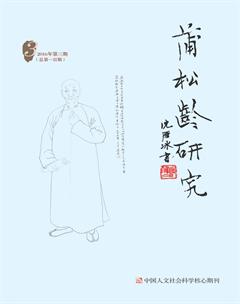蒲松齡與安于拙(去巧)
楊海儒
摘要:本文共分三大部分,圍繞蒲松齡與安于拙交游主題,組織文獻史料。從“聊齋詩與安去巧”入手,參閱淄川道口安氏和於陵安氏兩部家譜與淄川蒲氏、劉氏族譜以及縣志等史料,逐一梳理脈絡,認定安去巧及其姑母在蒲松齡與劉氏定親中的重要作用,成為蒲、安二人交游契機。通過進一步研討,再以“張邑侯舉安于拙鄉飲介賓“為線索,分析蒲松齡與縣令張嵋的特殊關系,找到蒲向張薦舉安為鄉飲介賓的可能性,更是蒲、安二人交游情誼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蒲松齡;安于拙;張嵋;聊齋詩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蒲松齡與安于拙的交情,見載聊齋詩《題安去巧偕老園》(七律二首)與《寄十三兄去巧》(七古一首),共二題三首中。從兩詩看時間跨度相隔30多年,而實際上,二人交往始自蒲氏弱冠,延至其古稀之年。其間見面不多,然而友情深厚,且維持50年不變,直至安氏晚年卒前。二人是何關系?為何交往?學術界未見有人論及并深究。筆者對此曾關注多年,搜集過有關家譜等文獻史料,但限于淄川安氏先祖溯源存疑,未能寫成,竟一拖廿年。友人安盛山先生近送所需家譜,使舊念復萌,謹以拙作,以饗同好。
一、聊齋詩與安去巧
《聊齋詩集》卷二“乙卯”年有《題安去巧偕老園》(七律二首)。詩云:
蒜發蕭蕭白映簪,羨君玉樹已成林。煙霞聊復耽詩酒, 妻子猶堪作鶴琴。
名教身隨黃卷老,高眠人在碧山深。鹿門蹤跡今何在?豐草白云更可尋。
柳線叢叢帶早霞,日長婢子煮新茶。青山入室人聯座, 白發連床月上紗。
花徑兒孫圍笑語,石亭棋酒話桑麻。門前春色明如錦, 知在桃源第幾家?
《聊齋詩集》卷四“丁亥”年有《寄十三兄去巧》(七古一首)。詩云:
梓橦山下仙人居, 方瞳紺發九十余。疑有長繩系懸車, 顏如映日紅芙蕖。
衍波箋上飛明珠, 綰蛇縈蚓為細書。行步便捷如凌虛, 君獨何修壽容舒?
弱冠東去近精廬, 得睹顏色親華腴。君攜壺酒同歡娛, 座上和風吹四隅。
我累口腹緣諸雛, 爾日分衿音載疏。白帢蒙塵履沾濡, 別時年少今垂胡。
古稀垂近老且癯, 齒牙搖動霜上須。逢人問訊見君無?云復矍鑠豐采都。
嘆想飛越夢蘧蘧, 我遽登門傳相呼。未知猶能認故吾?倚杖大笑握長裾。
應或仿佛辨形模, 向坐傾談古道迂。二老刻燭為贏輸, 麈尾揮落快何如!
按聊齋詩集編年,前詩“乙卯”為清康熙十四(1675)年,作者36歲,正值中年。其自南游作幕歸來,數年間舉業未果,尚無定處。故詩稱安氏“名教身隨黃卷老”,極羨其詩酒自娛與妻子同樂,遠避“鹿門”“碧山深”的隱居生活。七律二首描述了安氏與家人歡聚偕老園,悠然自得的田園樂趣。
后詩“丁亥”為康熙四十六(1707)年,作者68歲,已年近古稀。其時在西鋪畢家坐館已近30年,困于棘圍,終未中舉。故詩稱“古稀垂近老且癯”,雖“別時年少今垂胡”,但仍不忘“弱冠”時舊友,還“逢人問訊見君無”?七古一首描述了年已九旬的安氏,依然“矍鑠豐采都”,且能寫詩,還作“細書”,而步履便捷穩健,顏面紅潤“壽容舒”。同時追憶年少時與安氏交游,至老難忘的情懷。夢想再與之重逢,“傾談古道”,“刻燭”為詩,其樂無窮的景象能得實現的內心企盼。
安去巧,名于拙,字天能,去巧乃其號。府學增生,明御史安伸次子。其“幼失恃,十三歲入泮,事繼母以孝聞。學憲周舉優行,旌之‘行高品粹。邑侯張公舉鄉飲介賓,壽九十五歲卒。所著有《嬾漫村草》藏于家。”名載《淄川縣志》(卷六下)《鄉飲》與(卷十)《三續義厚》。
二、安于拙家世探討
安于拙,出于淄川城東北大劉莊(即今羅村鎮道口村)安氏家族。與蒲松齡夫人劉氏家族同里。20多年前筆者為考查劉氏家譜與安氏族人相識,曾應邀為安氏續譜查考提供有關史料并幫助潤色修改續修序跋。當時即發現其所依清嘉慶間初修、宣統末年續修的舊譜尚需溯源,認為淄川安氏應與於陵(今周村)安氏同族,并建議先與周村安家莊聯系求證老譜后再續不遲。然此忠告未被主持者采納,而匆忙定稿付梓,造成遺憾。后幸其族中有識者安盛山先生悉心盡力,多次往返周村安家莊考查,終得和於陵安氏族譜銜接。證實周村老譜中原先就包括淄川安氏一支,世系詳明,且能上溯至宋、元各代,并非嘉慶與宣統舊譜所載僅限明清時期先人而以上無征。最近,由盛山先生主持新續的於陵安氏族譜即將面世。筆者亦將擱置廿余年尚未寫成的這篇舊稿翻出重寫,為完善聊齋先生交游史料略盡心力耳。
研究某人家世離不開文獻記載,除史志外,家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需要說明的是,淄川道口安氏族譜與於陵安氏家譜(以下簡稱“道口譜”、“於陵譜”)內容大體一致,只是始祖與個別地方存在誤差。筆者對兩譜異同詳加考辨,反復比對,并將安氏先祖播遷原因與軌跡基本澄清,解決了安氏道口譜中諸多訛誤。然而限于篇幅,本文僅摘要概述之(其余另文發表)。
(一)其先人世系及遷徙軌跡原因析
清嘉慶九年《淄川安氏族譜序》云:“吾族之先,江南海州籍也。自海遷莒,一支往日照,一支來淄川,族人所共知也。到淄之初,室家草創,族姓不過數人,未暇紀譜。越數世至封公順禮祖,始能以文學啟后。迨至五世冏卿公與衛輝公相繼發跡之后,族屬漸蕃,始有寫本舊譜。但自莒遷淄,約其世數應在有明嘉、隆之間,迄今近三百年矣……”
該譜世系為:一世始祖,失諱,江南海州人。二世祖文舉。三世祖盈,來至淄川東南山中。
《於陵安氏創修家譜序》云:“……吾安氏系出武威,始居山右應州。自唐,先祖文忠公諱重誨,官中書令,以下支派蕃衍,遂徙濟南之般陽郡。越數世,有恒產,再遷長白山東麓於陵城南隅,因家焉,名為安家莊。至宋末遭花馬軍之變,譜牒散失。故我始祖及二世祖諱字俱失考。迨中葉,戍之祖諱成,歷官元代淮東招討使、督理總把,鎮守山陽等處兼監戰府指揮,誥授忠顯校尉,謚忠顯。其塋兆在鳳山之陰,賜有祭葬,至今巋然尚存。稽諸墓表碑陰宗派圖有:先祖長白公諱云輝,仕宋樞密院參議;華亭公諱榮,武寧軍節度掌;建庵公諱某,金散大夫;永昌公諱全,未仕;會奎公諱聚,仕元千戶長。斯五世乃在忠顯公之上,其下數代諱字尚了如指掌,而云輝祖以上之世系,則有不敢妄述者矣。自忠顯公以后,官爵聯綿,子孫蕃育。徙居近鄉者有之,散處遠方者有之……”
從譜中世系看,淄川安于拙及其先人、祖、孫后輩數十世皆載其中,只是因始祖變化引起世數的差異,例如安于拙在道口譜中是六世,而在於陵譜中卻降為十七世。縷數支系,道口一支當屬五世“聚”的傳人。
以上安氏七世傳承人物中,一至四世的云輝、榮、某、全,與五世中的聚、六世中的成、七世中的提楹,都是淄川安氏始祖溯源的關鍵人物。加上其后至十一世中的提楹長子信、信之季子玉、玉之次子二公、二公之子鳳儀,便構成了一幅完整的淄川道口安氏始祖溯源圖譜。其一世至十一世的傳承順序如下:云輝-榮-某-全-聚-成-提楹-信-玉-二公-鳳儀。而道口譜則以“失諱者”為始祖(即鳳儀之子),文舉為二世,盈為三世(生六子)。事實上再加上前十一世,“失諱者”應為十二世,文舉為十三世,盈為十四世,以下類推。
查於陵譜中第十一世鳳儀名下世系名諱,一如以上所列無誤。但人物小傳記載略有出路。難得的是,於陵譜忠實記載了安伸兄弟五人子輩大排行的順序,找到了安于拙“行十三”的出處,而續修道口譜中則成缺項。
道口譜以“失諱”者為始祖。原因在于族人口碑相傳先祖遷自莒州,而未深究“吾族之先,江南海州籍也,自海遷莒,一支往日照,一支來淄川”語中的“江南海州籍”的祖先為誰,其原籍何處?其實七世中“提楹”小傳所稱:“歷官淮東招討,自上從祖父會奎公在江南修立海州,愛地風俗之美,因家焉。生二子:信、禮。后支派蕃衍,散居頗多”,便點出了根源。本來安居海州的“提楹”之父“成”,是安氏族中最有成就的一支,其功名曾上封至三世。而其后裔數世中大都有職銜。估計至元末明初遭遇戰亂,海州安氏族人難以在本地居留,只得四散避禍,天各一方,竟至失諱,后嗣不詳。最后“鳳儀”之子流落莒州,雖生三子,而再次分散。其長支“文舉”配董氏,生一子“盈”。傳稱“于明嘉靖、隆慶時又遷原籍淄川東南山實基焉。”安氏先祖從始居般陽,后徙於陵,再因軍功修立海州而落籍,又最終回遷淄川,數百年間十幾代人輾轉多地,畫了一個大圓。此為安氏遷移的歷史軌跡,而道口安氏始祖即“失諱”者及其子孫卻渾然不覺,只知其原籍自海州遷莒,以至于在當時遭遇了科舉籍貫障礙,而大費周折。
(二)其祖安順禮始居道口
按於陵譜與道口譜皆稱,道口安氏自失諱者長子“文舉”之子“盈”于“明嘉靖、隆慶時又遷原籍淄川東南山中實基焉”。“盈”配王氏,繼配蔣氏,六子:尚仁、尚義、順禮、尚智、尚信、順德。此輩中,尚仁,無子。尚義,一子邦。尚智,無子。尚信,以族侄守強為子。順德,二子:仲、保。只有順禮一支人丁與科舉最盛。小傳稱:“順禮,行三,字敦五,號鄰黌,敕授文林郎、河間知縣,特贈河南道監察御史,累贈奉政中憲大夫、太仆寺少卿。配劉氏,累封太宜人、太恭人。五子:仕、傅、伸、偉、僎。女三:一適東華;一適張思義;一適蒲杞。公少有大志,謙讓能容,卒年七十四歲。苦節懿德載墓志行述。”《縣志·封贈》載其傳中除所封秩銜外,稱其“性恬退,與人無競”,并舉實例說明。更贊其“仲子令武強,迎養官舍,問讞獄有平反則喜,否則輟食彷徨立。既受封章服一御輒卻曰:‘食人之食者受人之事,乘人之車者分人之憂。一田舍翁,何功于上而服此稱?封君十余年,屋不加楹,田不加畝,而急人之難,未嘗以無為解。其為長者,行類如此。”從其號“鄰黌”看,知其已自淄川東南山中遷居道口村。道口位于淄川東北十余里的黌山東麓,原名大劉莊,即蒲松齡夫人劉氏故里。再從其婚姻看,“配劉氏,累封太宜人,太恭人”,知其不僅娶妻劉氏族中,更與岳家同居大劉莊。為安氏家族的振興奠定了基礎。
淄川道口安氏家族科舉的振興始自第十六世即“順禮”與劉氏所生五子(仕、傅、伸、偉、僎),其后綿延至子孫數輩,至二十余世未絕。以下打破排行順序,而按與安于拙的世系遠近簡要敘述之。
(三)其父輩安仕、安傅、安偉、安僎各家科舉仕途實況
安仕,譜載:順禮長子,號嵩盟,禮部儒士。子五(砥如、礪如、礎如,于蕃,礎如)。其初業儒,文藝已曉暢。因原籍系莒,為淄人所沮抑。弟傅已入庠,幾不得入科試,遂廢業。弟伸任河澗時,遙授禮部儒士。旦夕侍封公。諸葭莩有事,多來商榷。公曲為解,務得眾快,食少事繁,勞不可任。明萬歷辛亥五月十四日卒。可見安氏族人因原籍貫受阻于科舉之景況若此。然而其子孫輩卻不乏人才。“仕”之長子砥如,行一,字岐東,號道蒸,庠生,鄉飲大賓。不僅因子貴敕封文林郎、曲州知縣,而且“存心仁厚,己卯歲荒,鬻己田得價盡行周急,全活多人;又捐資設立義學,成就多人。”康熙丁亥歲邑侯題額曰“品行端方”,載在邑乘。所生六子中,除長子康,無功名外,次子舒,字斯玉,廩膳生,中式順治庚子科副榜;三子銳,字抑之(縣志稱“退之”),順治乙卯(縣志載“乙酉”)科舉人,丙戌科聯捷進士,授直隸廣平府曲州縣知縣,敕授文林郎;四子鐸,邑庠生;五子鏞,邑庠生;六子鐘,字禹年,庠生。“仕”之次子礪如,字華蒸,禮部儒士,子五。(所生五子中除三子宷、四子宜無功名外,長子盅、次子憲、五子寵皆庠生。而宷之長子“景興”與孫“詵”亦皆庠生)。“仕”之三子礎如,行七,無子。“仕”之四子碧如,行八,字和蒸,應試名于藩,庠生。傳稱“時盜賊不時竊發,公為練總,率民兵備御,閭里賴以粗安。”子二。其五子礎如,行十,子一。
安傅,順禮次子,字執中,號芹盟。明萬歷甲申游淄庠,己丑食廩餼,庚子科中式前魁。初任滕縣教諭,二任授國子監助教,三任歷刑部郎中,四任升河南衛輝府知府。誥授朝議大夫。配陳公智女,誥封恭人。子四:盤如、九如、硡如、鼎。葬于道口莊西。其長子盤如,行四,字泰蒸,庠生,一子,貞。其次子九如,應試名柱礎,行五,字廣思,庠生。子四。其三子硡如,行九,生三子。其四子鼎,行十一,字穎思,庠生,子二。以上“傅”傳按於陵譜記載,而道口譜中則詳記其科舉受阻細節。稱其“舉者遷淄草創,備歷艱辛。甲申游淄庠,眾忌紛起。時都中移文查核冒籍。會公幫補,淄人借口莒籍以相齮龁。公嘆曰:‘淄不我容,吾其莒也,莒跡又湮,計無復之。兄仕,弟伸、偉,自此罷讀。戊子公考第三,而功令無保結者,不準應試。公以未得保結,困衡萬狀。幸郡伯李公一意憐才,司教介石張公及茂才王君獻廷輩十余人相與申解,吳宗師批云:‘莒籍亦系本省,不妨應試。己丑公考第一,復以優行嘉。嘗時侮者在門,聞報至乃戢。弟伸、偉復理故業,未幾皆入泮。丁酉公考第一,弟考第六。”可見其當時窘況。
安偉,順禮四子,號藿盟,邑増廣生,改入國庠生。天性孝友。庚辰歲饑,賑粟煮粥,全活數千人。撫、按特加旌獎,撫臺蔣公題額曰“行高品粹”,按臺朱公題曰“名高月旦”。卒年八十有七歲。子三。長子石旬如,號黌村,行六,邑庠生。其次子大介,行十四,字天錫,原名岳。由歲貢生中式順治甲午科舉人。承父訓誡,心益凜、德益修、學益勤。中乙未會試副榜,署理萊州府高密縣教諭。敕授修職郎。子一繼振字幼癡,太學生。
安僎,順禮五子,號藻盟。由歲貢生中萬歷壬子科副榜。
以上知,安仕作為兄弟之長,因籍貫受阻科舉,僅以“禮部儒士”終,然其近侍父母并代理家政,且教弟讀,積勞成疾,以致早卒。其子孫輩大都進學,有舉人、進士、秩官,有善舉、益民、救世,不僅稱頌鄉里舉鄉飲大賓,且得邑侯題額旌表。安傅科舉初遇坎坷,而其矢志不渝,終以鄉試中舉,歷任數職,官至知府,光耀門楣。其子孫輩雖無大成就,然大都進學以繼書香。安偉以邑増廣生改入國庠,其因天性孝友,未能步兄長仕途,謹依母側,守家盡孝。而其災年賑粟煮粥,全活數千人,盛德感動撫、按,各加旌獎題額“行高品粹”、“名高月旦”。其子由歲貢生中舉,承其訓誡,再中會試副榜,任職教諭。孫輩中多人進學且習武,可謂文武雙全。其弟安僎,由歲貢生中鄉舉副榜,亦算學有所成。他們與安伸及其子孫輩共同構成了安氏族中龐大的科舉陣容,改變了家境,成為邑中名門望族。
(四)其父安伸事跡及其仕途遭遇
安伸,順禮三子,字振屈,號葵盟。生而魁梧,狀如耆宿。因播遷之際,室家草創,年十六始就塾。十九歲為文,輒出師右。乃從仲兄衛輝公學,是歲入泮。癸卯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歷任武強、河澗、陽城知縣。后任禮部主事,戶部江蘇司員外郞,山西道監察御史,河南道監察御史,升至太仆寺少卿。誥授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欽賜諭祭葬。卒年六十歲。元配婁氏(壽官婁守業女),誥贈恭人,晉階淑人,繼配姬氏,封恭人,晉淑人。子三(確如、于拙、于拯),女四(一適禮部儒士韓鳳起;一適知州王所須子鼎胤;一授右僉都御史高舉孫琮聘,早逝;一適兵備副使高捷子庠生瑞秋)。其臨歿時,病中寤語,潛聽之,皆公家事。倐而凈面南向,舉手如揖狀,曰:“此心不愧于朝廷,不愧于天地,雖我之罪未白,而知我之天自朗。”語畢遂逝。此按於陵譜記載,而道口譜中內容差異較大,除以上相同者外,歷官業績多為具體記述,更增加了因魏珰案蒙受不白之冤的細節。如初任武強知縣治理水患,調任河澗知縣厘革弊蛀,補陽城知縣遇旱禱雨輒靈的經過等,不再贅述。僅錄以下部分補充之:“逆珰久假叢神,中外脅肩。公獨抗然不投一刺。或曰:‘是將不利。公厲聲曰:‘俯首權閹,以博華膴,如萬代名節何!珰雖無以加公,而滋不悅。故公久當遷擢,僅以院咨加銜冏卿,珰阻之也。論者不察,至與獻媚速化者同科,豈不冤哉!后劾珰疏奏有曰:‘不拜生祠之強項,反遭無端之囊頭!語載縣志。旋里后,日聚順太恭人側,百凡可致。太恭人歡者,無所不致。公雖忠毅清直,而處事則物我無間。甚且寧己處其枯,而人集其苑,而后無憾。此固不勝縷述,僅志一二大概云爾。”以此可見其當年仕途中遭遇。
《淄川縣志·名臣傳》載其事跡稱:“安伸,號葵盟,萬歷丁未進士。初令武強縣,縣濱滹沱,漲則為災。公設法筑堤,邑永賴之。補陽城禱雨立應。擢授御史,巡視京通二倉,糾核侵耗,夙弊清焉。時有《議紅丸》一疏,當時服為確議。巡按山西,巡視皇城,厘奸剔弊。忌者以危辭撼公不為沮也。崇禎初,升太仆寺少卿,掌河南道事。初耿如杞以不拜魏珰祠下獄,公上疏白其冤,有‘不拜生祠之強項,反遭無端之囊頭等語,耿即獲昭雪。任陽城時,邑人為立生祠。后至康熙丁亥,又公舉入名宦祠。所著有《柱史草》、《黌麓漫吟》行于世。”
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中記載稱:“侍御居官清正,崇禎元年定逆案,乃列之魏黨。其兄為之辨云:‘當珰焰方熾,無不頌德歸功。每衙門有疏,通署列名,其人不必知,亦不必心愿也。文藏于家,不達于朝,人鮮知者。予觀《東林籍貫》、《盜柄東林伙》、《伙壞封疆錄》,皆有侍御之名。其為魏珰所惡久矣,安得謂之同黨?定案精審,猶有疏失,恐含冤者不止侍御一人也……侍御與余家相去甚近,故知之特詳。(思陵發建祠、稱頌諸疏,定案者姚希孟。)”王培荀,字景叔,號雪嶠,道光辛巳舉人,舉孝廉方正,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四川,歷署豐都、榮昌、新津、興文諸縣,癸卯鄉試同考官,特授嘉定府榮縣知縣。著有《聽雨樓隨筆》《鄉園憶舊錄》等書。其性鯁直,不喜濫交。出生于淄川豐泉鄉王氏家族。故居大窎橋,距離道口村僅數里之遙。因而其稱與安家“相去甚近”耳。
從家譜小傳與《淄川縣志》及《鄉園憶舊錄》中記載,可知安伸在崇禎元年定逆案時被列入魏黨實屬冤案,以致其仕途受阻,身心俱損,年僅六十即含冤離世。這在當時對于他這種注重名節且居官清正者的打擊可想而知,好在其身后能得以清白亦算幸運。
(五)安于拙及其兄弟、子侄與孫輩
安于拙兄弟三人,其為仲。長兄確如,傳稱:“行三,字鞏予,庠生。配許氏(許三戒女)。”過繼十三世文秀元孫世英之次子為嗣,名塵(道口譜名麈)。“麈”原名錞,傳稱:“字廉生。康熙乙卯恩貢,考授教諭,敕授修職郎。”其子六:景尹(字效伊);景向(字儕劉,庠生);景中(字又文);景敏(字亦遜,);景杰(還嗣本支);景孟(字淑圣)。
安于拙,行十三(其按父輩五人子嗣大排行)。傳稱:“字天能,號去巧。増廣生,舉優行,鄉飲介賓。工隸書。樸厚老成,享年近百歲。配朱氏(萊蕪縣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朱公童蒙女)子六。其長子纘,行一,初名念祖,字永言,府庠生,配孫氏、翰林院侍講、升刑部侍郎兼禮部尚書孫公之獬男、癸酉科舉人秠(即珀齡)女。”子二:景定(字慎先,増廣生),景藝(字同先,庠生)。其次子顯,字子亮,邑庠生。四子:景普、景寬、景喬、景羲。其三子繩,一子景曾。其四子素,字子郁,庠生,一子景昌字型先,號橦樸,庠生,不事生產,惟以讀書課幼為業,尤重墳墓修整、心親祭掃以時,善丹青,至今親族保重之。子三。其五子纟勉,字子強,庠生,一子景瑗(子四)。其六子緇,字子宜,庠生。二子:景博(武庠生);景龍(武庠生)。
于拙之弟于拯,行十五,字龍圖,庠生,一子綸。綸字子經,監生,五子。其長子景富。其次子景賢(字智先,武庠生,)。其三子景度(武庠生,)。其四子景襄(字君弼,監生,)。其五子景有(字若先,三子)。
以上看出,安于拙兄弟三人皆入學,且子孫人丁興旺,不乏科舉人才。其兄確如無子,過繼族兄世英次子麈為嗣。而麈不辱使命,不僅自己以康熙乙卯恩貢考授教諭職,而其六子中景向,也已入學。于拙本身壽近百歲,以増廣生舉優行,享譽邑中舉鄉飲介賓。所生六子中除三子繩未入學外,其余五子纘、顯、素、纟勉、緇皆入府、邑庠。其孫輩中入學者有纘子景定、景藝;素子景昌。而緇子景博、景龍皆入武庠。再下一代中景藝之子處善為監生,景昌次子立善為邑庠生。于拙一支四代人中有監生、府、邑庠生、武生十二人。其弟于拯之子綸乃監生。孫輩五人中除景富、景有未入學外,景賢、景度皆武庠生,景襄為監生。再下一代中景富嗣子生善乃監生,景襄四子欲善受恩賜八品頂帶。于拯一門四代人中不僅有兩監生、兩武生、一庠生,還有一位受恩賜八品頂帶者。如此算來,安于拙兄弟三人及其子孫后輩四代人中共有貢、監、庠生、武生二十余人,其中有考授教諭官職者,有受恩賜八品頂帶者,有邑舉鄉飲介賓者。雖不能與先輩安伸兄弟業績相比,但也未辱書香門風。他們沒在先輩所遭冤案的陰影下沉淪,而都在按各自的人生目標軌跡,體現著不同的人生價值。
三、蒲松齡與安于拙的交情
從《聊齋詩集》卷四丁亥年《寄十三兄去巧》詩中知,丁亥乃康熙四十六年(1707),蒲松齡已68歲,年近古稀。而詩中稱安去巧“方瞳紺發九十余”,家譜稱其“享年近百歲”,縣志稱其“壽九十五歲卒”。兩人年齡相差最少也有二十多歲,將近一代人的時光。他們是何關系又為何產生交往,且還稱兄道弟呢?要解迷團,還得從頭說起。
(一)蒲安劉家族聯姻乃二人交往契機
從家譜小傳知,安去巧祖父母順禮與劉氏共生五子三女。其長女適東華,次女適張思義,三女適蒲杞。蒲杞何許人也?這需要查證蒲氏家譜。從其名看杞字從木旁,應與蒲松齡父槃同輩。蒲父兄弟五人各名木急、樉、槃、柷、棐,無名杞者。蒲槃父生汭,行四,兄弟五人,其兄生澤、生溪、生洙與弟生沇所生七子各名汝風、汝松、木實、桾、椿、桓、杜,亦無名杞者。而蒲生汭父繼芳,行二,其兄續芳,弟紹芳,四弟聯芳,皆世廣之子。聯芳一子生洛;紹芳三子:生沼、生浦、生汶,他們子輩效魯、效伊、棯、棫中無杞名。續芳三子:萌、生池、生渠。其孫輩杞、楩、柟、樾、棟、栝、榷、榧、杔九人,杞乃長支長孫。譜中詳記“萌,劉氏、姚氏,任襄陽府□縣典史,生一子杞。”“杞,安氏、孫氏,清耆老,生三子:兆奎、兆寅、兆福。”以上所引,出自《蒲氏族譜》蒲松齡親筆書寫(影印)本無誤。
按支系輩份看,蒲槃與蒲杞同為世廣曾孫,各自的祖父是親兄弟。蒲松齡作為蒲杞的侄輩,并未出五服,是世廣一支中一分為四的次支傳人。蒲杞元配安氏乃于拙姑母,又是蒲松齡從伯母,這就使其娘家侄于拙與夫家從侄松齡成為表兄弟關系。從而兩人之間就有了交往的機會。聊齋詩《寄十三兄去巧》中“弱冠東去近精廬,得睹顏色親華腴。君攜壺酒同歡娛,座上和風吹四隅”就透出了這方面的信息。
蒲松齡與安于拙的交往始自何時呢?按詩中“弱冠東去近精廬,得睹顏色親華腴”看,應在安于拙中年,亦即蒲松齡“弱冠”之年近20歲時的清順治十五年前后。正值蒲松齡前一年與劉氏成婚,婚后次年即參加童子試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大振之時段。這也正應了詩句“君攜壺酒同歡娛,座上和風吹四隅”所描寫的當時氛圍。若無蒲劉成婚因素,即無其“東去”岳家大劉莊與安氏會面機會,若非其童試成名,難言“同歡娛”場面,此中大有安氏為其慶賀之意。故二人首次會面應在此時。蒲松齡岳家劉氏與安氏家族同里,且安劉兩家早有聯姻,安于拙祖父順禮即劉家女婿。于拙父輩五人與姑母三人皆劉氏所生。因而安劉兩家親情密不可分。安于拙姑母嫁于蒲杞,成為松齡從伯母,安蒲兩家也成姻親。蒲松齡東去大劉莊登岳父家門,同時到表兄安于拙家拜訪作客,便順理成章。
由此不免令人產生聯想,當年蒲劉婚姻是否與安氏有關?筆者經過分析史料,認為不無可能。此種觀點基于當時蒲松齡家境不富裕,非有眼光且了解實情者出面,是難以說動女方家允的。《聊齋文集·述劉氏行實》中就有當年蒲劉定親記載,其稱:“劉氏,蒲松齡妻也。父文學季調,諱國鼎,文戰有聲。生四女子,松齡妻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效陶、鄧,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去而學賈,積二十余年,稱素封。然四十余苦無一丈夫子。不欲復居積,因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是宿儒無其淵博。而周貧建寺,不理生產。既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每十余齡,輒自教讀;而為寡食眾,家以日落。松齡其第三子,十余歲未聘,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或訾其貧。劉公曰:‘聞其為忍辱仙人,又教兒讀,不以貧輟業,貽謀必無蹉跌,雖貧何病?遂文定焉。順治乙未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堅,亦從眾送女詣婿家,時年十三,姑董與同寢處。訛言既息,始移歸。又二年,始行御輪之禮……”。
劉氏十五歲嫁進蒲家,隨夫艱辛度日,為其生下四男一女。而夫常年游學在外,劉氏固貧寂守,獨撐其家,苦心經營,不廢兒讀。待夫晚年撤帳歸里,始得常聚。然不數年便因病先逝,讓蒲松齡痛心不已,僅年余亦即隨之而去。《述劉氏行實》洋洋千余言,飽含深情,盡詳劉氏一生經歷與賢德。以上所引部分,忠實記述了蒲松齡婚前家境以及與劉氏定親過程,尤其是劉家有人“訾其貧”時,而劉公國鼎卻態度堅定的應允了這門親事。
一般說來,兩家定親由媒人出面介紹,只是走過場的形式而已。事實上,男婚女嫁乃終身大事,負責任的雙方家庭事先都會充分了解對方情況,包括年齡、長相,性格、家境等各個方面。也有可能會找底實的知情人出面溝通,遇到難題甚至還要反復協商。對于普通窮困家庭而言,要求相對會簡單些,而對于那些有權勢的大家貴胄或者很殷實的書香人家,則會很挑剔且講究門當戶對。尤其女方會更加謹慎,唯恐選擇失誤,日后受苦、受累、受氣,難言幸福。
據《淄川縣劉氏族譜》清道光二十一年創修刻本記載,其“一世,始祖佐,行二,配魏氏,子一,自章邱回村遷居淄川大劉莊。”按譜中世系,始祖佐即國鼎祖父。而民國二十一年續修《劉氏支譜》抄本,系據塋田出土石碑記載遷自章邱后,赴原籍章邱續譜結果,其“一世,甫廣(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前明洪武間遷于冀州棗強劉家莊,永樂間又遷于章邱城里新街)子四(江、海、貴、讓)。二世,江(兄弟四人同遷于洄村河北,名劉家四戶,以后支分派別,族人眾多,遂居數處,不止一方),子一,寬。”以下延至“七世,春芳(偉次子),子二(文舉、文學,兄弟二人由章邑洄村遷于王村,遷于淄川城東北大劉莊)。八世,文舉,子一(佐)。九世,佐,配魏氏,合葬于莊西,子一(善)。”“始祖佐”,降為九世。“十世,善,佐子,配宋氏、陳氏、黃氏,合葬于泉子莊南,子八(盛揚、澤遠、明遠、國鼎、芳遠、裕遠、蔭遠、慶遠)。”而道光刻本中“二世,善”配氏、子嗣記載相同,只是在“明遠”名后注明“行三,庠生”。“三世”中“國鼎,行四,庠生,配崔氏,子三:○、樛、果”之記載,與民國譜抄本同。其中都有蒲松齡岳父“國鼎”記載,且知其為八兄弟中之行四,其兄“明遠”亦為庠生。可見當時劉家兄弟眾多,家大業大,并出了兩位庠生,名副其實的書香門第。當媒人登門時,劉家有人嫌蒲氏家貧,也在情理之中。而“文戰有聲”的劉國鼎擇婿肯定有標準,然其深知蒲槃家世,也知曉松齡人品,相信日后會有轉機,便力排眾議,聲稱:“雖貧何病?”遂文定焉。
按蒲松齡親手修訂的《蒲氏族譜》記載,其高祖世廣一支科舉最盛。自七世高祖世廣至十一世松齡同輩五代人中共有27人入泮,其中有舉人、貢元、進士,任職知縣、訓導及雜職者,不乏其人。這在當時當地可稱得上名門望族。盡管蒲槃與其父輩兩代人未能入泮,稍感落伍,然而其恪守儒業,希冀子孫光宗耀祖的夙愿未泯。因此為兒輩擇偶的標準不會降低。當“聞劉公次女待字”時,便成為蒲槃為子松齡征婚的首選。
蒲家莊在淄川城東七里處,距離偏東北方向的道口即大劉莊約十華里內。蒲、劉兩家的訊息互通存在一定的便利條件,且兩族間早有聯姻(《蒲氏族譜》中多有娶妻劉氏記載)。因此,蒲槃子松齡“十馀歲未聘”,劉國鼎“次女待字”的訊息都會有所耳聞。然而訊息傳聞有了,即使兩家都有意愿,也總得有熱心者從中串聯才行。這位串聯者不僅對雙方家境、人品等情了如指掌,還要知其價值取向與未來趨勢,更要有一定的權威性,即言出眾服的能力。這一角色,不是一般人所能充當的。依筆者觀點,只有蒲杞元配安氏與其侄于拙能勝任此役。其一,安氏乃御史安伸之妹,其夫蒲杞乃蒲槃從兄,作為蒲杞之妻,不僅了解蒲氏家底實情,更知蒲槃之子松齡人品及擇偶標準,其說話會有一定分量。其二,安氏之母出于劉氏家族,作為劉氏甥女,其既知劉氏家世,亦有蒲氏代言人資格,為外祖族中表侄女推薦夫婿人選,會有很強的誠信度。其三,安氏之侄于拙,乃安伸之子,既在本族中有相當地位,也會在本莊外祖家族表兄弟中有一定影響,若代姑母安氏轉達蒲家意愿,也是最佳人選。無論當時蒲、劉兩家誰占主動,唯此安氏與其侄于拙二人才能讓蒲槃“聞劉公次女待字”而心動,能使劉公國鼎不顧家人反對說出“聞其為忍辱仙人,又教兒讀,不以貧輟業,貽謀必無蹉跌,雖貧何病”的通情達理之語而應允定婚。舍此姑侄,無能任者。
(二)蒲、安二人交往始末
按家譜史料記載,蒲松齡與安于拙的表兄弟關系,自蒲杞與安氏成親即已存在。然而兩人正式會面應如前所論始自蒲松齡成婚且以縣、府、道三第一入泮之后。聊齋詩《寄十三兄去巧》中“弱冠東去近精廬,得睹顏色親華腴。君攜壺酒同歡娛,座上和風吹四隅。”數句述之甚詳。繼而詩稱:“我累口腹緣諸雛,爾日分衿音載疏。白帢蒙塵履沾濡,別時年少今垂胡。古稀垂近老且癯,齒牙搖動霜上須。逢人問訊見君無?云復矍鑠豐采都。”自“爾日分衿”至此詩寫作的“古稀垂近”之年,時間跨度近50載。作者由“別時年少”至“今垂胡”,雖既“老且癯”,又“齒牙搖動”須發白,但仍不忘舊友,“逢人問訊見君無?”而此時的安去巧卻如詩中句稱“方瞳紺發九十馀”,“顏如映日紅芙蕖。衍波箋上飛明珠,綰蛇縈蚓為細書。行步便捷如凌虛,君獨何修壽容舒?”以故被問者便答復云其依舊“矍鑠豐采都”。因而作者竟“嘆想飛越夢蘧蘧,我遽登門傳相呼。未知猶能認故吾?倚仗大笑握長裾。應或仿佛辨形模,向坐傾談古道迂。二老刻燭為贏輸,麈尾揮落快何如?”夢想再與安氏重逢懷舊暢敘友情。可知二人自初見分別后很少會面,而關系卻一直未斷。雖相差約25歲左右,且各自家庭、遭際不同,然兩人感情融洽親切,始終如一。詩中所言“音載疏”,而仍有來往。如聊齋詩《題安去巧偕老園》即其例證。
上詩寫于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作者36歲。從詩題看,是專為安氏偕老園所題。偕老園遺跡今已難覓,但從描寫環境與實況分析,范圍當不出道口村西附近。此處西面緊鄰黌山與梓橦山,符合“青山入室人聯座”,“高眠人在碧山深”以及“鹿門蹤跡今何在?豐草白云更可尋”與“門前春色明如錦,知在桃源第幾家”的情景氛圍。此時安于拙已年過六十,或居舊第或辟新園,額稱“偕老”實不為過。其妻朱氏系萊蕪縣曾官任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朱童蒙之女,乃大家閨秀。為安氏生育纘、顯、繩、素、纟勉、緇六子,再加孫輩、曾孫輩中共有12人成為監生或文、武庠生。安于拙感佩不已,因生摯其手共白頭之念而名其園。當時蒲松齡肯定來過此處,或自愿或被邀為偕老園題詩,都在情理之中。其親臨其境,見剛歷花甲之年的安氏“蒜發蕭蕭白映簪”,而其子孫已“成林”入學。其夫婦相伴優游林下飲酒作詩,猶如古賢者隱居鹿門山一樣閑適。清晨周圍“柳線絲絲帶早霞”,隨著日升則有“婢子煮新茶”侍奉。開門“青山入室人聯座”,入夜則“白發連床月上紗”。不僅有兒孫笑語圍花徑,更有石亭以供“棋酒話桑麻”。安氏偕老園儼然一處世外桃源、人間仙境。讓久處窘困之中的蒲松齡羨慕不已,便將自己對安氏的滿腔熱情以及對其居第的贊美之意,傾注于該詩之中。
除上述例證外,尚有一事還須提及,即縣志《鄉飲》篇所記載的安于拙事跡中有“邑侯張公舉鄉飲介賓”之語。說明安于拙是由縣令張嵋任中舉為鄉飲介賓的。《淄川縣志·續秩官》載:“張嵋,字石年,仁和人,貢監。康熙二十五年任。精明有才干,邑中百廢俱舉,雅意文獻,邑乘重修。于二十八年升任鞏昌府同知。淄人同故明吳江沈公立祠尸祝之,號曰‘沈張二公祠”。
張嵋任淄川三年,政績顯著,受百姓愛戴,聊齋詩中亦多稱頌者。如《和張邑侯過明水之作》(七律八首)、《送別張明府》(七律三首)、《悲喜十三謠》(七絕十三首)等。聊齋文《呈石年張縣公俚謠序》末段所稱:“初入驛舍接清塵,榮已擬于下榻;再向荒階迎玉趾,跡直近于式廬。方欲識荊,傾風自想;遂勞說項,戴海難戡。抱刺三年,舊篋開而滅字;歔枯片語,寒谷變而生春。踐阮籍之窮途,方將涕淚;邀孫陽之小顧,便欲驕嘶。漫擬《擊壤》之謠,聊代稱觴之祝。”以及聊齋詩中“小結茅廬孝水陽,郵亭初接令公香。”“但得孫陽雙眼顧,寧教陸氏一莊荒。”“三年久借韶光拂,兩世同被化雨榮。”“衡茅三載浹恩光”等語句都透出作者與張嵋之間關系非同尋常。蒲松齡與其長子蒲若都曾在學業上得益于張嵋的幫助(即為其“說項”)。而張嵋也樂與蒲松齡交往且征聽其建言。甚至當其擢升甘肅鞏昌府同知離淄赴任前即請蒲松齡代筆《上鞏昌府知府書》,可見其對蒲氏的信任及對其文筆的賞識。而蒲有事亦請張幫忙,如《與邑侯張石年(嵋)》文末稱:“有瑣陳者:某約所舉息爭鄉約王憲侯者,其設帳治弟之家已三年矣,實恐救鄉鄰之斗而誤童蒙之求,祈老父臺分推屋烏,準與豁免,則銜恩者不止王生也。伏惟電照不宣。”
由此,筆者推測,安于拙當年被舉鄉飲介賓之事,有可能得蒲松齡推薦之力。《淄川縣志·鄉飲》記載,先后有12人小傳簡介在冊。其中提及由某“邑侯舉”者只有三人:安于拙、李堯臣、李堯佐。舉李堯臣的邑侯吳公,乃吳堂,華容人,庚辰科進士。其四十九年任淄川知縣,五十年丁憂。李堯臣的鄉飲介賓是蒲松齡舉薦的。聊齋文中有《舉張拔貢歷友(篤慶)作大賓呈》與《舉李希梅作介賓呈》即當時薦書。雖縣志《鄉飲》未載張歷友之名,然聊齋詩《張歷友、李希梅為鄉飲賓介,仆以老生參與末座,歸作口號》所云:“憶惜狂歌共夕晨,相期矯首躍龍津。誰知一事無成就,共作白頭會上人。”足可證實。而舉安于拙為鄉飲介賓的邑侯張公,即張嵋無疑。因自其康熙二十五年任淄后至雍正間再無張姓知縣。按蒲松齡與張嵋間的信任關系,推薦安于拙為鄉飲介賓事,易如反掌。只要蒲發話,張不用再聽別人意見便可決定。因為安于拙的門第及其自身條件,無可爭議。若有議定過程,邑侯表態,即獲通過。蒲松齡對于安于拙的感激之情終生難忘,作為投桃報李,蒲也應對安有所表示。既然有此機會,何不作順水人情?無論二者誰占主動,都無可厚非。舉為鄉飲介賓,即可遂安氏心愿,又使蒲心意遂,可謂兩廂情愿,皆大歡喜。當然這種事情不可對外宣揚,也無須留下記載,涉事三人皆心知肚明。蒲、安二人可謂心照不宣,邑令張嵋則各遂其愿。
大約蒲松齡寫《寄十三兄去巧》詩以后兩三年內,安于拙離世(壽95歲)。卒年當在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前后。此時蒲松齡已70歲,其妻劉孺人也已67歲。越四年即五十二年癸巳(1713)九月二十六日劉孺人病歿。僅隔年余,至五十四年乙未(1715)正月二十二日酉時,蒲松齡竟依窗危坐而逝。
綜上所述,蒲松齡與安于拙(去巧)的交游,涉及蒲、安、劉氏三個家族。須由聊齋文獻入手,參閱地方史志及各家族譜史料,逐一展開梳理,從“聊齋詩與安去巧”、“安于拙
家世探討”、“蒲松齡與安于拙的交情”三大部分進行論述并再分為多個分題詳加研討,理清脈絡,力圖說清蒲、安、劉三家族間的聯姻關系,最后落實到蒲、安二人的交往契機與交往始末。其間穿插安氏在蒲松齡與劉氏定親過程中的作用,蒲松齡與縣令張嵋的關系以及薦其舉安于拙為鄉飲介賓之事,完成蒲、安二人交游論述全程。
值得提及的是,該稿所引安氏兩部家譜實屬重要的歷史文獻,可補淄博地區明清以前至宋、元時期原住民史料之缺。其提供者安盛山先生,乃安去巧直系第12世孫,長期熱心家族史料并整理完善及刊印。其不僅有功于族內先人與后輩,也有利于地方史料的保存與研究,更為弘揚聊齋學及其文獻的完善作出貢獻。
筆者在此謹致謝意!并以拙稿敬獻讀者,以俟方家教正。
(責任編輯: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