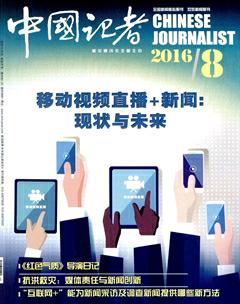面對亂象與迷離:藝術家報道的誤區與應對
趙越
內容提要 一些媒體開設了書畫藝術板塊,向廣大受眾傳播書畫知識,推介書法家、畫家,引導藝術品收藏與投資。與專業的美術、書法類刊物不同,大眾傳媒中的書畫版采編人員往往并非專業出身,也很少有人經過專業培訓,對藝術家及藝術品的評價定位往往失之偏頗,甚至誤導讀者。如何避免這些誤區,本文作者自2003年起在省級門戶網站上開辦書畫版面,在多年的工作中與諸多書法家、畫家深入交流,積累了較多經驗,也有一些教訓。
關鍵詞 書畫藝術 藝術品 藝術傳播 門戶網站
在采訪藝術家的過程中,被采訪者往往會提供一些資料以供參考。與權威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的新聞素材不同,由藝術家個人提供的資料往往是個體主觀意愿的產物,需要進一步甄別。另外,需要客觀評價當代書畫家。當代書畫家還沒有進入歷史定論的范疇,所謂大浪淘沙,走在這個時代的龐大的藝術群體還有待藝術史的篩選。即便其中有初露鋒芒的佼佼者,也需媒體客觀、中正地評價。同時,要以發展的視角看待問題,對同代的藝術家盡量不定論。
一、“大師”稱號需要歷史檢驗不可隨意使用
經常有讀者問:“目前在報紙、廣播、電視宣傳中常有書法家、畫家被冠以‘大師稱號,當今時代真有這么多的大師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史為鑒——元代百余年,僅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四位畫家被稱為“元四家”;明朝近三百年,僅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位畫家,被稱為“明四家”。也就是說,經過時間的沉淀,一個朝代僅有幾位畫家可被稱為“大師”。當代畫家是否能得到歷史的認可,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和篩選,如果僅因其取得一些獎項和成就,便以“大師”稱之,實乏嚴謹之態度。
在十幾年的采訪經歷中,我注意到一種普遍現象,凡江湖中略有書畫技藝者,往往自稱“大師”,或以弟子相擁營造氣勢,或通過非公開發行的印刷品自我炒作,或把自己的作品附著在當代名家作品后結集出版。而真正執著于藝術本身的書法家、畫家卻恥于被冠以“大師”稱號,他們會認為這種不嚴肅的吹捧是對其藝術精神的褻瀆。
二、要鑒別榮譽稱號的授予機構是否具有權威性
在我國,藝術領域的權威性機構包括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及其下屬的各省級、市級分支機構,還有在教育部注冊的美術院校、文化部認可的文博單位等等。
在采訪中,筆者曾經歷過一些藝術家自稱獲得過“聯合國世界和平文化使者”“世界杰出華人藝術家”“中國社會名人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名人藝術研究院企業名人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研究員”“中國書法協會理事”“省書畫家聯合會會長”等稱號。且不論當事人獲得這些獎項的真實性,僅就頒獎機構的專業性而言,便是象征意義大于藝術水平的。而藝術機構的名稱也有商業領域“仿名牌”的現象,比如上文提到的“聯合國世界和平文化使者”便不同于“聯合國和平使者”;“省書畫家聯合會”作為民間組織,既不同于“省文學藝術聯合會”,也不同于“省美術家協會”;而“中國書法協會”與“中國書法家協會”更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真正的權威機構由國家設定并認可,而以群團組織在民政部門注冊的各種民間藝術機構,資質水平相對遜色。
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與藝術作品水平的高低無必然聯系。比如,一項藝術創作參與人數最多、篇幅最長、尺寸最大,都可以申報并獲得“吉尼斯之最”,這種評價標準與藝術水平沒有關聯。
三、認定歷史名人的后裔要有切實依據
在十幾年的采訪中,我曾有過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見聞。一位王姓書法家曾說:“我年過五旬,仍未有驚世之名,只因過于老實。十年前,便有文化公司負責人建議,‘你既姓王,何不自稱明末大書法家王鐸后裔?以引起關注,便于宣傳炒作。”好在這位書法家為人誠實,婉拒了對方“美意”,但藝術界興此之風,的確令人憂心。
更有一位衛姓書法家自稱“衛爍第72代孫”,衛爍是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其生活年代距今1600余年,若考證其真偽確有難度。可是其自己提供的材料實在漏洞百出,竟有“國務院定價潤筆10萬/平方尺”的字樣,讓人對其與衛爍的關系也只能一笑了之了。
筆者在赴江浙一帶采訪時,經常會聽說某人是王羲之后裔、某人是文征明后裔,等等。在采訪中遇到此類情況,不可盲目認可。且不說歷史名人后裔的身份需要祖傳家譜及戶籍部門的驗證核實。即便此人確為名人后代,其藝術造詣也需單獨評判,因為藝術的傳承并不以血源關系為依據。
四、以作品藝術含量為準繩不渲染創作過程
書畫藝術有別于歌舞、戲劇及其它舞臺表演藝術,創作過程及創作者的肢體動作不能計入藝術評價范疇。
近年來,經常在報刊上看到所謂“懸腕書法創始人”“懸筆書法開創者”等相關報道。更有江湖中人,大肆渲染書畫創作過程,寫字時或運氣發功,或搖頭擺尾,花樣之多,不勝枚舉。一些剛入行的媒體人也往往被其所惑。
事實上,藝術最根本的價值在于藝術作品本身,而不在于創作過程是否具有表演性,更不在于表演是否精彩。“懸腕”和“懸筆”僅僅是書寫過程中的姿態而已,與書寫者水平的高下無關;氣功和武術精彩與否,也不能決定書法作品的優劣。
同理,書畫作品的另類展示也不能作為評判藝術價值的依據。2014年,在各大媒體上喧囂一時的《中國首例直升飛機運載“中華龍”驚現四川敘永》新聞,記錄了直升機在四川瀘州市敘永縣半山降落,并在落地之后徐徐展開一幅“價值千萬”的書法長卷。作為一條社會新聞,這的確能夠吸引眼球。但從藝術角度看,則有值得商榷之處:盛大的展示過程與藝術作品的價值并無因果關系,說其“價值千萬”恐怕證據不足。
五、要認識到不是所有的獨特風格都具有審美價值
2015年,某報登載的書法家作品《當代亂書》令人瞠目——只見尺幅之上,筆墨橫飛,或糾纏一處,或孤懸一線,墨色糾纏,一字難辨。筆者恐一己之見不足為據,持報請幾位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評點。一見此作品,他們皆眉頭緊皺,嘆息連連,更有嚴厲者批評此類媒體,不分良莠,沒有選擇,誤導讀者。
近年來,為了追求與前人不同,標新立異、吸引眼球,有些書畫家胡寫一氣,亂畫一番,遠離了中國傳統的書法、繪畫之審美范疇,而媒體對此類藝術家及藝術作品的報道則為虎作倀,助長了這種行為。
追求自己的藝術風格是值得提倡的,但新聞媒體要傳播審美范疇內的獨特風格。如果脫離了審美的界限,丑得再有風格,也是沒有審美價值的。藝術鑒賞家壬季遷先生曾表示:“中國人鑒賞書畫必須具備一門知識和經驗,即筆墨的問題。”
書畫版面的采編人員應在工作中加強學習,熟悉筆墨關系,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萬不可以丑為美,將宣傳陣地拱手讓位于個別人錯誤的藝術嘗試。
六、準確評價不以浮夸之語奪人
在大眾媒體對書畫家的報道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表述。一位知名畫家曾笑問記者:“現在書畫界還有新聞嗎?書畫家自己準備的通稿,記者轉手即發。”這一問令人心痛,也發人深省。
某新聞網站書畫板塊在對中青年書法家的報道中頻頻出現“形神兼備,瀟灑飄逸,構圖別致,耐人尋味”等毫無個人特征的語言;而史書上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飄若浮云、勁如蛟龍”,也被隨意用在評價當代書法家的文章中。
以某媒體刊發的文章《速寫一生寄情山水》為例,文中對畫家的作品評價多見“氣勢宏大、創意獨特、技法新穎、空靈雋永、含蓄蘊藉、迷遠飄渺、奇妙幻境、雄渾幽深……”等用語,泛泛而無所指,無法體現出畫家的藝術特色。
語言空洞、任意拔高成為目前書畫版面的“常見病”,有讀者甚至戲言,一篇文章,套用到幾位書畫家身上,只要換個名字,都不會出現太大紕漏。
這一方面可能源于被采訪者的藝術水平平庸,不值一書而勉強作文;另一方面則說明我們的采編人員沒有潛到藝術深處,發掘藝術創作者的藝術特色。
“康德說,美是對功利的刪除。”書畫版面的采編人員在寫文章時,應放下功利之心,不宜對被采訪者拔高放大,追求“一鳴驚人”的宣傳效果。
七、借助權威機構把關準確把握獎項的學術含量
在這個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時代里,絕大多數都是非美術專業出身的編輯、記者應如何判斷藝術家的藝術水平,把真正有價值的藝術作品傳播給廣大受眾呢?筆者認為,當在某個專業領域自身判斷能力不足時,可以借助這個行業中專業人士的評判——被采訪者曾獲得的獎項,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標準。
但如今各類獎項充斥社會,其中不乏商業運作、個人炒作等含有雜質的“藝術活動”。哪些獎項含金量較高,學術水平較強呢?
根據筆者多年觀察,在美術領域,由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每五年一屆的“全國美術作品展”(簡稱“全國美展”或“屆展”)是美術界無可爭議份量最重的獎項。曾在“屆展”中獲得金、銀、銅獎項,甚至入展都能體現美術家扎實的藝術功底和卓越的創造力。緊隨其后的,是三年一屆的“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覽”和兩年一屆的“北京雙年展”。如果一位美術家曾經獲得以上活動的獎項,說明其具有相對穩定的藝術水準。再次之的,是由全國美協或各省級美協主辦的其它美術活動及獎項。
在書法領域,最無爭議的獎項當屬“中國書法篆刻蘭亭獎”。這個獎項是經中宣部批準,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中國書法藝術最高獎,是18個國家級文藝獎項之一,也是書法藝術創作者的最高榮譽。略遜之的,是由中國書法家協會舉辦的其它書法活動及各省級書協舉辦的省級“書法篆刻蘭亭獎”。這些獎項的評委都是多年在全國或全省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可的專家、學者,其自身治學嚴謹、評選也比較專業。
除以上獎項之外,有一些展出單位由于藝術積淀深厚,對作品的要求也比較高,例如中國美術館、中華藝術宮以及各省級美術館;國家博物館和以首都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為代表的各省級博物館。在以上美術館、博物館舉辦過個人展覽的書畫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可信度。
除以上問題之外,新聞工作者還要注重職業操守,尊重藝術本身的價值,不因個人利益而褒貶,不為種種誘惑所動。(作者單位:東北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