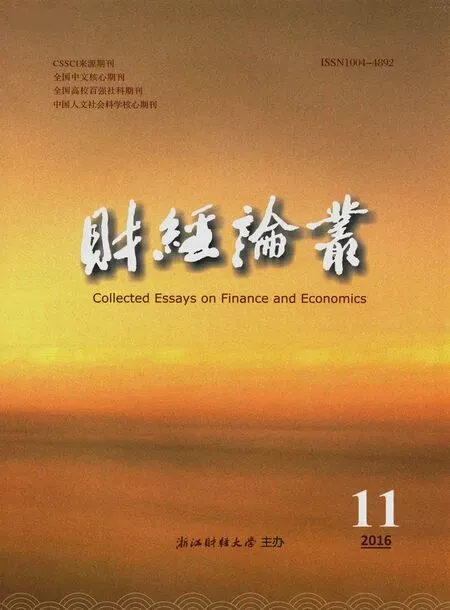網絡建構視角下核心企業網絡權力與企業間領導力生成研究
——基于“大淘寶”網購平臺案例
吳昀橋,郝 斌
(1.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083;2.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上海 200237)
?
網絡建構視角下核心企業網絡權力與企業間領導力生成研究
——基于“大淘寶”網購平臺案例
吳昀橋1,郝斌2
(1.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200083;2.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上海200237)
通過對單一企業網絡縱向案例研究,本文探討了企業間網絡中核心企業網絡權力與企業間領導力的動態變遷。研究發現:核心企業在網絡拓展中形成了網絡權力,這種權力會隨著生態企業網絡的發展而逐漸演化,且這種動態網絡權力配置較好地維系了企業間協調機制的有效性;過于強大的網絡權力降低了核心企業行為對伙伴企業的意義建構性,進而影響到企業間領導力的提升。為此,核心企業只能通過正式權威的建立,在不同時期分別形成技術、平臺和制度層面的領導力。本研究較好地彌補了依托對稱性網絡結構而形成的關系管理理論解釋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可以引導非對稱性網絡結構下企業間關系理論研究的深化。
企業間網絡;核心企業;網絡權力;企業間領導力;商業生態
一、引 言
聯盟合作與企業間網絡的日益盛行,驅使網絡管理成為企業搶占市場機遇、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路徑。近年來,大量研究聚焦于此,從不同角度闡釋了企業網絡管理策略及其效能機制[1][2][3]。其中,企業間網絡管理的關系視角強調持續性、嵌入性網絡關系在協調網絡資源、管理網絡活動中的作用,企業之間通過信任、承諾、依賴等方式相互聯結,關系規范和市場信譽進而成為約束伙伴企業行為的主要手段[4]。與之相對應的契約理論視角則質疑非正式關系的約束效果,認為私利會成為企業打破關系平衡的誘因,企業只有通過締結正式契約,才能夠有效管理其伙伴企業[5]。而從網絡知識管理與分享的角度看,協調與溝通作為即時互動機制,能夠促進企業間知識共享與利益整合,進而培植合理有序的網絡關系[6]。網絡管理的伙伴選擇視角則認為,伙伴企業的管理不應該是一個單純的事后行為,需將網絡管理的內容嵌入到前期的伙伴選擇中[7][8]。這些研究視角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場,也形成了各自獨立的邏輯體系,但卻共享同一個隱含假設,即企業間網絡是基于資源交換或能力互補而催生的平等合作機制。
然而,在產品內分工日益細化、企業間協作動機愈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企業間網絡中的平等關系開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非對稱性的關系結構及其催生的企業間網絡權力[9]。其一,企業間資源的非對稱性依賴關系開始成為跨企業邊界合作的常態;其二,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通過搶占網絡中心位置來贏得結構性優勢和利益分配權;其三,市場競爭已經逐漸演變為企業網絡之間的競爭,少數大型企業成為中小企業賴以依托的競爭領導者。在非對稱性網絡關系下,傳統的網絡管理理論顯然難以解釋核心企業的網絡行為及其管理策略,故對企業管理實踐也難以提供有效指導。此類問題的出現,引發了少數學者的關注,并開始將研究視野聚焦于核心企業的網絡構建與管理[10][11]。諸如,Dhanaraj和Parkhe在其開創性研究中,將核心企業的網絡管理總結為三方面的活動:管理知識流動性、管理創新可獲取性、以及管理網絡動態性[2];Paquin和Howard-Grenville基于核心企業能力與行為的演變,分析了非對稱性網絡管理的動態性[3];Perrons則通過對Intel的案例分析,展現了核心企業利用網絡權力來協助合作伙伴開展技術創新的動態過程[9]。但較為遺憾的是,由于相關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主流文獻還未能形成一致而清晰的邏輯分析框架與理論體系。
通過對當前相對較為有限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分析,可以發現,作為網絡的領導者,核心企業需要利用網絡權力來管理跨邊界的業務活動,其在整個網絡中的影響力左右著合作伙伴的利益和企業間網絡的價值創造。此時,核心企業具備了引導、控制和協調其他網絡成員企業的領導者權威和非正式權力,即企業間領導力[12]。具體而言,企業間領導力是指聯盟網絡中核心企業對成員企業的影響力,核心企業通過探索聯盟發展方向、整合聯盟資源與目標、協助解決成員企業困難、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與聲望來引導和影響聯盟其他伙伴企業,并促進聯盟成功。為了更好地探索核心企業利用網絡權力培育并管理企業間領導力的內在機制,本文引入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試圖通過對案例企業的歷時性分析,重點回答以下問題:核心企業如何通過網絡建構來強化自身網絡權力?網絡權力如何作用于核心企業的網絡地位,進而催生企業間領導力?
二、理論基礎
從關系交換的理論視角來看,網絡伙伴企業之間是基于持久交互作用的資源交換關系,關系雙方均擁有彼此需要且有價值的資源[13]。資源的相互依賴會促進企業之間的關系性嵌入[14],并催生企業在維系彼此之間資源可獲取性過程中的信任、承諾以及交互作用(reciprocity)[15][16],形成企業之間因關系性嵌入所產生的網絡內知識沉淀,進而誘發網絡外知識溢出效應,呈現出雙重網絡嵌入,推動網絡發展與升級[17]。正是在此理論邏輯下,近年來主流文獻從二元層面和網絡層面分別對企業間合作關系的運行與協調機制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索[18][19][20]。但是,此理論邏輯所蘊含的隱藏假設是,合作企業之間的資源交換與業務交互作用是在一種對稱性網絡關系下展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使得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也存在著進一步完善與深化的空間。
最近幾年內,少數學者開始打破以往理論建構中所依托的對稱性網絡假設,將研究視角轉移到小企業與大企業的合作中,試圖探究非對稱網絡關系下企業間知識管理與整合。總體分析,這類研究大體遵循兩條路徑:其一,基于小企業的立場,探討小企業如何在合作中避免大企業的知識侵犯、維護自身利益、開展知識探索[21][22][10];其二,基于大企業和整個網絡關系的立場,分析大企業如何更好地管理網絡價值創造并帶動小企業的發展[23][2][3]。
由于市場地位或能力不足,小企業在與大企業合作中往往具有先天的劣勢。大企業所具備的強勢技術學習能力和資本優勢對小企業的技術知識形成了威脅,Katila等將此形象地描述為“陪鯊魚游泳”[21]。然而,這種威脅還取決于“鯊魚”本身:其一,“鯊魚”是否具備了侵占知識的能力;其二,“鯊魚”是否有知識侵占的動機[10]。實際上,大企業知識侵占的能力和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具備的網絡權力及其運用方式[9]。大企業可以選擇基于強勢網絡位勢轉嫁內部成本,例如供銷關系中的附加報價(add-on pricing)[11],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網絡能力和地位來更好地協調和管理跨邊界的價值共創。在以大企業為核心的非對稱性網絡內,成員企業的角色完全不同于對稱性網絡,企業之間的依賴也由對等性轉變為非對等性[4]。大企業的市場地位和技術主導能力越強,越有利于形成強勢的網絡權力,進而提升小企業的單邊依賴性。
在非對稱性網絡中,核心企業由于占據了較成員企業更具優勢的位置,其個體行動在網絡的形成、成長和成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4][25]。然而,僅單獨的網絡位置并不能創造出利益,核心企業會利用其位置優勢,通過保護、探索和管理網絡,去獲取網絡利益的更大份額。除了占據中心位置以獲取網絡利潤的更大份額,中心企業也應承擔其責任,使得整體網絡的生產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因此,公司在評估其通過聯盟網絡所創造出的價值時,首先要判斷公司在網絡中的位置。
Ibarra在研究個人權利時,認為權力除了來源于個體屬性和正式權威,同樣來自于縱向的勞動分工[26]。對于資源和不確定性的控制可能來源于跨邊界的位置或者組織工作的核心位置[27]。而在產品內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網絡中核心企業,例如Intel、Dell和Cisco等,負責向市場供給最終產品,并承擔產品價值的實現,而其他生產與服務企業則圍繞最終產品業務鏈條從事價值創造活動。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致使網絡成員企業更加依賴核心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能力,核心企業也隨即成為網絡的中樞。因此,可以說,這些處于價值網絡高位環節的核心企業的業務拓展與市場開發能力顯著影響整個價值網絡的價值創造和整體競爭力[28]。正是由于非對稱性網絡中這種企業在價值網絡中進行的勞動分工,可以將個人權力的結論引申至網絡層面,即企業間的權力同樣來源于網絡中的分工,換句話說,處于價值網絡中高位環節位置可以為企業提供權力的來源。例如,模塊化技術結構的發展,不僅使得主導設計成為技術結構的核心要素,而且還使得成員企業對于主導設計的模塊集成商的依賴性增強,模塊集成商也從而獲得對于成員企業的權力,而升格為平臺領導者[28]。
非對稱性網絡下的權力結構突顯了核心企業的異質性角色,也賦予了其網絡協調與管理職能。核心企業作為網絡的“守門人”[29],不僅要承擔自身的業務發展,還肩負著整個網絡價值共創的使命[30]。盡管核心企業享受著優勢網絡地位及其衍生的網絡權力所帶來的收益紅利,但也會受到諸多挑戰。第一,核心企業需要與網外的同業企業競爭以吸引優質業務伙伴。戰略伙伴選擇理論強調通過關系建立之前的有效伙伴選擇以促進合作成功[31][7]。雖然企業間網絡中大多數非核心結點上往往因技術門檻較低而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相應的伙伴選擇也相對較容易,但也有少數結點在技術上具有較高的要求,對應的市場厚度也較小,要選擇并建立有價值的伙伴關系并不容易。此類供應商在業務合作與交易上往往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和選擇權,為了吸引這一類優質供應商,核心企業需要與其他同業企業展開爭奪。第二,核心企業承擔著網際競爭的重擔。產品內分工的深化和網絡化生產的發展一方面將業務重心下移(系統→模塊),另一方面又將市場競爭的重心上移(企業→網絡),企業間網絡成為最終產品市場競爭的基本單位。核心企業在網絡間競爭中的表現無疑會影響到成員企業的追隨意愿,因為較強的競爭力對成員企業來說意味著持續、穩定的合作機遇和可預期的未來收益。第三,核心企業在發展自身業務的同時,還需兼顧企業間的利益協調與整合。根據商業生態系統理論[32],網絡成員之間存在互賴、共生的利益聯系,彼此之間通過知識流、物流、資金流緊密相連。在長期的業務協作中,利益分歧在所難免。如何協調網絡成員間的利益、建立包容性的利益整合機制,無疑是對核心企業的挑戰。
核心企業所面臨的內外部挑戰彰顯了網內協調與管理的重要性,近期的主流文獻也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33][30][34]。諸如,Dhanaraj和Parkhe指出,網絡成員企業并非僅僅對網絡誘因和約束做出反應的惰性實體,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會主動開展價值搜尋與聯合互動的自發性主體[2]。在另一項歷時性研究中,Paquin和Howard-Grenville發現,在網絡建構早期,核心企業會隨著技能和資源的積累而逐漸形成網絡管理能力,而隨著網絡的發展,核心企業在努力為不同成員企業創造價值過程中會遭遇越來越多的困境,網絡管理也相應從偶發性的成員選擇轉變為持續而緊密的關系互動[3]。然而,這些研究始終沒有超越企業間關系視角的束縛,將核心企業的網絡管理視為基于關系治理機制的知識獲取與業務協調。由于關系治理機制需要建立在持續性、反復性的互動和行動可預期的假設基礎上[35],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企業間利益協調與整合問題。
在外部挑戰和內部管理的雙重壓力下,以松散耦合結構為依托的關系治理機制已經難以滿足跨邊界價值共創的要求,核心企業需要借助更強的掌控力,以實現對成員企業的規制和整合。可以說,核心企業基于依賴非對稱性所形成的網絡權力為網絡管理奠定了結構性基礎。核心企業可以利用結構優勢對成員企業決策施加影響,并在全網范圍內推行既定的網絡規則。然而,Shulman和Geng的研究發現,網絡權力的過度使用有可能引起新的管理困境[11]。從Hogg等的關系認同視角來說,網絡權力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成員企業對既定關系的價值性、戰略性、公平性等方面所形成的認同[36]。這種認同的產生并不依賴于核心企業是否運用網絡權力,而在于網絡權力實施的方式和情境。核心企業的角色不能僅滿足于權力的實施者,更應該體現出網際競爭下的領導者和探索者。在既定的網絡管理行為和策略下,核心企業不再依賴于強權管理,而是逐漸培養和塑造企業間領導力[12][34],以此來引導成員企業之間積極有效的互動與融合。在此理論邏輯下,核心企業如何利用網絡權力開展管理,以培育自身的企業間領導力?隨著網絡權力的實施,核心企業的地位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本研究將嘗試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關注核心企業如何通過網絡權力的建構和運用來提升企業間領導力,是一個較新的領域,基于現有文獻還難以形成系統的邏輯分析框架,適合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37]。通過對一個典型案例的分析,深化對同類問題或現象的理解[38],在研究過程中不預設過多的框架限制,使研究者可以發現更多的理論關系[39]。本文依據案例典型性、數據可得性、數據獲取便利性等三個標準來進行案例企業選擇[40][41],最終選定“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以下簡稱“大淘寶”)為案例樣本,即以淘寶、天貓、聚劃算等個人網購平臺為核心的商業體系(不包括阿里巴巴B2B平臺)。
(二)變量測定
在變量測量上,努力保持相對寬泛的概念范疇,以確保變量能夠從數據中析出[42]。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選擇文獻中已有的分類及測量方式,以保障研究的可復制性。創新模式主要引用Henderson和Clark的框架,劃分為架構創新和模塊創新[43]。架構創新是指企業對整個生態系統與網購平臺的打造與調整;而模塊創新即基于既定業務或服務的改進行為,屬于局部性調整。網絡權力的測度在網絡中心性概念基礎上,結合核心企業的異質性角色,主要基于核心企業在網絡管理中所依托的優勢點。意義建構衡量核心企業在多大程度上與成員企業共享學習經歷、并對重要戰略問題持有共同理解[6],相關測度如服務共享、業務扶持等。企業間領導力包括技術、平臺、制度等三個方面[28],重點測量核心企業如何從這些角度去引領、影響或管控伙伴企業的行為與戰略選擇。
(三)資料收集
根據Miles和Huberman“證據三角形”觀點,資料收集渠道必須多樣化,以實現不同資料之間的相互驗證,避免因資料的片面性而降低理論構建的有效性[44]。同時,多渠道的資料收集有利于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進而提升案例研究本身的建構效度。為此,本研究主要通過實地訪談、文獻資料、內部檔案數據等三種方式收集研究所需資料。實地訪談包括對“大淘寶”內部人士、中小網上賣家、平臺服務商、行業專家等15人進行了面對面訪談。訪談采用半結構化的方式進行,配以主問、輔問和記錄人員,以確保充分挖掘研究所需信息,每次訪談約持續1至1.5小時。訪談結束后,研究人員與受訪者交換名片,以便進一步的跟蹤核實。文獻資料收集途徑包括:(1)通過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收集主流媒體對“大淘寶”相關業務、戰略或高層人員的新聞報道、專訪等資料;(2)通過EBSCO、ABI、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優秀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數據庫收集與“大淘寶”有關的研究文獻資料;(3)通過上海市圖書館、浦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收集與“大淘寶”及其主要高層管理人員相關的圖書資料。內部檔案數據包括:(1)阿里研究報告,指通過阿里網站平臺收集的阿里研究中心在不同時期發布的研究報告;(2)平臺運行相關內部資料,主要包括各個時期阿里制定的網商規則相關資料、各類業務的相關宣傳與分析材料、淘寶論壇中的相關信息發布和評論等;(3)高層講話和公司報告,主要包括阿里集團高層在公司內部、網商論壇、企業家論壇等場合所做的報告,以及公司社會責任報告、年報等。
(四)數據整理與編碼
本研究采用深度內容分析法,在對案例數據分析之前不預設理論偏好和初始假設[45]。為分析不同時期“大淘寶”開展的網絡建構與管理行為,我們將案例企業所經歷的發展時期劃分為培育期、成長期和拓展期三個階段。根據不同時間階段,對“大淘寶”網絡構建的關鍵事件進行了梳理和分類,關鍵事件的確定原則主要依據Ring和Van de Ven的界定,即“這一事件影響到合作雙方關系的發展”。整個數據整理與分析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兩步[46]。第一步,通過初步內容分析識別關鍵概念及其潛在關系。基于此,將研究團隊分為兩個小組,分別對資料進行通讀并展開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注重采用表格來予以輔助[47]。隨著分析過程的推進,安排兩個小組一起開展討論。經過多輪的資料閱讀與討論,確定了以下變量為本研究的關鍵變量:創新模式、網絡權力、意義建構、企業間領導力。第二步,基于前述所明確的關鍵概念,對資料進行編碼。在第一階段工作的基礎上,研究團隊根據本文的主題及關鍵變量進行漸進式編碼。創新模式按照架構創新和模塊創新進行編碼,網絡權力按照強制性和柔性編碼,意義建構按照強、弱編碼,企業間領導力按照技術、平臺、制度編碼。整個編碼過程由研究團隊共同討論確定,最終形成的編碼關鍵詞及條目數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測度關鍵詞及編碼條目數
四、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首先通過時間序列展開,剖析“大淘寶”生態網絡的成長及其企業間領導力形成的基本過程;其次,開展跨階段的比較分析,以揭示企業間領導力生成過程中各相關要素的演變路徑;最后,對案例分析中所揭示的實證證據進行理論總結與討論。
(一)基于時間階段的“大淘寶”生態網絡成長分析
1.“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培育期。2003年5月,以C2C業務為核心的淘寶網正式上線。盡管淘寶網的建立為阿里巴巴集團在網購生態系統中贏得了較好的網絡位置,但在平臺流量大量集聚之前,其并不具有顯著的網絡權力,淘寶網仍然需要通過大量的廣告來吸引中小網店和網購消費者的注意。為了迅速贏得中小網商的關注,淘寶網推出了一系列的架構創新措施。在互聯網業界普遍倡導商業模式贏利導向的環境中,淘寶卻充分發揮了互聯網雙邊平臺定價模式創新特性[48],采用完全免費方式來引導網店和網購消費者的匯聚,并很快獲得了大量人氣的積累。該戰略的成功實施至少有賴于淘寶兩方面的能力:其一,強大的資金實力,來自集團層面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使得淘寶團隊能夠將免費戰略執行到底;其二,淘寶團隊卓越的戰略視野,這可從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云的演講中得到充分體現,“淘寶選擇免費的商業模式,并不是因為對手是收費的,我們為了與他們競爭,所以就采用免費的方式……我們最后選擇免費,完全是因為市場……在這個時候,市場的培育是最重要的。”淘寶網在第一階段所推出的另一項架構創新舉措是誠信系統的建立,包括賣家評級、在線評價等。誠信系統的建立為淘寶網提升其服務能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淘寶網一系列的網絡建構行為構成了其網絡權力的基礎,體現在中小網商對淘寶平臺的認可與追從。正如一位網店經理所說,“早期的淘寶網盡管在綜合服務體系構建上不能與今天相提并論,但在人氣的集聚能力上,的確明顯超過了同時期的競爭對手”。利用早期市場競爭相對較小、網購文化尚待培育的歷史時機,淘寶網迅速通過架構創新占領了行業高端,在短時間內大量爭取網站流量,培養用戶體驗。正是由于淘寶網網絡權力的作用,中小網商對這一平臺產生了深度的非對稱性依賴,很多網商開始增加對淘寶網店鋪的人力和資金投入,也越來越受到淘寶平臺規則的約束。在這樣的過程中,淘寶網的強制性網絡權力得以逐漸建立起來。
對于很多網商而言,這一時期淘寶的架構創新策略使其在諸多方面受益,即較強的意義建構性。其一是低成本的網店運作。由于淘寶網完全減免前六年的平臺服務費,為中小網商節省了較大的成本支出。其二是學習和成長的機會。淘寶網推出的一系列網商培植計劃如淘寶大學、在線互動社區、論壇等,使得中小網商可以獲得大量的網店經營知識,這在網購行業發展的初期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其三是人氣集聚的優勢。由于淘寶網成功的模式創新,淘寶當時成為網購的代名詞。大量的網購客戶被吸引過來,使得在淘寶網上開店成為網上銷售的主要渠道。更為重要的是,為了培植網絡平臺,淘寶網在這一時期采取了低門檻、寬松管理的策略,為網商的創新管理和迅速擴張提供了契機。
2.“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成長期。進入“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生態系統構建”開始成為網絡發展的核心目標,最為標志性的事件無疑是“大淘寶”戰略的提出和實施。在這一階段中,阿里巴巴集團主要從兩個方面豐富和拓展其電商網絡:一是“大淘寶”內部資源協同與功能拓展,二是平臺物種多樣化與生態鏈打造。
從“大淘寶”內部來看,阿里巴巴集團一系列的戰略性舉措確保了其網絡功能逐步增強,這些創新為中小網商的業務拓展提供了較好的資金、信息、業務配套等諸多方面的支持。在自身平臺功能日益強大的同時,“大淘寶”注重通過引入外部的多樣化生態物種來拓展網絡的服務功能和水平。正如《2010大淘寶生態圈百年合作伙伴發展倡議書》中所指出的,“在大淘寶商業生態圈建設中,合作伙伴作為重要的生態角色,其價值不可或缺”。這方面的舉措包括用以引入第三方程序開發者的淘寶開放平臺和涵蓋物流、營銷、渠道等方面“淘寶合作伙伴計劃”的“淘拍檔”平臺。這些平臺用以整合發展各方面的電子商務外包供應商,在IT、渠道、服務、營銷及倉儲物流等電子商務生態鏈的各個環節為淘寶賣家提供個性化產品和個性化服務。
“大淘寶”的模塊創新策略將其自身至于整個生態系統的中心,顯著提升了其強制性網絡權力。利用此權力,“大淘寶”開始考慮自身的贏利模式,包括一系列的業務性收費和強制性規則。同時,“大淘寶”對于規則的設計越來越細,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也越來越大。強制性網絡權力的提升一方面強化了“大淘寶”在網絡管理中強制執行的空間,提升了網絡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引發了部分的抱怨和不滿。例如一位網店經理指出,“在阿里巴巴第一次的店家清退中,我們竟然因為屬類問題被清退出了天貓平臺…后來費了很大的功夫,花費了幾十萬,才再一次進駐”。由此,強制性網絡權力的提升對于“大淘寶”網絡創新行為的意義建構性無疑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日益發展的生態體系為中小網商的成長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另一方面,過大的費用壓力和維護成本大大擠壓了中小網商的贏利空間。
從這一階段的網絡建構行為來看,由于網絡拓展所賦予的日益增強的控制力及其對中小網商的約束,“大淘寶”的強制性網絡權力得以進一步強化;柔性網絡權力仍然在發揮作用,但相較于第一階段效果略有減弱,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強制性網絡權力所取代。由于“大淘寶”對市場把控能力的逐漸增強及其對網絡生態系統的日益豐富化運作,其平臺領導力得以顯現。
3.“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拓展期。在經歷了網絡功能的豐富化之后,“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的第三階段開始立足于新一輪的架構創新,包括物流骨干網“菜鳥”網絡計劃、余額寶、移動社交通訊工具“來往”、基于手機的在線網購平臺“手機淘寶”、作為C2B(customer to business)先行者的“天貓預售”,等等。此外,“大淘寶”在這一階段中所推出的“雙十一”購物節活動較好地推動了平臺的整體性升級。從網絡建構的角度來說,這一舉措至少在三方面使“大淘寶”受益:實現了很好的平臺營銷效果;進一步發展和培育了網購客戶;更為最為重要的是,“大淘寶”通過此活動的展開對其平臺的數據處理、信息溝通、物流配送等整個系統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演練,顯著提升了其大規模網購業務的綜合處理與協調能力,實現了“大淘寶”、物流企業、網店、第三方服務商等不同角色之間的協同。
“大淘寶”在這一階段的架構創新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其強制性網絡權力,特別是服務于全網的物流體系構建,無疑增強了中小網商對平臺的非對稱性依賴。同時,“大淘寶”在這一階段利用其結構優勢所開展的一系列創新行為,也再一次體現了其能力上的優勢,特別是對于新市場領域和新服務模式的探索。從這個角度來看,“大淘寶”的網絡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
而就“大淘寶”權力運用的意義建構性而言,則體現出了截然相反的趨勢。換言之,“大淘寶”網絡發展策略對于中小網商而言的意義建構性進一步降低了,主要體現在:其一,各種收費項目進一步增加再一次擠占了中小網商的利潤空間;其二,整個平臺上的超競爭狀態使得中小網商難以獲得快速成長的機會;其三,“大淘寶”的重心已經由網商的培植轉向了自身勢力范圍的圈定。日益降低的意義建構性無疑會影響“大淘寶”企業間領導力的提升。為此,“大淘寶”在第三階段主要通過對制度體系的建構來提升其領導力,即所謂的制度領導力。一是自身平臺制度體系的完善,特別是對規則體系的修正和升級;二是共享的價值觀和理念;三是參與行業標準和立法的制定。
(二)企業間領導力生成機制各要素的跨階段縱向比較分析
1.創新模式。在第一階段里,“大淘寶”的網絡建構策略側重于基礎架構的搭建,力圖通過全新的平臺架構和服務體驗贏得市場關注。這一過程中,推出了諸多架構創新,包括以網絡評價和信用評級為核心的誠信體系、以支付寶為依托的網上支付體系、以免費為主要手段的營銷服務體系等。這些架構構成了網商賴以生存的土壤,也成為“大淘寶”進一步擴張的基礎。在形成主體架構的同時,“大淘寶”也完成了功能性的模塊創新,進一步拓展了“大淘寶”企業網絡的服務承載能力。進入第二階段,“大淘寶”架構創新的步伐有所放緩,對原有架構的升級工作主要包括“大淘寶”戰略設計及天貓平臺的搭建、基于O2O戰略所推出的“淘一站”線下實體平臺、致力于提升“大淘寶”綜合信息處理與計算能力的阿里云等方面,而基于主體架構所開展的功能拓展成為這一階段中“大淘寶”網絡優化的主要手段。大量模塊創新使得“大淘寶”在保持主體架構基本穩定的同時,顯著提升了網絡的綜合服務和價值創造能力,同時,也為“大淘寶”在第三階段升級主體架構奠定了基礎。進入2011年以后,“大淘寶”開始將戰略視角聚焦于新業務平臺拓展,在原有基礎架構上對“大淘寶”網絡做了根本性的變革。相比較而言,“大淘寶”在第三階段所開展的模塊創新則明顯減少,這主要源于第二階段所開展的大量模塊創新工作很好地豐富了企業網絡的服務功能,同時也體現了“大淘寶”在平臺構建策略上的戰略性調整。
2.網絡權力。與一般電商平臺相比,“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在建立之初就具備較強的資金實力和平臺能力。特別是在投資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大淘寶”在營銷推廣策略和效果上明顯優于同期其他對手,在構建有效的網上交易機制上也體現出了顯著優勢。這種能力上的優勢使得“大淘寶”可以向中小網商施加積極影響,從而贏得中小網商的主動追隨和遵從。
3.意義建構。在2003年淘寶網成立之初,“大淘寶”主要立足于新市場的培育,試圖通過讓更多的網上賣家贏利來形成流量優勢。在這一階段中,“大淘寶”采取了有效的網絡構建策略,也推出了一系列讓賣家受益的服務。而對于“大淘寶”本身來說,并沒有過多考慮自身的贏利問題。正如馬云所說,“你向每個會員收取費用,一定要給會員創造遠遠多于他付出的費用的價值,這是每個阿里巴巴人都應該牢記在心的”。顯然,這樣的做法對于“大淘寶”的伙伴企業具有很強的意義建構性,彼此之間在持續的互動中能夠形成共同的認知和理解。進入第二階段以后,如何豐富和完善已有平臺、為網上賣家及配套服務商提供更多機會仍然是“大淘寶”重要的戰略方向。而與此同時,“大淘寶”也開始考慮自身的贏利模式問題,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的收費工具或規定。在這一過程中,過分地追求利益反而給網上賣家帶來了較大的經營成本壓力。相應的,網絡構建行為對網上賣家而言的意義建構性也有所減弱,因為過分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會降低有關企業間關系需求的共同認知,也不利于在網絡拓展與協調上形成一致性認知。正因為如此,“圍攻淘寶”事件才得以發生。而在第三階段中,“大淘寶”網絡拓展行為對于網上賣家的意義建構性進一步減弱。網絡關系上的共享利益和關系性戰略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忽視,“大淘寶”的賣家很可能會因此而遭受較大的利益侵害。
4.企業間領導力。在第一階段中,“大淘寶”企業網絡正處于培育期,還不足以對網上賣家、配套服務商等形成直接影響,因此這一時期并不具備明顯的平臺領導力。而在技術層面,“大淘寶”通過推出網上支付平臺和信用評級系統,很好地完成了對伙伴企業的引導和培植。實際上,網購平臺本身的技術架構并不復雜,但信用體系、支付寶等關鍵業務相關技術架構的搭建,從根本上奠定了“大淘寶”技術領導力的基礎。進入第二階段后,不斷增加的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使得企業網絡架構日趨完善,對于網上賣家、配套服務商等伙伴企業的影響力也因此日益強化。基于“大淘寶”企業網絡,越來越多的中小網商獲得了經驗和利潤,也樂于追隨“大淘寶”的戰略步伐。此時,“大淘寶”所表現出的是平臺領導力,即通過建構完善的網上交易平臺并有效整合企業間網絡信息與資源而形成的對其他伙伴企業的影響力。在第三階段里,盡管平臺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大淘寶”的網絡管理與協調策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平臺、規則、行為規范等諸多要素組成的系統共同作用于伙伴企業,由此形成一種制度性約束和影響。其一,平臺作為基礎保障支撐著伙伴企業之間的協調行為;其二,“大淘寶”所塑造的網絡規則、規范與行為準則確保了穩定的網絡關系并推動企業間價值共創。為此,這一階段“大淘寶”所形成的企業間領導力可界定為制度領導力,即通過建構和利用網絡制度來推動企業間價值協同創造而形成的對成員企業的影響力。
(三)結果討論
核心企業通過網絡構建來強化自身中心性位置、贏得控制權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學界共識[49][34],“大淘寶”的發展歷程對此進行了很好的印證。網絡權力作為核心企業賴以開展企業間管理的基礎,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管理的方式和策略選擇,這也是Dhanaraj和Parkhe(2006)[2]等研究的隱含假設。盡管網絡權力并不具有與企業內部職位權力相類似的強制性,但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伙伴企業行為和網絡價值分配[9]。基于此,“大淘寶”在初期采取了免費策略,借此大力提升其網絡權力,當網絡權力足夠強大時,才開始引入贏利機制。從核心企業生成的角度來看,網絡權力的提升是一個由能力向結構轉化的過程,核心企業作為網絡資源的整合者,在內部需要協調不同伙伴企業之間的利益,在外部則需要領導伙伴企業參與跨網絡的市場競爭,能否具備較強的企業間領導力因此顯得至關重要。類比于個體在企業組織中的情況,本文認為網絡權力構成了企業間領導力的基礎,“大淘寶”的經營實踐也對此進行了印證。在發展的早期,由于“大淘寶”還不具備足夠的控制力,其網絡權力相對較小,只能通過免費等方式來吸引潛在伙伴的加盟,所以在這一階段,其企業間領導力還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而隨著平臺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網絡權力的提升,“大淘寶”逐步實現了對整個網絡的控制,潛在伙伴也開始主動追隨“大淘寶”的業務戰略。此時,其平臺領導力開始顯現。進入最后一個時期,日益完善的平臺制度體系賦予了“大淘寶”更加強大的網絡權力,也使其逐漸體現出制度領導力。這里,從技術到平臺再到制度的躍遷,體現了“大淘寶”企業間領導力邊界的拓展,而非強度的提升。就觀察的結果來看,“大淘寶”在其發展歷程中并沒有塑造出較強的非正式影響[12],其企業間領導力更多來源于正式網絡權威和創新能力。
從另一方面來看,網絡權力向企業間領導力的轉化會受到意義建構的影響[6]。網絡權力的使用只有在具有較強聯合意義建構性的前提下,才能夠獲得伙伴企業的認同和追隨,進而衍生出企業間領導力。就“大淘寶”的發展歷程來看,意義建構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降低,強制性網絡權力的使用則日益頻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大淘寶”已經牢牢把控終端網購消費市場,現有合作伙伴很難輕易脫離淘寶陣營;第二,懸殊的規模差異使得伙伴企業很難向核心企業發起有實質意義的挑戰;第三,經營中的能力和資源慣性使得伙伴企業對“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產生了較強的依賴性。較低的意義建構性意味著伙伴企業與核心企業之間在諸多戰略問題上難以形成一致的理解,核心企業過多地考慮自身的利益訴求勢必引起伙伴企業的不滿甚至叛逃。鑒于由此引起的潛在危機會一直存在,企業高層無疑應該提高警惕,并制定與采取預防性措施。
企業間領導力的生成不僅僅有賴于既定情境下的網絡控制和價值共創,更體現在突破現有情境或制度束縛,為新業務的拓展贏得合法性,即非正式經濟向正式經濟的轉化[50]。強勢的核心企業往往能夠將非正式經濟正式化,為伙伴企業贏得新的市場機會,進而提升自身的企業間領導力。“大淘寶”在這方面堪稱典范。例如,原來游離于國家體制之外的余額寶,經過“大淘寶”的持續經營和廣泛協調,成功演變為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創新形式。非正式經濟作為新的業務形式,充分體現了核心企業的創新能力,而將非正式經濟轉化為正式經濟,再一次驗證了核心企業的市場領導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非正式經濟正式化彰顯了核心企業的制度領導力。
五、結論與啟示
核心企業到底如何獲取網絡權力并形成企業間領導力?“大淘寶”的發展實踐為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鮮活的實例。本文通過對“大淘寶”生態企業網絡三個階段發展實踐的深入分析和縱向比較,揭示了核心企業網絡構建中的創新策略調整、網絡權力演變和企業間領導力生成的動態機制,明晰了核心企業網絡權力向企業間領導力轉化的理論邏輯。探索性案例研究結果顯示:核心企業在網絡拓展中逐漸形成網絡權力,這種權力會隨著生態企業網絡的發展而增強;過于強大的網絡權力降低了核心企業行為對伙伴企業的意義建構性,進而影響到企業間領導力的提升。為此,核心企業只能通過正式權威的建立,分別在不同時期形成技術、平臺和制度層面的領導力。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通過探索成員異質性在網絡構建中的作用,拓展了企業間網絡相關研究。本文從核心企業和伙伴企業之間的網絡位置與分工差異出發,梳理和識別了成員異質性下企業的網絡構建策略和地位變遷,能夠對已有文獻形成有效的補充和拓展。特別地,本研究強化了成員異質性所引起的位勢差在企業間協調與信息分享中的作用,有利于深化Lipparini等關于核心企業與伙伴企業之間信息流動的相關研究[23]。具體而言,核心企業與伙伴企業之間的信息并非自由流動,而是會受到網絡結構及地位差異影響,占據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會運用其能力或結構優勢來干預網絡信息流動。第二,通過剖析企業間領導力及其轉化機制,發展了核心企業生成的相關文獻。企業間領導力問題不僅凸顯了網絡成員特質作為研究對象的必要性,而且回應了近期有關對核心企業開展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呼聲[49]。特別在核心企業生成的問題上,主流文獻始終沒能取得突破。本文有關企業間領導力的探討,為理解核心企業從能力提升、規模擴張到地位演變的動態過程提供了一個替代性視角,有利于彌補當前企業間網絡理論在論述非對稱性問題方面的不足。在某種程度上,本研究揭示了為何某些企業在聯盟或平臺戰略的實施上遠勝其他企業的原因。
本文的結論對管理實踐同樣具有啟示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至今為止核心企業在如何管理聯盟網絡的問題上還缺少可參考的理論,更多的理論解釋都集中在信任、關系、契約等協調問題上。而實際上,大型企業高層對聯盟網絡的管理不僅是外部協調的問題,同時也是利用位置優勢所形成的權力來開展管理的問題。網絡權力在大型企業管理其聯盟網絡中往往能夠起到更好的效果,在更短的時間內、利用更少的資源來組織起有效的協作。然而,過分地透支網絡權力有可能導致大型企業喪失其優質合作伙伴,從而在長期的聯盟管理中得不償失。此時,與伙伴企業協作以培育共享的戰略體系或能力架構無疑能夠促進企業間利益最大化。要想打造跨企業邊界的整合性優勢,大型企業需要培育自身的企業間領導力。為此,大型企業應更加關注伙伴企業的利益,發展包容性的協同戰略,并將伙伴整合到長期發展的戰略圖景中。作為探索性研究,本文僅僅通過單一案例對核心企業網絡權力及其企業間領導力問題進行了討論,在理論歸納與構建上難免存在不足。進一步研究有必要通過更加多元化的經驗分析來彌補這一缺陷。
[1]Capaldo, A.Network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The leveraging of a dual network as a distinctive relational capabilit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pp.585-608.
[2]Dhanaraj,C.,Parkhe,A.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pp.659-669.
[3]Paquin,R.L.,Howard-Grenville,J.Orchestration blind dates and arranged marriages:Longitudinal processes of network[J].Organization Studies,2013,34(11),pp.1623-1653.
[4]Xia, J.Mutual dependence, partner substitutability,and repeated partnership:The survival of cross-border 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pp.229-253.
[5]Ding R.,Dekker H.C., Tom G.Risk,partner selection and contractual control in interfirm relationships[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13,24(7),pp.140-155.
[6]Revilla,E.,Villena,V.H.Knowledge integration taxonomy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rade-off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2,140,pp.854-864.
[7]Li,D., Ferreira,M.P.Partner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4(1),pp.308-319.
[8]Shah,R.,Swaminathan,V.Factors influencing partner selection in strategic alliances:The moderating role of alliance contex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29(8),pp.471-494.
[9]Perrons,R.K.The open kimono:How Intel balances trust and power to maintain platform leadership[J].Research Policy,2009,38,pp.1300-1312.
[10]Diestre L.,Rajagopalan N.Are all ‘sharks’ dangerous? New biotechnology ventures and partner selection in R&D 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33,pp.1115-1134.
[11]Shulman,J.D.,Geng,X.Add-on pricing by asymmetric firms[J].Management Science,2013,59(4),pp.899-917.
[12]郝斌,任浩.企業間領導力:一種理解聯盟企業行為與戰略的新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1,(3):109-118.
[13]Uzzi,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pp.35-67.
[14]McEvily,B.,Marcus,A.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11),pp.1033-1055.
[15]Folta,T.B.Governance and uncertainty:The tradeoff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commit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pp.1009-1028.
[16]Schreiner,M.,Kale,P.Corsten,D.What really is al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how does it impact alliance outcomes and succ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pp.1395-1419.
[17]彭偉,符正平.創業導向、雙重網絡嵌入與集群企業升級關系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區的實證研究[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4,(3):71-80.
[18]Gulati,R.Alliance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pp.293-317.
[19]Powell,W.W.,Koput,K.W.Smith-Doerr,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pp.116-145.
[20]Zaheer,A.,Bell,G.G.Benefiting from network position:Firm capabilities,structure holes,and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pp.809-825.
[21]Katila,R.,Rosenberg,J.D.Eisenhardt,K.M.Swimming with sharks:Technology ventures,defense mechanisms and corporate relationship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8,53,pp.295-332.
[22]Vandaie,R.,Zaheer,A.Surviving bear hugs:Firm capability,large partner alliances,and growt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pp.566-577.
[23]Lipparini,A.,Lorenzoni,G.,Ferriani,S.From core to periphery and back: A study on the deliberate shaping of knowledge flow in interfirm dyad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pp.578-595.
[24]Goerzen A.,Beamish P. W.The effect of alliance network diversity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26(4),pp.333-354.
[25]Goerzen A.Managing alliance networks: Emerging practic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19,pp.94-107.
[26]Ibarra H.Network centrality, power, and innovation involvement: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o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36,pp.471-501.
[27]Astley W. G,Sachdeva P. S.Structural sources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 theoretical synthesi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1),pp.104-113.
[28]郝斌,劉石蘭,任浩.企業間領導力理論和實踐溯源與層次結構探討[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3,(5):50-59.
[29]Munari,F., Sobrero, M.,Malipiero, A.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ocalized spillovers:Focal firms as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2,21(2),pp.429-462.
[30]Provan,K.G.,Kenis,P.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Structure,management,and effectiveness[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pp.229-252.
[31]Hitt M.A.,Ahlstrom,D.,Dacin,T.M.,Levitas,E.Svobodina,A.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China vs.Russia[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2),pp.173-185.
[32]Moore,J.F.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5,pp.75-86.
[33]Suarez,F.F.,Lanzolla,G.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cs in building a first mover advantage the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2),pp.377-392.
[34]Sydow,J.,Lerch,F.,Huxham,C.Hibbert,P.A silent cry for leadership:Organizing for leading (in) clusters[J].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pp.328-343.
[35]Oliver,C.Determinan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gr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0,15(2),pp.241-265.
[36]Hogg,M.A.,van Knippenberg,D.,Rast,D.E.Intergroup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Leading across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37(2),pp.232-255.
[37]Eisenhardt,K.M.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pp.532-550.
[38]Pettigrew,A.M.Longitudinal field research on change:Theory and practice[J].Organization Science,1990,1(3),pp.267-292.
[39]Dyer,W.G.,Jr.Wilkins,A.L.Better stories,not better constructs,to generate better theory:A rejoinder to Eisenhard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3),pp.613-619.
[40]彭新敏,吳曉波,吳東.基于二次創新動態過程的企業網絡與組織學習平衡模式演化——海天1971~2010年縱向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4):138-149.
[41]Yan,A.,Gray,B.Bargaining power,management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United States-China joint ventures:A comparative case stud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6),pp.1478-1517.
[42]Laamanen,T.,Wallin,J.Cognitive dynamic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path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9,46,pp.950-981.
[43]Henderson,R.,Clark,K.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 35(1),pp.9-30.
[44]Miles,M.B.,Huberman,M.A.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An Expanded Sourcebook[R].SAGE, Thousand Oaks,CA,1994.
[45]侯杰,陸強,石涌江,戎珂.基于組織生態學的企業成長演化:有關變異和生存因素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12):116-130.
[46]Ring,P.S.,Van de Ven,A.H.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1),pp.90-118.
[47]Glaser,B.G.Strauss A.L.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Aldine Transaction,1967.
[48]楊文明.互聯網平臺企業免費定價反壟斷規制批判[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5,(1):104-113.
[49]Müller-Seitz,G.Leadership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A literature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2,14,pp.428-443.
(責任編輯:聞毓)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Power and Inter-firm Leadership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the“Big Taobao”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WU Yun-qiao1,HAO Bin2
(1.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2.Business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Big Taobao”ecological network,this study explores hub firms’ power and inter-firm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inter-firm networks.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types of network power are formed from the extension of inter-firm network: structure-driven power and capability-driven pow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firm network,structure-driven power and capability-driven power first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with a subsequent tendency of co-evolution, thereby maintaining the efficacy of the inter-firm coordination mechanisms;network power lowers the effect of joint sense-making between the hub and partners,thu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firm leadership;consequently,the hub firm has to foster technological,platform,and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different phases by introducing formal authority.By extending literature of network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asymmetry,this study helps to enhance the explaining power o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ory which was originally built on the basis of symmetric network structure, and contributes to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firm relationship under asymmetric network structure.
inter-firm network; hub firm; network power; inter-firm leadership; business ecology
2016-04-2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重大項目(15ZDA06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青年項目(71102067)
吳昀橋(1984-),男,湖北公安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講師,博士;郝斌(1981-),男,安徽安慶人,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博士。
F270.7
A
1004-4892(2016)11-00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