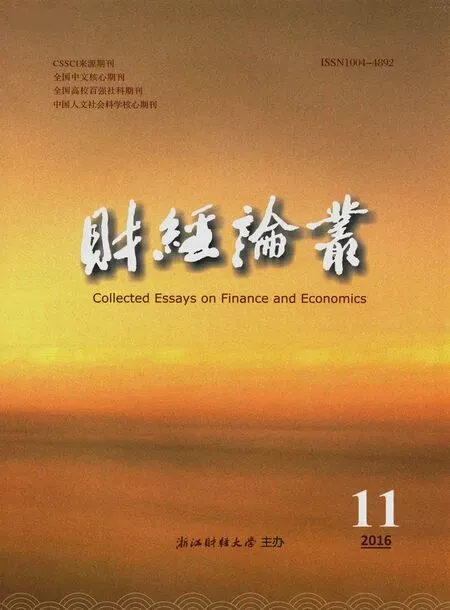我國中等城市財政運行的可持續分析
——基于106個地級市2003-2013年的數據
王德祥,雷 蕾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
我國中等城市財政運行的可持續分析
——基于106個地級市2003-2013年的數據
王德祥,雷蕾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中等城市是我國未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承接載體,在現代化戰略全局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的理論框架,對我國中等城市2003-2013年期間的財政收支數據進行面板協整分析。實證結果表明中等城市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之間確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財政可持續性較弱。而不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民生投入的增長以及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對財政收支差額的影響較為顯著,是造成可持續性較弱的主要風險因素。
財政可持續;中等城市;協整檢驗
一、引 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并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的經濟危機,許多國家的主權債務嚴重激增,財政可持續性研究又一次得到廣泛關注。與此同時,中國由于全球經濟波動以及國內產業升級導致增速放緩,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赤字擴張與債務攀升,人口結構變化和支出需求壓力增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呈現不斷擴大之勢,使財政的可持續性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此,加強對我國財政可持續狀況的研究,對提升我國財政狀況和促進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體系發展不均衡,中小城市相對衰落,城市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或城市群(帶)。根據聯合國研究表明,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城市居民居住于人口小于50萬的中等城市中。從中國城市年鑒的統計來看,我國城市結構在數量上以中小型為主,并且就人口和GDP份額而言,其所占比重也相當高。作為我國城市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連接大城市和小城鎮的紐帶,基于大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以及持續發展邊際成本的限制,中等城市是我國未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承接載體,在現代化戰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考察中等城市公共財政體系的可持續性就更有必要了。
二、文獻綜述
“財政可持續”(Fiscal sustainability)這一概念學術上并沒有一個確切統一的定義,最早由Buiter(1985)比較明確地提出,他將其闡釋為“經濟實體的財政存續狀態或能力”[1]。這很大程度上是指政府償債能力,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財政狀況無力償還債務時,它就不能存續而宣告破產;反之財政則可持續。
國外對財政可持續的研究歷史相對較長。實證研究方面,對于財政可持續的條件和評價方法存在一些不同的界定,總體來說包括兩類方法。第一類是指標法。Domar(1944)通過數理分析提出收斂的債務負擔率理論,將債務與總產出的比率收斂于一個有限值作為財政可持續的判斷標準[2]。從理論上看,如果政府債務增長率小于或等于經濟增長率,財政就擁有償債能力。Blanchard(1990)基于此進一步提出了在保持政府債務負擔率不變的條件下更具政策實施參考的“基本預算缺口指標”、“稅收缺口指標”等指標[3]。Mendoza(2004)提出了“自然債務限度”(Natural Debt Limit),是相對安全的指標,即政府可能出現的最差財政盈余或赤字時的債務負擔率[4]。還有被廣泛了解的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債務負擔率不得高于60%、赤字率不得高于3%的指標。它的最主要的優點在于計算簡單,易于比較,但并沒有考慮個體的差異以及變量的不確定性,很難具有普適性。
第二類是對“跨期預算約束”理論的研究和運用。檢驗“跨期預算約束”是否成立又涉及兩種計量方法:第一,檢驗累積債務或赤字的平穩性。如果時間序列平穩,那么“跨時預算約束”得到滿足,財政是可持續的。Hamilton & Flavin(1986)較早考察了美國年度財政赤字和累積債務,認為時間序列是平穩性的,財政可持續[5]。后續Uctum & Wickens(1996),Bohn(2005)等的實證研究都是基于此[6][7]。第二,檢驗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平穩性及相對均衡關系,比如Trehan & Walsh(1988)、Hakkio & Mark(1991)、Quintos(1995)、Bravo & Silvestre(2002)等的研究。他們認為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時財政可持續的跨期預算約束條件才能得到滿足,并且兩者之間協整向量(-1,β)需滿足0<β≤1[8][9][10][11]。在β=1時,財政強可持續;0<β<1時,僅存在財政弱可持續性。
我國對財政可持續的研究與國外比相對較少,實證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央政府層面。周茂榮等(2007)利用協整檢驗的方法對我國1952-2006財政收支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后認為我國財政可持續且可持續的顯著性水平較高[12]。張旭濤(2011)對我國1978-2010年間的財政狀況進行基本盈余率和債務負擔率的關系分析[13]。余永定(2000)構建了一個確定性模型計量分析影響財政的各個確定變量和變量間的確定關系[14]。陳建奇等(2012)在此基礎上擴展到一個隨機動態分析框架,并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當前財政沒有偏離可持續的發展路徑[15]。
近年來,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凸顯使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集中在省一級政府的研究相對較多。匡小平(2004)對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分析方法進行了研究[16]。馬拴友等(2006)研究了財政可持續性的條件,使用動態優化方法對其進行了較為嚴密的論證[17]。羅航(2009)運用面板協整檢驗的方法對我國省級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基于估計的協整系數得出其可持續性較強的結論[18]。唐祥來等(2014)從動態角度對江蘇省財政狀況進行分析,發現小口徑財政高度依賴中央轉移支付表現出弱可持續性或不可持續性,而中口徑財政在考慮非稅收入因素后轉化為強可持續性[19]。
隨著研究的深入,財政可持續的內涵也在不斷地擴展。張新平(2000)構建了一個財政可持續發展評估指標體系,包括財政可持續發展與經濟發展、稅收建設、資源開發與利用、社會穩定與進步、生態環境保護等五個方面[20]。武玉坤(2011)認為影響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有制度性壓力、結構性壓力和不確定性壓力,維持可持續性的路徑選擇是財政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有機結合[21]。基于此,本文試圖從財政收支角度,運用多城市面板協整的方法對中等規模城市的財政可持續狀況進行分析和評價,從而為其財政穩定和區域發展以及我國城市化提供一定的政策參考。
三、理論框架
原則上說,如果政府可以無限度地發債那么任何預算赤字值都是可能的,但事實上這自然不可行因為政府面臨著自身預算約束。政府收支的會計恒等式如下:
(1)
其中,Z是除利息支付以外的支出,P是財政收入,D是公共債務,r為實際利率[22]。
在政府存續財政具有延續性的前提下,移項并重寫后續時期的該等式,逐次迭代,遞歸地解出跨時期的預算約束:
(2)
跨期預算約束條件要求政府在無限期的債務現值趨近于零,這也被稱為非蓬齊博弈條件,即不能永遠靠借新債來償還舊債。當(2)式右側的第二項為零時,即:
(3)
將該條件帶入(2)式則可以得出:
(4)
等式(4)表示的是當前公共債務存量與未來基本盈余現值之和相等。如果等式(3)或是等式(4)成立,那么意味著累積債務滿足跨期預算約束,政府公共財政可持續。為了更方便地進行實證檢驗,對等式(1)進一步做代數變形,定義:
(5)
得到一個現值借貸約束(Present Value Borrowing Constraint,PVBC)方程:
(6)
假定y代表GDP的實際增長率,現值借貸約束可變形為:
(7)
假定實際利率r和實際GDP增長率y固定不變,預算約束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8)

將這個條件帶入(8)式相似地可以推出:
(9)
綜上,要評價財政是否存在可持續性,我們可以對債務存量差分的平穩性以及基本預算盈余與滯后的債務存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

(10)
等式(10)的右半部分是一階差分的形式,因此ZZt和Pt之差即為基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條件的一個平穩過程。所以,財政可持續要求ZZt和Pt必須協整并且差分平穩。其檢驗涉及到如下的協整回歸:Pt=α+βZZt+μt。μt是一個平穩的序列,此時如果β=1,這兩者之間一定存在協整關系,財政可持續性強。但學術上一般認為財政可持續的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協整向量只需滿足0<β≤1,若0<β<1,財政為弱可持續。
四、數據和實證
(一)數據描述
本文所用的城市相關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根據2014年最新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調整,我國中等城市被重新定義為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據此,以2013年人口狀況為標準,根據地級市市轄區平均人口數以及縣級市年末總人口數,符合區間條件的包括106個地級市以及165個縣級市。鑒于可得的數據,最終選取了106個地級市2003-2013年的面板數據確定為分析主體。
地級市的統計口徑限定為市轄區,包括城區、郊區,不包括轄縣和轄市。選取的統計指標包括地區生產總值(GRP),一般預算內收支口徑的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和地方公共財政支出。

圖1 中等城市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均值狀況 數據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從近些年中等城市總體均值的數據來看,財政收入以及財政支出的增長很快,都超過10%甚至最高年份達到30%以上,同時,兩者占地區生產總值GRP的比重也呈不斷上升趨勢,表明兩者的增長快于GRP的增長,財政能在城市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財政支出一直大于收入,且兩者差距還比較大,需要預算外收支的調節來達到平衡。
從中等城市個體的數據來看,收入比重約介于1%-19%,支出比重約介于2%-35%,普遍收不抵支,收支失衡明顯。而且直觀上看,收支比重與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方向比較一致,即GRP較大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傾向于有更大的財政收支比重,這與時間上的縱向趨勢也符合。
(二)面板單位根檢驗中等城市財政收支序列的平穩性


表1 中等城市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注:括號中為p值。
(三)面板協整檢驗中等城市財政收支序列的長期均衡關系


表2 中等城市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Kao和Pedroni面板協整檢驗結果
實證檢驗結果顯示兩種方法下統計結果都較為顯著,表明基于多城市面板協整的分析,中等城市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面板序列存在較強的長期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中等城市政府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間的相關系數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列于表3、表4。

表3 中等城市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面板回歸結果
表4中等城市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長期協整系數估計

長期協整系數t統計量H0:β=00.68192949.01446H0:β=10.68192922.86142
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根據計量結果得出的面板協整回歸方程關系表達式為:SR=0.6819ZC-35552.51。長期協整系數估計值為0.681929,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顯著地拒絕β=0的零假設。但同時通過計算對β=1的零假設進行檢驗,也可以顯著地拒絕原假設,因此協整系數β顯著地小于1。協整系數僅為0.681929,顯著小于1并且與1相差較遠,表明如果僅考慮小口徑的一般預算內收入難以保證一般預算支出的需要,中等城市財政狀況雖未背離常態嚴峻到不可持續的程度,但不能嚴格滿足跨期預算約束,公共財政具有弱可持續性。
樣本中約近十年的數據顯示中等城市財政運行的常態是收不抵支,似乎難以持續。但事實上通過實證檢驗,地方公共財政仍具有弱可持續。這可以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范圍內理解:根據前文的理論框架分析,由等式(10)可知,政府跨期預算約束條件下財政可持續要求地方收入增量必須大于公共支出和債務增量,并且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假定在長期情況下這一條件得到滿足。因此,基于現狀中等城市必須要約束支出和債務,同時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通過各種方式增加收入,從而實現財政自立和健康發展以及可持續。
綜上檢驗結果,我國中等城市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之間確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但財政可持續性較弱。
五、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鑒于中等城市相關數據的缺失,文章替代性地以地方政府為口徑建立一個同期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作為參考以探尋中等城市財政持續性較弱的原因。作為地方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等城市各方面占其比重明顯,趨勢也具有一致性。收支失衡程度以地方財政收支差額(CE)來衡量,通過定性分析和逐步回歸篩選出擬合優度較高的解釋變量:地方財政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ZY)、地方財政非稅收入(FS)、地方財政民生支出(社保、教育、醫療衛生支出之和,記為MS)以及地方財政債務付息支出(ZW),最終回歸結果如下:

表5 地方政府收支差額影響因素回歸結果
模型整體擬合較好,各變量的顯著性水平也比較高,結果表明地方政府財政可持續性主要受以下一些風險因素的影響。
(一)轉移支付制度的制約
轉移支付和財政收支差額顯著正相關。2003至2013年間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絕對量增長了近400%,與地方政府自有財政收入的比值達到70%-88%的區間。中央政府大規模的各種補助造成地方政府的高度依賴,把補充收入當作重要收入來源。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財政收支增長直接造成了地方財政規模虛增,不利于調動積極性和和主觀能動性,有些地方甚至可能利用信息優勢進行欺瞞謀求自身利益,中央的調控也就背離了初衷。其次,分稅制后財權上移事權下移造成地方事權和財權的不匹配是收支失衡一個重要背景,這種長期制度性缺口應該通過制度內部的改革或者調整來解決,預算外收支的調整只是輔助性和間接性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不能成為常態,否則最終會影響到財政的可持續性。最后,中央與地方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轉移支付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不夠規范,結果上也并不能使各級政府之間事權與財力完全匹配,中等城市仍面臨著嚴重的收支矛盾和巨大的財政困境。
(二)人口結構變化與民生投入的壓力
民生支出的快速增長也給地方財政支出帶來巨大的壓力,是收支長期失衡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嚴峻的人口結構轉變一方面會使勞動力人口減少,儲蓄和投資下降,從而阻礙經濟的長期發展,另一方面也將逐步給公共支出帶來壓力,嚴重地威脅中等城市城市長期財政可持續。另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中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事業的相對較少,而行政、建設性開支比例卻一直很大,財政支出結構面臨公共財政轉型,近些年教育、衛生、醫療、社保等方面支出無論絕對額還是占地方一般預算支出比重均有明顯快速增長的趨勢,這將增加中等城市的財政負擔,而且大部分都是剛性支出。
(三)龐大地方政府債務的威脅
債務付息支出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地方債務的增長,也會顯著造成財政收支失衡。盡管除一些特殊規定外,地方政府及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但近些年來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實際上繞開相關規定通過組建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發行企業債、公司債、資產證券化、資產信托計劃和銀行貸款等多種形式籌措資金。地方融資平臺迅速發展,龐大的地方政府債務已經嚴重威脅到中等城市財政可持續,加劇了財政風險。根據2013年12月30日審計署發布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我國當前地方政府債務絕對規模很大,僅是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即達到108859.17億元,而其中市級政府負債規模顯著偏高,占地方政府債務的比重平均達到41.03%。城市財政增長的負債化現象和潛在風險不斷加大,制約了經濟社會的發展,給中等城市財政可持續帶來嚴重隱患。

表6 2013年6月底地方各級政府性債務規模情況表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2013)。
六、結 論
近些年來,我國城市的經濟運行、人民生活和社會事業都平穩推進,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其中的中等城市,尤其是文中的分析主體地級城市經濟高位運行,財政收入持續增長,地方政府財力逐年增強,為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給改善民生和調整經濟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本文從財政收支角度,運用多城市面板協整檢驗的方法對中等城市財政收支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以及可持續狀況進行研究和判斷,結果表明中等城市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之間雖然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但不能嚴格滿足跨期預算約束,一般預算內收支失衡明顯,財政可持續性較弱。隨后建立了一個以地方政府為口徑的同期多元回歸模型作為替代進行實證分析,推斷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合理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制約、人口結構變化與民生投入的壓力以及龐大地方政府債務的威脅。對此我們應該清醒地加以認識,積極應對。
[1]Buiter W. H.,Minford P.A. Guide to public sector debt and deficits[J].Economic Policy,1985,1(4):3-6.
[2]Domar E. D.The “burden of the debt”and the national incom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4,34(4):798-827.
[3]Blanchard O. J.Suggestions for a New Set of Fiscal Indicators[Z].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1990.
[4]Mendoza E. G.,Oviedo P. M.Fiscal solvency 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tale of the tormented insurer[J].General Information, 2004(14).
[5]Hamilton J. D.,Flavin M. A.On the limitations of government borrowing:A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test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4):808-19.
[6]Uctum M.,Wickens M.Debt and deficit ceilings, and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policies:An intertemporal analysis[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6, 62(2):197-222.
[7]Bohn H.The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4).
[8]Trehan B.,Walsh C. E.Common trends,the government’s budget constraint, and revenue smoothing [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1988,12(2-3):425-444.
[9]Hakkio C. S.,Mark R.Is the budget deficit“too large?”[J].Economic Inquiry, 1991,29(3):429-445.
[10]Quintos C. E.Sustainability of the deficit process with structural shifts.[J].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5,13(13):409-417.
[11]Bravo A. B. S,Silvestre A. L.Intertemporal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policies:Some tests for European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8(3):517-528.
[12]周茂榮,駱傳朋.我國財政可持續性的實證研究——基于1952-2006年數據的時間序列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24(11):47-55.
[13]張旭濤.基于FTPL的中國財政可持續性研究[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1,(5):85-89.
[14]余永定.財政穩定問題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世界經濟,2000,(6):3-12.
[15]陳建奇,劉雪燕.中國財政可持續性研究:理論與實證[J].經濟研究參考,2012,(2):34-51.
[16]匡小平.論地方財政可持續性的分析方法[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4,25(6):77-80.
[17]馬拴友,于紅霞,陳啟清.國債與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J].經濟研究,2006,(4):35-46.
[18]羅航.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可持續性的面板協整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12):84-88.
[19]唐祥來,孔嬌嬌.地方財政可持續性實證檢驗:江蘇1995-2010[J].經濟與管理評論,2014,30(1):72-77.
[20]張新平.我國財政可持續發展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J].生態經濟,2000,(11):4-7.
[21]武玉坤.我國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1,(15):142-144.
[22]Afonso A.,Jalles J. T.Revisit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Panel cointegration and structural breaks in OECD countries[J].Working Pap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2012,66(1):33-51.
(責任編輯:風云)
A Analysis of Medium-sized Cities’ 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Data of 10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3 to 2013
WANG De-xiang,LEI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Medium-sized cities are the important carriers to undertak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futu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strategy.Based on the government’s inter-temporal budget constrai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makes panel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ata of medium-sized cities from 2003 to 2013.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um-sized cities’ fisc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but sustainability is weak.The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unreasonabl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the growing inpu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vast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s deb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They are the main risk factors causing weak fiscal sustainability.
fiscal sustainability; medium-sized cities; cointegration test
2016-06-10
王德祥(1957-),男,湖北鐘祥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雷蕾(1992-),女,江西東鄉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生。
F812.7
A
1004-4892(2016)11-002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