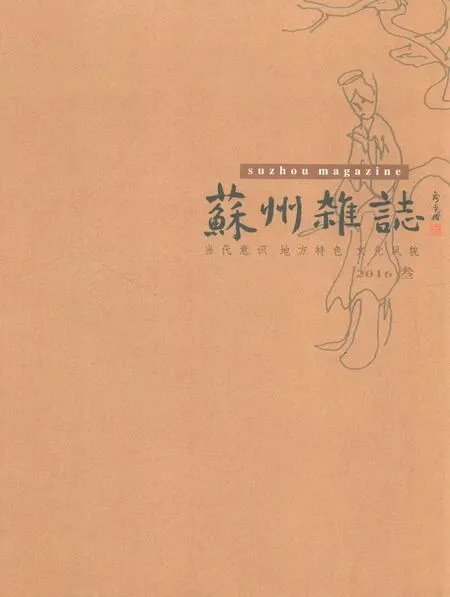『采珠者』桑毓喜先生
韓光浩
『采珠者』桑毓喜先生
韓光浩


今年五月的一個上午,我來到了桑毓喜先生的書房,對窗的書房里陳設簡潔,窗外的金雞湖碧波蕩漾。一本他參編的《中國昆劇志》放在了他的書案上,一切還如往昔。桑夫人秦慶華為我指點,這是桑先生用的杯子,寫過的筆,我陡然一驚,倏忽之間,桑先生離開我們已三年了,但是靜靜地翻著載他文字的書頁,總有一種他還在書房里,帶著他標志性的粗框眼鏡,尋章摘句獨坐靜寫的那種錯覺。
記得當年第一眼看到《昆劇傳字輩評傳》這本書,是在春天,一個春蠶吐絲的日子。如果說傳字輩們在大家心里是一棵棵百年老桑樹的話,翻開書頁,在這些桑樹下,我發現有位作者在仰望天空,他也姓桑,叫做桑毓喜。后來慢慢地欣賞到他更多的作品,那樸實的筆墨,寫出了昆曲水磨調的山高水長,篳路藍縷。我想,桑先生躲在書齋里的那幾十年,如湖畔的水鄉漁夫一般,他必定是在其間發現了旁人難得一見的珠貝,因為在他寫下的字和字之間,我讀到了珍珠散落在歲月里的靈動聲響。

一
桑先生是蘇州人,有著深深的江南情結。而當50多年前的一天,他揭開了昆曲的面紗,從此便找到了他一輩子的鐘情所在。
普通人家出身的桑毓喜先生,曾經交不起繼續求學的學費,也為生計擺過修筆攤,但正是這份苦與難,讓他對筆墨文字分外珍惜。1960年的春天,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夢回鶯囀”的季節,他被調入蘇州市戲曲研究室工作。從此他便屏息凝神,以文為寄。他是真的喜歡啊,一面配合顧篤璜先生尋找昆劇、蘇劇等歷史遺存,一面訪問老藝人、老曲家、記錄相關歷史、藝術資料,忙得不亦樂乎。其實,他所在的戲曲研究室編制不足4人,他擔負了大量的搜集和寫作的工作,卻終日不肯浮泛,無事便憂。
可他不覺苦。甫進戲曲研究室,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為了編好一套戲曲研究資料叢書,他自帶行李,夜攤早卷,睡在一張長方桌上。寂無一人,他與風月對話;寒風酸骨,他同古人談心。現在在昆曲曲友和戲曲圖書收藏界中流傳的《昆劇穿戴》、《昆劇選淺注》《韻學驪珠新編》《昆劇劇目索引匯編》等書籍都是出自他的手里。他事無巨細,從組稿、付印、校訂到出版、發行等全系列都是一個人負責,讓人咋舌,而他卻快活不可言。后來,他又參與編寫了《中國戲曲志·江蘇卷》《蘇州戲曲志》《中國昆劇志》等;他先后出版專著《昆劇傳字輩》《昆劇傳字輩評傳》,功莫大焉。
桑先生也趕上過“上山下鄉”,在他的昆劇搶保和研究生涯里,多得是“上山下鄉”之事。他為昆曲闖蕩過大上海,蹲點過小村莊:他數赴滬上,征集來清末民初曲家李翥岡珍藏昆曲精抄本一百六十冊,冊冊奇珍;他先后六次深入寧波,尋訪八位民國初年紅極一時的寧昆演員,將他們請到蘇州為青年演員教戲,并逐個訪談,記錄整理成了《寧波昆劇老藝人回憶錄》。此書內容被臺灣的洪惟助教授驚為昆曲史罕見之記錄,2012年,他親自趕到桑先生的病房簽訂了出版合約,并于2013年正式在臺灣出版,為昆曲史“填空補白”。
為文之事,形同人生。有文重于山,有文輕于羽。有人下筆百萬言,只是茶余飯后之料,而有人用墨如金,卻是后來者不可或缺的探路之燈。桑毓喜先生的昆曲研究生涯看上去水波不興,無非是搜集整理,其實,積沙成塔之中已是星斗其間。一路行來,旁人已經無法想象他幾十年書齋苦修的毅力,但是拿明人袁宏道寫給朋友李子髯的話頗可中的:大抵世上無難為的事,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的日子。“胡亂”這兩個字,放在桑先生這里,并無不恭,因為在世俗的眼光中,為昆劇不計名利勉力而為,豈非“胡亂”之事。而桑先生卻心生歡喜,只管一路做將去。

昆博的先生紀念展
二
桑先生的學問,大致集中在昆劇史上。我雖不精此道,但也知道,這曾經是一個日趨式微的學科,然而,式微并不表示沒有意義。吐火羅文也式微了,但季羨林以吐火羅文研究享譽國際。我理解,學問的式微,只是彼時彼地。時至今日,彼時小眾的學問,此時成了大眾的滋養。
跟著桑先生去讀傳字輩的昆曲史,不亦快哉。
《昆劇傳字輩評傳》這本書,桑先生是經歷了二十余年的艱辛寫作,這是一部饒有特色的“昆劇現代史”,桑先生以虔誠的心態,用20萬字的篇幅記述了自1921年“昆劇傳習所”的創立,經歷“新樂府”、“仙霓社”階段和1941年的解散,以及解放后《十五貫》的巨大成功等一脈相承的具體過程;也開列了傳字輩演出過的近七百出劇目;還考訂了傳字輩所有人員的生平概要,至善至詳。44位昆曲傳字輩和他們的演出劇目,自他道來之后,旁人再言傳習所,莫不以此為史。
而在《寧波昆曲尋訪記》中,他的記錄又讓人大開見聞:“寧波東鄉姚家鋪,有新老兩座祠堂,當地都是漁民,老祠堂中演戲,很是嚴格,觀眾大多是上年紀的人,他們不向戲臺上看,只是側耳傾聽,聽得滿意,點點頭,聽得不滿意,向演員斜瞟一眼。場子里寂靜無聲,甚至演《尋親記》中的《榮歸》也不許敲大鑼,凡是敲大鑼、演武場或場面熱鬧的戲,都在新祠堂里演,那里觀眾都是年輕人。”生動記錄了昆曲的老聽客和新粉絲之間的區別。此書中還有很多地方的記載也十分有意義,比如記錄五毒戲的各種臺步,白娘子的“蛇步”要上身挺直,臺步細碎快捷;時遷的“雀步”,要一蹲一跳,飄忽輕捷。此外,還有老外的“鶴步”,副末的“龜步”,大面的“鬼步”,各有不同特色。認真治史之心,在先生筆下處處可見。
說起桑先生的認真,那是有個故事的。1973年秋,桑毓喜被江蘇省公安廳調至句容灣灣山煤礦勞改隊管教科工作,從事備案及對犯人加減刑調查材料的審報,歷時7年。他要審犯人,就要重證據。犯人的供詞里只要有一個矛盾之處,他就要東南西北去調查,一定要搞得明明白白。后來他的嚴謹出了名,很多犯人一聽見今天提審的是“桑管教”,馬上膝蓋一軟,一個字都不敢說假話。
當年的“桑管教”,一不留神,成了昆曲史壓臺面的“打鼓佬”,文字“板眼”一絲不茍。這份嚴謹的來處,是桑先生的兩條腿和一支筆。他每寫一文,必左右推敲,上下求證,數易其稿,六百余萬字,莫不如是。以至中國的戲曲研究大家郭漢城先生也曾親筆致函,贊揚桑先生“治學嚴肅”,惺惺相惜。
三
桑先生在別人的眼里是個實在人,他那一見面就幫著未來的小舅子推“山芋車”的記憶至今讓夫人秦慶華一想起來就微笑。而在桑毓喜的老同事們眼里,桑先生也是這樣一個人,別人有困難,他總是記著,就像昆曲有難,他也是勉力地奔忙著,直到生命通道的盡頭他還是不忘昆曲。
最后幾年,他已經要靠輪椅行走了,他還是堅持著要讓女兒開車送他到昆曲博物館門口,他進去還有很多事情要囑咐博物館的“接棒者”,有什么史料要去搶救,有什么老藝人的身法要去搶錄,有哪一位昆曲老人過世要去慰問。他始終念念不忘,因為,昆曲是他的命根子。后來的一段日子里,桑先生由于肌肉萎縮,不能寫字了,他就堅持讀書看報,他一直說,他要不斷充實自己的幾本書,以后還要修訂,所以要學習。再后來,他報紙都看不下去了,就一直唉聲嘆氣。那時節,輪椅上坐的是一個多么無奈的學者啊,但是他逢人說的還是昆曲。促使他能堅持到最后一刻的,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人間情懷。這種人間情懷使他堅信昆曲里的善和美,是真正意義上的寶貴財富。
2012年6月29日,是蘇州舉辦“第六屆中國昆劇國際研討會”的日子,他早就和女兒約好了,要她送他過去,他知道或許這是他生平最后一次參加這個會議了。他和女兒說要帶上一些自己的書,來贈送給一些海內外的老朋友,這是他最高興的事情了。然而他沒有如愿,在病魔的瘋狂追逐住下,他進了醫院,再也沒有出來。
然而,桑先生做學問的態度和鉆研精神,永遠留在世間。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桑毓喜先生的一生中有很多的求而不得,但這一切并不妨礙他的文字成為珍珠的過程,他只有一個目標——在文字里記錄歷史、記錄一代代曲人情感的寄托和靈魂的升華。我想,人性只有趨善從美,才會有記錄和寫作的沖動,也才會寫出值得珍惜的文字。從這個角度說,桑先生的心,是收集文字的玉盤,而他的作品就如同盤里滾動的大珠小珠。
我手頭上有一份桑夫人秦慶華送來的剪報本,里面貼滿了桑先生在報紙上發表的昆曲史小品。我認真地翻閱著,一個字一個字讀來,我又聽到了一粒粒珍珠滾動的聲響。